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手把手教你写《诗学的读书笔记》,(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13 1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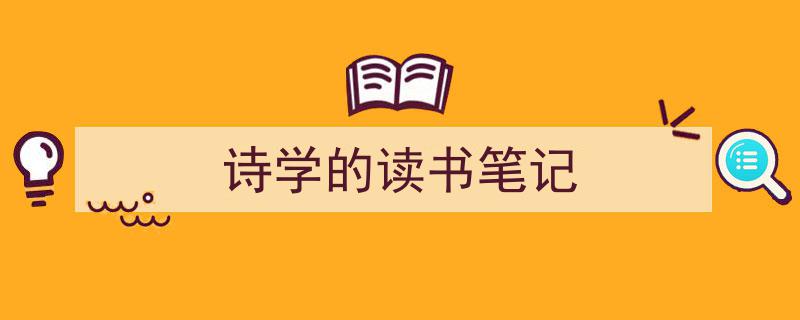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诗学的读书笔记作文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明确主题:在写作之前,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读书笔记主题,即针对诗学的哪些方面进行探讨,如诗的本质、诗歌的表现手法、诗歌与人生的关系等。
2. 结构清晰:一篇优秀的读书笔记应具备清晰的结构,包括引言、主体和结论。引言部分简要介绍诗学的背景和自己的阅读目的;主体部分围绕主题展开论述,分析诗学的理论观点、代表人物和作品;结论部分总结全文,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感悟。
3. 引用准确: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引用诗学理论、观点和例证,确保准确无误。引用时,应注明出处,以体现学术严谨性。
4. 分析深入:对诗学理论、观点和作品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其内涵,揭示其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诗歌的形式、内容、表现手法、主题思想、审美价值等。
5. 结合实际:在分析诗学理论时,可以结合实际作品进行解读,以增强说服力。同时,也可以将诗学理论应用于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探讨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
6. 表达流畅:在写作过程中,注意语言表达的流畅性和准确性,避免出现语法错误和语义不清的情况。
7. 观点独特:在阅读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敢于提出质疑和反驳。在写作时,要突出自己的
在《诗》中发现诗:清代解《诗》学对古典诗学体系的拓展
作者:孙兴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解《诗》学与传统诗学之建构研究”负责人、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诗经》这部先秦典籍,古人既视之为“经”,又视之为“诗”,其在社会政治领域的文德教化和文化学术领域的诗学构建两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由于环绕在它头顶的“经”的光环过于耀眼,致使其“诗”的身份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闻一多《匡斋尺牍》中曾对此表达不满:“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经过漫长的蛰伏期,到清代,将《诗》当文艺(诗)看终于成为一股强大势力,在专门的《诗》学著作以及浩如烟海的诗话、笔记、信札、序跋和诗评中,隐藏着大量这方面材料,它们对丰富和深化中国古典诗学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何谓真诗:在“真诗观”的基础上确立新的诗学规范
在清人看来,明代诗学出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求真不得反成伪,遂使伪诗大行其道。面对此一诗道之厄运,清初诗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真诗”问题的大讨论,力图廓清明代“真诗”思潮中的种种流弊,从而建立新的诗学规范。在此一挽“真诗”之狂澜于既倒的过程中,清代的解《诗》学又贡献了哪些值得关注的观点呢?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诗中须有“真我”。这个“真我”的要义,就表现为“我”之真诚无欺的情志在诗中的自然流露。李柏《襄平张少文诗集序》中说《三百篇》之作乃“率于性者也”,正因其“悉出于天机自然”,故而成为“天下万世诗祖”,确立起后代诗歌创作的楷模与评判的价值尺度。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明代的“真诗观”也是强调“真我”的,如王世贞明确说“有真我而后有真诗”,但问题是,他们所追求的“真我”却误入或以模拟复古为真(如七子派)、或以俚语童言为真(如公安派)、或以幽情单绪为真(如竟陵派)的歧途,结果就表现为以某种预先设定的面目遮蔽了“我”的真性情,这个“真我”也就成了“伪我”,所作之诗自然就是“伪诗”。
“真”须受“正”的制约。既然“真我”的要义在于情志的真诚无欺,那么是不是抒写了真诚无欺之情志的诗歌就可以被称为“真诗”?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真诚无欺”既可用来描述带原始感性意味的自然情感,也可用来描述符合道德理性的社会情感,二者在正统儒家文艺思想中的价值有着天壤之别。杜濬《奚苏岭诗序》中辨析说:“夫诗至于真,难矣!然吾里自一二狂士以空疏游戏为真,而诗道遂亡。真岂如是之谓耶?夫真者必归于正,故曰正《风》正《雅》,又曰变而不失其正。”庞垲《诗义固说》中解释“正变”之内涵曰:“合于礼义者,为得性情之正,于诗为正《风》正《雅》;不合礼义者,即非性情之正,于诗为变《风》变《雅》。”这显然是以《诗》之“正”作为规范,来对“真”进行制约,让其回归儒学“以礼节情”的文化传统,从而让诗更好地发挥对民众进行“温柔敦厚”之良好德性的教化功用。
“真诗”须具有“美”的艺术形式。在保证了诗歌所抒写之情志既“真”且“正”的前提下,如何将其完美地传达出来,就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冯武《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凡例》中指出:“盖诗之为道,固所以言志,然必有美辞秀致而后其意始出。”这就明确说明了艺术传达的美感对所传达之内容具有的重要意义。只有既“真”又“正”且“美”的诗歌,方“不失《三百篇》遗意”,才是真正的“真诗”。
总之,清代解《诗》学对明代“真诗观”的反思,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诸如诗的本质属性、诗应当表现何种性情、诗的美学品质如何保证以及诗之审美与道德之关系等诸多问题的认识,集中体现出中国古典诗学在这些问题上的真知灼见,值得当代诗学认真倾听。
如何读解:对构建中国解释学理论体系的独特贡献
解释学在中西方均有悠久传统,却是在西方率先发展出严密的理论体系和鲜明的学科特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出现了构建解释学中国学派的强烈呼声,呼吁将西方解释学理论与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资源结合起来,以构建起“与西方解释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的以研究中国对经典问题解释的理论体系”。
清代的解《诗》学中包含着对构建中国解释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思想资源。如关于解读活动的“成见”问题,崔述《读风偶识》指出,解《诗》者只有把胸中的“成见”统统抛开,紧紧立足于《诗》文本本身“就诗论诗”,方能避免因“成见”而产生的“伪识”,从而得到真正的“诗人之旨”。
破除“成见”之后,在实际的解《诗》活动中就出现了两种思路:一是以追求“自得”为目的的解诗思路,可称之为中国《诗》学解释学的主观派。王夫之论《诗》之兴观群怨时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又说:“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在他看来,文本的“意义”是处于流动之中的,不同的读者会在各自的阅读中创造出不同的意义——正是这些意义,使得诗成为了鲜活的历史流传物。可见,“自得”所强调的,正是解释者对文本意义的重建和领悟,肯定解释者在意义重建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以追求“原意”为目的的解诗思路,可称之为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客观派。方玉润在阐述其《诗经原始》书名之内涵时称:“名之曰原始,盖欲原诗人之始意也。”表明其目的就是为了将诗人封印于诗篇中的“原意”发掘出来——这个“原意”,乃是独立于读解活动之外、存在于读解活动之前的凝固不变的意义;能否正确获取“原意”就成为读解活动成败的标志。
上述关于“成见”“自得”“原始”等思想,从小处看,探讨的只是在具体的解《诗》活动中,解释主体以何种态度、秉持何种原则对待《诗》文本以及《诗》的意义如何生成和获取的问题,其实将之运用于整个中国传统经史解释活动,这些意见也是适用的,它们是中国文化土壤中生发出来的构建“解释学中国学派”的宝贵资源。
达意成章:“意”所开创的中国古典诗学的新向度
在诗的本体论问题上,《尚书·尧典》所说之“诗言志”被朱自清称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随着陆机“诗缘情”的提出,“言志”还是“缘情”遂成为中国古典诗学史上一个长久争论的问题,并主导着某一时代文艺思潮的走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有“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说法,但总的来看,“意”并未受到足够重视。
宋代诗学标举“意”,但这个“意”侧重于诗之“理趣”,由此形成了宋诗的显著特色。清代解《诗》学则又开辟出另一新的进路。吴乔说:“人心感于境遇,而哀乐情动,诗意以生,达其意而成章,则为六义,《三百篇》之大旨也。”这段议论清楚地区分了“情”和“意”,认为它们是紧密关联却又有着重要区别的两个概念:蕴藏于心者是“情”,外化为章者是“意”。“意”是由人心之中转移到了文本(即“章”)之中的东西,它赖以栖身的所在,不再是人心,而是文本。将“意”和“文本”联系起来思考,是古典诗学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更有论者从此角度切入,在其解《诗》活动中对《诗》和《书》在语言表达方面的不同特色进行辨析。如王夫之《诗广传》中说:“意必尽而俭于辞,用之于《书》;辞必尽而俭于意,用之于《诗》:其定体也。”《书》的特点是用简练的言辞将“意”和盘托出,而《诗》的特点则是用重章叠句、反复咏歌的方式将一个带有极强暗示性的“意”婉曲地传出。王夫之将“意”和“辞”(文本)联系起来谈论,这一点是极为明显的。
上述将“意”与“文本”联系起来谈论问题的思路中,有一个暗示着诗学转关的重要信息需揭示出来,即:在传统诗本体论之“言志”“缘情”外,清代解《诗》学又特别推举出了“尚意”一派。“意”与“志”“情”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是在文本(而非诗人内心)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而文本是经语言文字规约过的,这个规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用理性来考量安排的过程,其目的就在于以最佳的结构状态来传达尽可能完美的“意”。“尚意”观很容易就会导向对文本结构的关注,由此既总结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文本结构论”,又开启了现代诗学中的“文本中心论”,其现代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除以上所举三端外,清代解《诗》学中还隐藏着大量宝贵的诗学材料,但这些材料大都以零碎的、非理论的形态存在,常常进入不了诗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相信随着相关文献的不断整理以及研究的不断推进,那些因入思方式的局限而长期被“视而不见”的材料,将会在别样的问题意识的烛照下获得新的生命,并在构建富于中国特色诗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07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随笔 | 王晓华:酒的诗学
如果说完全清醒的我们仅仅是大地上的过客,那么,微醺的饮者则同时是乌托邦的公民。这是醉之允诺。
原文 :《酒的诗学》
作者 |深圳大学 王晓华
图片 |网络
神奇的液体
在人造物的行列中,一种神奇的液体至今仍占据重要地位。它既是水,又是火,具有点石成金的魔性。当它聚集、流溢、渗透,无数人进入激情洋溢状态,欣欣然陶醉于生命的强大和丰盈。随着生存的浪漫化,饮者被诗性附体,语言之花向着天空开放。
这种神奇的液体就是酒。“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说文解字·酒》)“就,高也。从京从尤。尤,异于凡也。”(《说文解字·就》)
在某些时刻,酒似乎具有升华凡人的力量:
“天上人间酒最尊。非甘非苦味通神。一杯能变愁山色,三笺全迥冷谷春。”(朱敦儒《鹧鸪天·天上人间酒最尊》)
当它引燃血管的导火索,生命会绚丽如礼花般爆发、升腾、绽放。身体似乎可以无所不在,能够往来于天地之间:
“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屈原《九歌·东君》)
当凡俗的身躯被放大时,人似乎变得无所不能,甚至可以抵达不死之境:
“既饮旨酒,永锡难老。”(《诗经·鲁颂·泮水》)
由于酒的魔力,它曾被当作沟通人神的媒介:
“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屈原《东皇太一》)
当酒的香气升腾之际,世界变得朦胧,万物开始重新结缘。诸神从高处降临,加入大地上狂欢的行列,人则似乎随时“乘回风兮载云旗”(屈原《少司命》)。上与下的紧张被暂时消解,凡俗者与神圣者重新结盟。甚至,“连那疏远的、敌意的或者被征服的自然”,“也重新庆祝它与自己的失散之子——人类——的和解节日。”(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剧的诞生》,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25页。)此刻,乌托邦若隐若现,理想国光芒四射。
生存的浪漫化
在原初的饮酒仪式中,一种在场者总是放大了人的欠缺。这就是永恒者。当人称之为神时,一种时间意识已经绽露:个体只能短暂地生存。当他/她于想象中前行时,最终会遇到无法越过的大限。短暂者终将离去。离去并不是奔赴某处,而是坠入虚无之中。对虚无的畏弥漫于生命意识之中,牵连出巨大的恐惧和亘古的哀愁: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陶渊明《饮酒·其三》)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高翥《清明日对酒》)
在从先秦到近代的汉语诗歌中,沉痛之语绵延不绝,道出了短暂者的无奈之情。短暂,是人无法克服的宿命。对酒的发明就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
在醉中,瞬间被拉长、充实、诗化: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水浒传·第二十九回》)。
这是“个体化原理”瓦解的时分,更是此在凸显的瞬间。它既意味着朦胧中的越界,又带来了晦暗中的澄明:
闲愁如飞雪,入酒即消融。(陆游《对酒》)
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王维《酌酒与裴迪》)
这是短暂的救赎,这是瞬间的逍遥。真正的饮者投身于一种不可能的实践:在瞬间中体验永恒,甚至忽略瞬间与永恒的差别。此举注定无法完全成功:
“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
然而,它又绝非徒劳无益: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起决定作用的机制是醉后的遗忘。借助它,饮者获得了短暂的解脱。在流传下来的饮酒诗中,我们可以发现遗忘的诗学。遗忘并不能克服生存的短暂品格,但可以将之悬搁起来。在刻意制造的晦暗状态,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人象征性地完成了自我超越。这是时间维度的浪漫化。
浪漫化的本质是追求无限,但这恰好与生存的有限性相悖:个体既不能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也无法越过生存的大限。在试图将世界浪漫化的过程中,诗人处于深渊的两端,必须忍受自我的分裂。此时,饮酒是克服悖论的一种方式。酒总是与醉相关。“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于乱也。一曰溃也。”(《说文解字》)溃当然会导致个体层面的混乱,但更意味着越界和出位、疯癫和狂欢、解构与超越。边界和等级依旧存在,但暂时被悬搁起来。在酒的香气弥漫之处,乌托邦腾空而起,诸神翩翩起舞。由于酒的魔力,生命突破了皮肤的边界,一个隐形的帝国诞生了,饮者拥有更广阔的疆域,甚至可以畅游于星汉之中:
从醉里,忆平生。可怜心事太峥嵘。更堪此夜西楼梦,摘得星辰满袖行。(王国维《鹧鸪天·列炬归来酒未醒》)
这是想象中的狂欢,是内在的嘉年华。它存在于缩微的宇宙中,但并非仅仅是一个人的节日。在微醺之际,饮者加入到万物狂欢的行列:他/她与明月同饮,携松树起舞,伴飞鸟放歌。一个宇宙剧场悄然成形,天、地、人、神、物都成了演员。
当我们饮酒时,世界被浪漫化了,人变成了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的越界者。这不正是生存之魅吗?生存就是不断地前行、出位、绽出。当人越过原有的疆域时,陶醉感就会应运而生。人就其本性而言是能醉者。能醉意味着人将醉带入澄明之中,造就自我反射的醉境。当饮者烂醉如泥时,醉境就会消失。真正的饮者追求适度的醉。只有后者才能将人的人道抬得足够高。当李白声称“惟有饮者留其名”时,他已经破译了其中秘密。如果说完全清醒的我们仅仅是大地上的过客,那么,微醺的饮者则同时是乌托邦的公民。这是醉之允诺。虽然它不能带来永远的解脱,但至少意味着瞬间的救赎。对于短暂者来说,这或许已经足够。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9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万象 | 李白的酒量其实就一杯“啤酒”的量……
把酒祝东风:在比利时,我喝到了最美味的啤酒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