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写作《化归与转化的思想》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31 05: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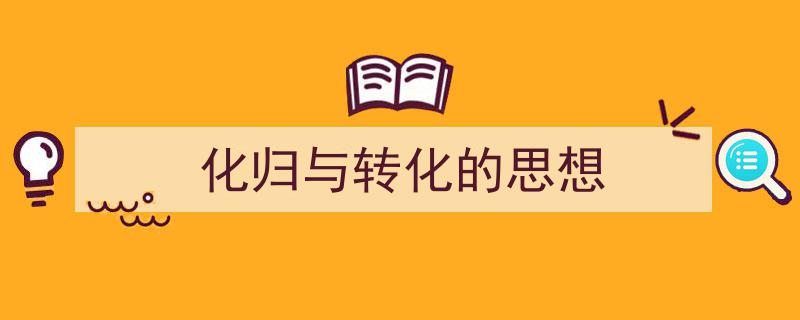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化归与转化”思想的文章,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的深度、清晰度和说服力:
1. "深刻理解核心概念 (Deep Understanding of Core Concepts):" "定义清晰:" 首先要明确界定“化归”与“转化”的含义。化归通常指将复杂、陌生、难解的问题通过某种手段(如变换、替换、简化等)转化为简单、熟悉、易解的问题来解决。转化则更广泛,可以指事物形态、性质、关系等方面的转变,也可以指在思维过程中调整视角、变换方法等。要阐述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本质把握:" 理解这两种思想的核心在于“化难为易”、“变未知为已知”、“变不熟悉为熟悉”。它是一种重要的思维策略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思想。
2. "阐述其重要性与普遍性 (Elaborate on Its Significance and Universality):" "思维方法:" 强调化归与转化是贯穿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基本思维方法。它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解决问题:" 论述它是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有效途径。无论是数学中的难题、工程中的瓶颈,还是学习中的困惑、生活中的难题,都可以尝试运用化归与转化的思想。 "学科体现:" 结合具体学科实例(如数学中的
翟元斌 陈振 ‖ “庄仕华现象”:雷锋精神新时代转化典范及理论内涵
所谓“庄仕华现象”,是指以当代雷锋庄仕华为代表所展现出的一系列体现时代精神与高尚品质的行为特征及其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的现象。
庄仕华通过扎根边疆医疗事业50余年的职业化奉献,将雷锋精神的“服务人民、甘于奉献”内核内化为“职业信仰与社会责任的统一”,创造了13万例无事故手术的医学成就并开展大规模公益帮扶,实现了雷锋精神从道德号召到职业化实践的深度转化。
在实践逻辑上,庄仕华现象通过双重路径推动精神转化:一是组织化运作,建立覆盖全国13省市的“少先队庄仕华中队”“跟着庄仕华学雷锋志愿服务中队”百余支,形成“大手拉小手”的常态化实践机制;二是教育化融入,通过进入大中小学思政课堂、开发特色课程及建设校园文化,构建“识先锋—悟品质—践行动”的教育体系,使雷锋精神实现代际传承。
理论层面,该现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层契合:其边疆坚守体现“爱国”,医疗精益求精诠释“敬业”,公益帮扶彰显“友善”。更重要的是,它推动雷锋精神实现三重升华——从个体行为到组织化实践、从医疗奉献到教育引领、从地方经验到全国推广,使其成为可复制、可持续的普适价值理念。
庄仕华现象为新时代雷锋精神传承提供了系统化、制度化范本,对道德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一、界定“庄仕华现象”与雷锋精神的时代背景在新时代背景下,雷锋精神的传承与转化成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议题。庄仕华,作为一位扎根边疆医疗事业的军医,被授予“当代雷锋”称号,其事迹和精神实践不仅体现了雷锋精神的延续,也彰显了其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升华。庄仕华现象并非简单的个人模范行为,而是一种将雷锋精神与职业信仰、社会责任紧密结合的时代典范,它为雷锋精神的现代化实践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雷锋精神自1963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以来,逐渐成为全党全社会的道德标杆。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即在平凡岗位上尽职尽责、默默奉献——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解读。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改革开放后的“无私奉献、服务社会”,再到新时代“奉献人民、服务国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化,雷锋精神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庄仕华现象则是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以实际行动将雷锋精神的“服务人民、奉献社会”转化为职业化的医疗奉献行为,其精神实践不仅具有个人意义,更在社会层面为雷锋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
庄仕华现象与雷锋精神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其价值不仅在于个体的道德实践,更在于其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推动作用。作为一位长期在新疆工作的军医,庄仕华将“螺丝钉精神”具体化为“医生的螺丝钉精神”,在偏远、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为边疆人民提供医疗服务,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践行了雷锋精神。他的事迹表明,雷锋精神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化概念,而是可以通过职业化、组织化的方式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延续与拓展。
由此可见,庄仕华现象不仅是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更是其转化的典范。通过医疗事业的深耕与奉献,他将雷锋精神从口号式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并在边疆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影响力。这种转化不仅体现了雷锋精神的时代适应性,也展现了其在新时代背景下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意义。
(一)“庄仕华现象”的核心内涵:扎根边疆医疗事业的职业化奉献典范
庄仕华现象的核心在于其“职业化奉献”的特质。作为武警新疆总队医院的名誉院长,庄仕华在新疆边疆地区深耕医疗事业50余年,其事迹被广泛认为是雷锋精神在当代社会的具体实践。他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军医,更是一位将雷锋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典范人物。
庄仕华的职业化奉献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他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雷锋精神与本职工作紧密结合。他曾在腹腔镜手术领域创造了13万例无事故的医学奇迹,通过持续的技术钻研和实践,为数以万计的边疆患者解决了病痛问题。其次,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为偏远地区医院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培养。例如,他义务帮助了26家偏远贫困农牧区医院改善医疗条件,培养了200多名技术骨干,并帮助680多名患者摆脱贫困。这种将个人职业成就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实践,使得庄仕华成为“职业信仰与社会责任的统一”的代表。
庄仕华现象的典范意义还在于其“人人可学、处处可为”的特质。他强调,雷锋精神并非遥不可及的道德楷模,而是每个人都可以践行的生活准则。例如,他通过“庄仕华志愿服务中队”的建立,将雷锋精神转化为青少年群体可以参与的组织化实践平台。这一做法不仅拓展了雷锋精神的传播路径,也增强了其在新时代的可操作性与可推广性。
此外,庄仕华的奉献行为与雷锋精神中“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理念高度契合。他从一名卫生员起步,逐步成长为外科专家和医院管理者,始终将专业精神与奉献精神并重。他曾在煤油灯下刻苦学习医学知识,并通过反复练习剥葡萄皮等日常细节,将普通技能转化为专业成就。这种对职业的极致追求,正是雷锋精神在新时代职业化语境中的生动体现。
综上所述,庄仕华现象的核心在于其将雷锋精神的职业化实践推向极致,通过持续的医疗奉献、公益行动和组织建设,为新时代的道德教育和社会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榜样。
(二)雷锋精神的历史演变:从“螺丝钉精神”到“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时代价值变迁
雷锋精神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从具体行为到普适价值理念的演变过程。最初的“螺丝钉精神”强调的是个体在集体中的定位与作用,即每个人都要像螺丝钉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不计个人得失。这一精神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受到推崇,成为激励无数人投身国家建设的道德力量。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雷锋精神的内涵逐步扩展,从单一的职业奉献,演变为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
进入21世纪,雷锋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色,即“服务人民、奉献社会”。这种演变不仅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也体现了国家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更高要求。庄仕华现象正是这一演变的现实写照。他不仅在医疗岗位上践行“螺丝钉精神”,更将这种精神延伸至社会服务领域。他常年奔波于新疆的高原、戈壁和牧区,行程累计达40万公里,巡诊超过38万人次。这种超越个体岗位的奉献精神,使得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雷锋精神的历史演变还体现在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爱国、敬业、友善”等理念,而庄仕华的实践正是对这些价值的生动诠释。他不仅通过精湛的医术服务边疆人民(敬业),还通过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推动社会和谐(友善),同时以坚定的政治信仰和行动践行“爱国”精神。例如,他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雷锋精神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是一座永放光芒的灯塔”,这表明其精神实践不仅与雷锋精神一脉相承,更与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
此外,庄仕华现象还展示了雷锋精神从“道德楷模”向“精神引领者”的转变。在新时代背景下,雷锋精神的传承不仅依赖于对雷锋本人的纪念与宣传,更需要通过“当代雷锋”这样的典型人物,将精神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行为模式。庄仕华通过建立“庄仕华志愿服务中队”、参与学校思政课教学、推动“庄仕华精神”进入青少年教育体系,使得雷锋精神的传承不仅停留在口号层面,更在教育与实践领域实现了“常态化”与“长效化”。
由此可见,庄仕华现象作为雷锋精神的现代转化,深刻反映了雷锋精神在时代变迁中的价值适应性。他将“螺丝钉精神”升华为“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实践理念,并通过职业化与组织化的手段,使得雷锋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加鲜明的光彩。这种演变不仅是雷锋精神的延续,也是其在新时代背景下,作为道德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的体现。
二、“庄仕华现象”作为雷锋精神时代转化典范的实践逻辑庄仕华现象之所以能够被视为雷锋精神时代转化的典范,不仅在于其对雷锋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更在于他通过组织化运作和教育化融入,将这一精神有效地转化为可推广、可持续的社会实践模式。这种转化路径体现了雷锋精神从个体道德自觉到制度化推动的深刻变革,使得雷锋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得以延续、普及并融入日常生活与教育体系。通过分析其继承精神的逻辑,以及组织化和教育化两个具体路径的实践效果,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庄仕华现象在雷锋精神转化中的独特价值。
(一)继承:将雷锋精神的“服务人民、甘于奉献”内化为“职业信仰与社会责任的统一”
庄仕华对雷锋精神的继承,首先体现在其对“服务人民、甘于奉献”的深刻内化。雷锋精神的核心在于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而在庄仕华的职业生涯中,这种精神被转化为一种“职业信仰与社会责任的统一”。庄仕华自1973年入伍以来,始终坚守在医疗一线,从一名卫生员成长为外科专家,再到医院管理者,他的职业信仰从未动摇。他将“把病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把病人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生命”作为职业信条,这种对患者的责任感不仅是一种职业操守,更是一种将社会责任融入职业行为的体现。
庄仕华的这种信仰与责任的统一,源于他对雷锋精神的深入理解和长期践行。他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自己是在雷锋精神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并始终以雷锋为榜样,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行动指南。他不仅在技术上追求卓越,如通过每天练习剥葡萄皮来提升微创手术精度,更在精神上践行“甘于奉献”的信念。他长期为贫困患者垫付医疗费用,累计捐款超过80万元,帮助580多位患者摆脱困境,这些行为充分体现了他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也彰显了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性。
由此可见,庄仕华的“服务人民、甘于奉献”并非一种抽象的道德口号,而是通过具体的职业行为和长期的社会责任承担,将雷锋精神内化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仅支撑着他在边疆医疗事业上的坚守,也推动他将雷锋精神融入更广泛的社会实践,为后续的组织化和教育化路径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 转化路径
其一:通过组织化运作实现雷锋精神的普及与常态化
庄仕华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实践逻辑在于通过组织化运作的方式,将雷锋精神的个体行为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化实践。“跟着庄仕华学雷锋志愿服务中队”正是这一路径的典型体现。从2023年9月首支少先队庄仕华中队在抚顺成立开始,这一模式迅速扩展至全国13个省市,包括辽宁、新疆、四川等地,累计建立了百余支特色中队和志愿服务团队。这些组织不仅将雷锋精神注入青少年群体,还通过具体的志愿服务活动,使这一精神在实践中得以延续和强化。
跟着庄仕华学雷锋志愿服务中队的运作方式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首先,它通过“大手拉小手”的方式,将庄仕华本人的道德实践与青少年群体的教育活动紧密结合。例如,在沈阳市皇姑区宁山路小学,“庄仕华中队”被授旗后,学校聘请庄仕华为荣誉校长,并通过授旗仪式、主题报告和志愿服务活动,让青少年在参与中体验雷锋精神的内涵。其次,这些中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跟着庄仕华学雷锋志愿服务中队形成联动。通过这种组织化的志愿服务体系,庄仕华不仅将个人的奉献精神传播到更广泛的群体中,也通过制度化的运作方式,确保雷锋精神的传承具有可持续性与常态化。
跟着庄仕华学雷锋志愿服务中队的建立,还为雷锋精神的实践提供了新的社会空间。这些中队不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还涉及环境保护、关爱退役军人、青少年成长等多个领域。例如,成都英华学校“庄仕华中队”参与“青春护河”行动,清理河岸垃圾并普及环保知识,而克拉玛依市的“庄仕华中队之林”则通过植树造林活动,将雷锋精神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这种组织化运作模式,使得雷锋精神的传播不再局限于特定节日或纪念活动,而是融入了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可实践、可感知的精神力量。
此外,跟着庄仕华学雷锋志愿服务中队的建立也体现了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适应性。在社会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雷锋精神的传承面临挑战。然而,“庄仕华志愿服务中队”通过组织化的形式,使得雷锋精神的传播更具系统性和针对性。例如,庄仕华亲自参与思政课教学,通过互动式、体验式教育,使得青少年不仅在理论上理解雷锋精神,更在实践中体验其价值。这种组织化运作方式,不仅提升了雷锋精神的影响力,也为新时代道德教育提供了可推广的路径。
其二,通过教育化融入实现雷锋精神的价值传承
如果说组织化运作是雷锋精神普及的外部机制,那么教育化融入则是其价值传承的内部逻辑。庄仕华现象的一个重要实践路径,就是通过将雷锋精神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实现对青少年群体的价值引领和道德塑造。2024年10月28日,成都英华学校举办了一场以“弘扬庄仕华精神,践行雷锋精神”为主题的思政课活动,庄仕华亲自到场与师生互动。他通过讲述自己的医疗经历和奉献故事,将雷锋精神转化为具体的教学内容,使得学生能够通过身边榜样的行为,理解雷锋精神的实质。
庄仕华的教育化融入实践具有多层次的特点。首先,它通过课程设计,将雷锋精神与思政课的核心目标相结合。例如,克拉玛依市第五小学、第十小学开发了《庄仕华精神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实践研究》课题,并通过“AI对话”“先锋人物进课堂”等方式,构建“识先锋—悟品质—践行动”的三阶教学体系。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感,也使雷锋精神的传承更加生动和具体。其次,庄仕华的教育化融入还体现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例如,学校设立了“庄仕华学雷锋书屋”,收藏了大量关于雷锋精神的书籍和资料,为学生提供了学习雷锋精神的平台。这种文化环境的营造,使得雷锋精神不再是书本上的理论,而是校园生活中的日常实践。
庄仕华现象的教育化融入还通过“庄仕华中队”的活动得以深化。这些中队不仅在课堂上学习雷锋精神,还在课外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如为贫困学生捐款、为边疆群众送医送药等。例如,在河南郑州的伏牛路第四小学,“庄仕华中队”不仅参与植树造林活动,还通过“庄仕华中队之夜”等文艺活动,将雷锋精神融入校园文化。这种“理论学习+实践体验”的模式,使得雷锋精神的传承更加立体和深入。
此外,庄仕华的教育化实践还体现了雷锋精神的时代化特征。在新时代背景下,雷锋精神的传承不仅需要理论灌输,更需要与青少年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庄仕华通过“庄仕华志愿服务中队”的建立,将雷锋精神与青少年的成长需求相融合。例如,他鼓励学生从小立志,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这种教育化路径不仅提升了雷锋精神的传播效果,也为新时代道德教育提供了创新思路。
通过组织化运作和教育化融入两条路径,庄仕华现象实现了雷锋精神从个体到群体、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转化。这种转化不仅使得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庄仕华的实践逻辑表明,雷锋精神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可以通过具体制度和教育方式,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其价值传承与社会普及。
三、 “庄仕华现象”所蕴含的理论内涵与价值引领庄仕华现象不仅是一种道德实践的典范,更是一种具有深刻理论内涵与价值引领意义的道德体系。通过将雷锋精神融入医疗事业、志愿服务与青少年教育,庄仕华的实践超越了个体行为的范畴,实现了从具体行为到普适价值理念的升华。这种升华不仅契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友善”的核心要求,也为新时代的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一)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契合机制(聚焦“爱国、敬业、友善”)
庄仕华现象之所以能够成为雷锋精神时代转化的典范,首先在于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在新时代倡导的价值体系,其核心内容包括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爱国、敬业、友善”是庄仕华现象最直接体现的价值维度。
爱国:庄仕华的边疆医疗实践体现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庄仕华自1973年入伍以来,始终坚守在边疆医疗一线,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他的“庄仕华志愿服务中队”项目不仅覆盖了全国13个省市,更通过在新疆等地的医疗援助与民族团结行动,展现了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定信念。庄仕华在新疆边疆巡诊40万公里,服务39万多人次,这种深入基层、服务边疆的行为,正是“爱国”精神的现实体现。
敬业:庄仕华将雷锋精神与职业信仰高度统一
庄仕华的职业生涯充分展现了“敬业”的精神内涵。他从一名卫生员成长为外科专家,始终秉持“把病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的信念,并创造了13万例无事故的微创手术记录。他不仅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还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将雷锋精神中的“螺丝钉精神”转化为“医生的螺丝钉精神”,即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不断钻研,为国家医疗事业作出贡献。
庄仕华还通过教育活动,将敬业精神传递给青少年。例如,在成都英华学校举办的思政课中,他鼓励学生“珍惜时光,严于律己,努力成为德技双馨的高技能人才”。这种敬业精神的传承,使得庄仕华现象不仅是一种道德实践,更是一种职业伦理的典范。
友善:庄仕华的公益行动体现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
庄仕华的志愿服务中队不仅关注医疗救助,还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他累计资助71名贫困学生,帮助690多名贫困患者摆脱困境。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正是“友善”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他通过实际行动,将雷锋精神中的“无私奉献”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具体行为。
庄仕华还通过“庄仕华志愿服务中队”推动青少年参与公益,帮助他们建立“服务社会”的价值观。例如,在湖南长沙的“庄仕华中队”活动中,学生通过文艺表演和志愿服务,将雷锋精神与友善理念深度融合。这种教育方式不仅增强了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也使雷锋精神的传承更具现实意义。
(二) 实现雷锋精神从具体行为到普适价值理念的升华
庄仕华现象之所以能够成为雷锋精神时代转化的典范,还在于其将雷锋精神从具体行为提升为普适价值理念。雷锋精神最初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主要体现在雷锋本人的具体行为上,如做好事不留名、勤俭节约等。然而,庄仕华通过组织化运作和教育化融入的方式,将雷锋精神提升为一种普适性的价值理念,并在多个领域实现了这一升华。
从个体行为到组织化实践:构建雷锋精神的长效机制
通过建立“少先队庄仕华中队和跟着庄仕华学雷锋志愿服务中队等组织,将雷锋精神从个体行为提升为组织化实践。这种组织不仅为雷锋精神的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使得雷锋精神的传播更加系统化、常态化。例如,在黑龙江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等七所学校聘请他为荣誉校长,并成立跟着庄仕华学雷锋志愿服务中队。这种制度化的组织形式,使得雷锋精神不再局限于特定时间或特定个体,而是成为一种长期的社会实践。
从医疗奉献到教育引领:雷锋精神的多维度升华
庄仕华不仅在医疗领域践行雷锋精神,还通过教育活动将其转化为一种普适价值理念。他多次参与大中小学思政课,通过讲述自己的医疗经历和奉献精神,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例如,在新疆医学院,他通过讲座和互动,鼓励学生“成为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这种教育活动将雷锋精神从具体医疗行为提升为一种教育理念,使得雷锋精神成为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精神资源。
从地方实践到全国推广:雷锋精神的广泛认同
庄仕华现象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从地方实践走向全国推广,实现了雷锋精神的广泛认同。他的事迹不仅在新疆边疆地区广为传颂,也在四川、辽宁、湖南等多个省市被广泛学习和推广。例如,2025年6月,“庄仕华大思政”论坛,通过网络开通。吸引了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志愿者和教育工作者参与。这种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使得庄仕华现象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雷锋精神时代转化的典范。
从历史记忆到现实行动:雷锋精神的时代适应性
庄仕华现象还展示了雷锋精神从历史记忆向现实行动的转化。雷锋精神曾被视为一种历史记忆,但在庄仕华的实践中,这一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例如,他通过“庄仕华志愿服务中队”的建立,将雷锋精神与当代青少年的成长需求相结合。这种转化不仅使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使得其成为一种可以被广泛认同和践行的价值理念。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庄仕华现象不仅实现了雷锋精神的组织化和教育化,还将其从具体行为提升为普适价值理念。这种升华不仅契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也为新时代的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庄仕华现象表明,雷锋精神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可以通过具体实践,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其价值传承与社会普及。
四、“庄仕华现象”的典范地位及其理论启示
(一)“庄仕华现象”作为雷锋精神时代转化典范的合理性
庄仕华现象作为雷锋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转化典范,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现实依据。其合理性首先体现在对雷锋精神核心价值的深刻继承与创新性转化。雷锋精神的“服务人民、甘于奉献”在庄仕华的职业生涯中被具体化为“职业信仰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他以军医的身份,将雷锋精神内化为医疗行业中的实际行动,展现出高度的专业精神与无私奉献,为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内涵拓展提供了鲜活样本。
其次,庄仕华现象的合理性在于其实践路径的系统性与时代适应性。通过“少先队庄仕华中队”“跟着庄仕华学雷锋志愿服务中队”的组织化运作,他将雷锋精神从个体行为扩展为群体实践,实现了雷锋精神的常态化与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将雷锋精神融入中小学思政课,他推动了雷锋精神的教育化传播,使这一精神成为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价值导向。
最后,庄仕华现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影响力。其“职业化奉献”与“医疗专业奉献”的路径展现出独特的专业深度与组织广度。这种转化不仅契合了当代社会对职业伦理与社会责任的更高要求,也为雷锋精神的传承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模板。
(二)“庄仕华现象”对新时代道德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贡献
庄仕华现象对新时代道德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推动了雷锋精神从历史记忆向现实行动的转变,使这一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通过将雷锋精神与医疗行业深度结合,他为雷锋精神的职业化落地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拓宽了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
第二,庄仕华现象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知行合一”的新路径。他通过组织化志愿服务与教育化融合的方式,构建了一个“识先锋—悟品质—践行动”的教育闭环,使得雷锋精神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可感知、可参与的价值实践。这种教育模式增强了雷锋精神在青少年群体中的认同感与参与度,为新时代道德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三,庄仕华现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深层次的契合。他以“爱国、敬业、友善”为核心,通过边疆医疗服务、技术钻研与公益行动,展现了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普适性价值。这种契合不仅强化了雷锋精神与国家主流价值观的一致性,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具时代感与实践性的教学资源。
综上所述,庄仕华现象不仅在实践层面成功实现了雷锋精神的时代转化,在理论层面也为新时代的道德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它展示了雷锋精神如何在专业化、组织化和教育化的路径中延续与发展,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供了典范与方向。
从概念到范畴:中国早期哲学中“变化”思想的生成与确立
“变”与“化”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极其重要且内涵深邃的核心范畴。二者从最初的独立概念,历经漫长复杂的语义演变与哲学提升,最终在战国中后期凝结为一对具有高度辩证性质的对偶范畴,深刻塑造了中国思想的特质与走向。
一、字源探微与早期语义:独立概念的初步展开
“变”字初义,在于更改、更易。《小尔雅·广诂》明言:“变,易也。”其早期应用多见于描述具体状态的转换。《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文公重耳流亡时,“公惧,变色”,描绘了因恐惧而导致的脸色改变,是具体生理状态的“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婴语:“工贾不变”,指工匠商贾各守其业,不轻易改行,此“变”指向职业身份或社会分工的稳定性。在政治社会层面,“变”更常指深刻的改革或转型。《论语·雍也》中孔子论及文化政治理想:“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此处的“变”蕴含了由现实向更高理想状态的根本性跃迁,已初步触及变革的本质。
“化”字本初,则与教化、感化紧密相连。《说文解字》释“化”:“教行也”,核心在于以德行或政教引导、转化人心风俗。《老子·第五十七章》所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正是此义——统治者行无为之政,百姓自然受到感化而归于纯朴。《老子·第三十七章》“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则将此“化”提升到宇宙论层面:侯王能持守无名之道,万物将依循自身规律自然化育生成。此时的“化”,已隐含了自然生成、演化的意蕴。
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文献中,“变”与“化”虽已各自蕴含丰富的哲学潜力,但二者在多数语境下仍是独立使用的单一概念。即便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所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此处“变化”虽已连用,但“变”与“化”在此基本同义,强调的都是军事态势如同流水一般没有固定形态,需根据敌情灵活“改变”策略。这里的“变化”尚未形成具有内部张力与区别性定义的对偶结构,本质上仍是一个内涵相对单一的复合概念。
二、战国酝酿:概念分立与哲学深化的前奏
进入思想空前活跃的战国时期,“变”与“化”作为哲学概念,其内涵开始被更深入地挖掘,并逐渐显露出分化的趋势。
(一)相对静止与普遍运动的认识深化
《管子·心术上》提出:“静则不变,不变则无过。”将“静”与“不变”相关联,视其为避免过失的一种状态(主要指心术修养)。然而,同一篇章又言:“虚而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此处“化育”一词,已将“化”与万物生成的根本动力——“德”联系起来,凸显了“化”作为宇宙创生与演化的普遍力量。《管子》作者敏锐地认识到,虽然追求内心的虚静有其价值(“静则不变”),但外部世界乃至内在德性的生成(“化育万物”)本身就是一个不息的变化过程。这反映了思想家们对世界存在状态(静与动、不变与变)的辩证思考开始萌芽。
(二)“变”与“化”语义的初步分野
孟子对二词的使用,清晰地体现了当时语义的分化倾向。他论“变”:“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此“变”指当诸侯危害国家社稷时,应当采取更换君主的激烈变革行动,带有明显的主动性、强力性和结果可见性。而论“化”:“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孟子·尽心上》),则指圣贤君子所经之处,百姓自然受到德性感化,这种“化”更强调一种春风化雨般的潜移默化过程,其效果深刻而持久(“神”),但变化过程往往不易被即时察觉。孟子虽未将二者作为对偶范畴进行哲学辨析,但其用法已为后世区分“显著之变”与“渐进之化”埋下了伏笔。
(三)“物化”思想的提出与“变”的专论
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了极具哲学深度的“物化”概念:“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周梦蝶的寓言,并非探讨梦境真实与否,而是深刻揭示了万物形态、界限在“化”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流动性、相对性和不确定性。“物化”指万物之间相互转化、彼此融通的状态,是宇宙大化流行本质的体现。其核心在“化”,强调转化的自然性、贯通性与界限的消弭。与此同时,名家代表公孙龙则以其独特的逻辑思辨,将“变”本身作为核心议题进行专门探讨,撰写了《通变论》。文中通过精密的逻辑推演探讨“变”的性质:“曰:谓变非不变,可乎?曰:可。曰:右有与,可谓变乎?曰:可。曰:变只。曰:右。曰:右苟变,安可谓右?苟不变,安可谓变?”公孙龙通过设定“右”这个对象及其属性(“与”),层层设问,尖锐地揭示了“变”与“不变”这对矛盾概念的逻辑困境:如果一个事物(如“右”)发生了“变”,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事物(“右”);如果它没有变,又怎能称之为“变”?这种看似诡辩的讨论,实际上触及了变化过程中事物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哲学难题,极大地提升了“变”作为一个独立哲学概念的思辨高度。庄子的“物化”论与公孙龙的“通变”辩,分别从宇宙生成论和逻辑哲学的角度,将“化”与“变”的哲学意涵推向了新的深度,为二者最终结合为一对范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范畴确立:《易传》与荀子的关键性综合与界定
战国中晚期,《易传》(尤其是《系辞传》和《文言传》)与荀子的思想,标志着“变”与“化”完成了从独立概念到对偶范畴的质的飞跃。他们不仅明确区分了二者的内涵,更深刻地阐述了其辩证统一关系。
(一)《易传》:宇宙法则的揭示与范畴对立的明晰
1.变化作为宇宙根本法则:《系辞上》开宗明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指出日月星辰运行(象)、山川草木显形(形),其背后呈现的正是宇宙间永恒不息的“变化”法则。变化被提升为贯穿天地的、最普遍、最根本的客观规律。《系辞上》又云:“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圣人效法的核心对象,正是天地所展现的“变化”之道。更进一步,《文言传》释乾卦:“天地变化,草木蕃。”强调正是天地间的阴阳变化、四时更迭,才使得万物(草木)得以繁茂生长。变化被确立为宇宙生成、万物演进的终极动力和普遍规律。
2.“变”与“化”的经典定义与辩证关系:《易传》最杰出的贡献,在于首次清晰、明确地对“变”与“化”进行了哲学定义,并揭示了其内在联系。《系辞上》言:“化而裁之谓之变。” “化”,指事物在时间中细微、渐进、不易察觉的量变积累过程。“裁”,有裁断、决断、使之显现之意。当渐进积累的量变达到某个临界点,发生根本性的转折,新的性质或形态得以确立,这个由“化”积累而成的转折点或质变点,就被称为“变”。简言之,“变”是“化”的阶段性结果和显著表现形态。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所疏:“‘化而裁之谓之变’者,阴阳变化而相裁节之谓之变也。” 这一定义深刻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连续性的、渐进的“化”与飞跃性的、显著的“变”之间的辩证关系:变由化生,化积为变。
(二)荀子:经验世界的印证与定义的补充
荀子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其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深刻观察,进一步从经验层面印证并补充了“变”与“化”这对范畴的内涵。
1.“变化”作为万物成就之因:荀子亦常连用“变化”,将其视为万物生成发展的普遍机制。《荀子·哀公》载孔子语:“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 大道之所以能成就万物,正是通过“变化”这一根本途径。这与《易传》视变化为宇宙根本法则的观点高度一致。
2.对“化”的精确定义:荀子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定义:“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荀子·正名》)此定义精准刻画了“化”的特征:事物在形态、状态(“状”)上发生了改变,但其根本性质、实质(“实”)并未发生本质性的区别,由此产生的差异(“异”)就是“化”。例如,一个人从幼年到老年,形体、容貌、体力发生了显著改变(状变),但其作为“这个人”的同一性并未丧失(实无别),这种由时间带来的、非根本性的差异状态,就是“化”的过程和体现。这个定义完美地解释了《易传》中作为量变积累过程的“化”。
3.与《管子》的呼应:《管子·七法》曾描述“化”的特征:“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其中“渐”(逐渐)、“久”(持久)、“靡”(细微)尤为关键,深刻揭示了“化”所具有的渐进性、长期性和细微不易察觉性。荀子的“状变而实无别”正是对这种渐进、累积性变化导致非本质差异的理论概括和提升。
(三)范畴确立的关键:相互规定与辩证统一
《易传》的“化而裁之谓之变”是以“化”来界定、说明“变”的产生根源(变由化生);荀子的“状变而实无别谓之化”则是以“变”(形态之变)的结果特征来界定、说明“化”的性质(化导致非本质差异)。这种“相互规定”的思维模式,是哲学范畴形成的关键标志。它表明:
1.“变”与“化”已成为一对具有明确相对独立内涵的概念:变指向显著、根本的转折(质变);化指向细微、渐进的积累(量变)。
2.二者被置于一个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之中:它们相互区别(显与隐、剧与渐、质与量),又相互依存(变是化的结果,化是变的基础)、相互转化(化积累到极点导致变,变后新的化又开始)。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深刻关系,使得“变化”最终从单一或同义复合概念,升华为中国哲学中一对成熟、稳定、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核心范畴。
四、思想奠基:早期变化观的深远影响
先秦儒道诸家对“变化”的深刻思考,特别是《易传》与荀子对“变”与“化”作为对偶范畴的确立,为中国哲学后续发展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
(一)《周易》哲学的支柱
“变”与“化”成为理解《周易》象数义理的核心钥匙。六十四卦的流转象征宇宙万物变易不居的规律(“易”者,变易也);卦爻之间的承、乘、比、应、往来、升降,无不体现着“化”的细微累积与“变”的时机显现(“化而裁之”)。占筮的本质在于“极数知来”、“通变”,即通过把握变化之理预测未来、指导行动。王弼注《易》,强调“适时之变”,程颐、朱熹阐发“变易”与“交易”之理,皆根植于此。
(二)宇宙生成论与本体论的核心
变化范畴被用来解释世界的起源与构成。道家(如《淮南子》)讲“气化流行”,宇宙万物由混沌未分之气,通过阴阳激荡、消息盈虚的“化”育过程生成(“化育万物”)。儒家(如张载)讲“气化”,“太虚即气”在聚散屈伸的永恒变化中形成万物万象。变化被视为宇宙存在的根本状态和内在动力(“生生之谓易”)。
(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圭臬
变化观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它要求认识事物必须具有发展的眼光(“知变化之道”),看到其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原始反终”)。在方法论上,强调因时制宜、通权达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无论是治国理政(“变法图强”)、军事谋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个人修养(“化性起伪”),还是应对自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都必须把握变化的规律与时机(“知几其神”)。董仲舒虽言“天不变道亦不变”,但其“更化”主张仍以承认社会需适时变革为前提。王夫之“天地之化日新”更将变化视为宇宙的绝对法则。
(四)辩证思维的重要源泉
“变”与“化”这对范畴本身就蕴含深刻的辩证思想。它们揭示了事物发展中量变(化)与质变(变)的关系、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渐进过程与飞跃转折的联结。这种对矛盾运动、对立面转化的深刻洞察(“一阴一阳之谓道”),构成了中国古典辩证法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强调矛盾斗争的西方辩证法形成鲜明对比,更倾向于一种和谐转化的动态平衡观。
结语
从甲骨金文中“变”隐含的武力更替,到《说文》里“化”指向的德性熏陶;从《孙子》中“变化”连用的浑然一体,到《易传》“化而裁之谓之变”、荀子“状变而实无别谓之化”的精妙互释,“变”与“化”这对范畴的生成史,正是中国哲学思维从具象走向抽象、从描述迈向思辨、从单一概念跃升至辩证范畴的缩影。
它们如一对深邃的哲学之眼,使先贤得以洞察天象流转的玄机、大地草木荣枯的韵律、人世兴衰更迭的法则。宇宙被理解为一个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有机整体,其内在脉搏正是这“变”与“化”的永恒律动——化如春雨润物,悄然累积;变似惊雷破空,万象更新。二者相推相荡,构成了华夏文明理解世界存在方式与运动法则的基石。后世无论是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论断,抑或王夫之“天地之化日新”的辩证宣言,无不在这对古老范畴的思辨疆域内展开其思想的远征。理解“变化”,便是理解中国哲学宇宙观中那不息的生命之流与深邃的生成之秘。
参考文献: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史哲大辞典》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