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精心挑选《梁晓声读书笔记》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31 16: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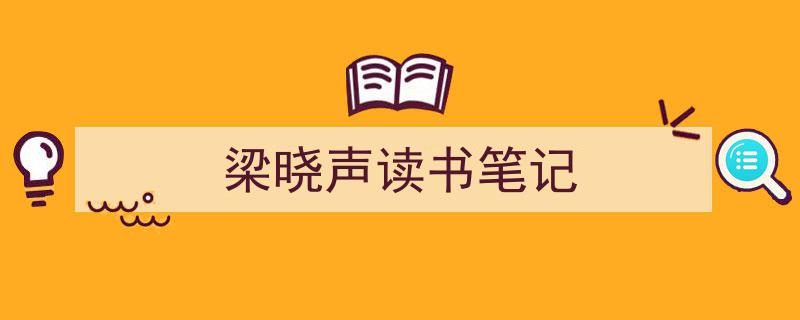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梁晓声读书笔记的作文,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事项,才能使文章既有深度又不失条理:
1. "明确核心主题与范围 (Clarify Core Theme and Scope):" "选择焦点:" 梁晓声的作品丰富多样,涉及知青、改革、家庭、人性等多个方面。你需要明确这篇读书笔记聚焦于他的哪部(或哪些)作品,或者哪个核心主题(例如,他对知识分子的思考、他对底层人民的关怀、他的时代记忆等)。 "界定范围:" 是针对某一部小说(如《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雪城》、《浮城志》),还是他的某个系列作品,或是他作为一个整体的写作风格和思想?清晰的界定能让你的文章更有针对性。
2. "深入阅读与理解 (Deep Reading and Comprehension):" "抓住关键点:" 仔细阅读选定的作品,找出梁晓声在书中探讨的核心问题、塑造的重要人物形象、运用的典型情节或象征意象。 "理解思想内涵:" 思考梁晓声通过作品想要表达什么?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有哪些看法?他的观点和情感是什么?这是读书笔记的灵魂。 "结合时代背景:" 梁晓声的创作与中国的巨大社会变革紧密相连。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
梁晓声:以平常心写平凡人
“皮皮,皮皮,我们开会啦。”老人披上一件衣服,走到书桌前,轻轻唤着一只活泼的卷毛犬。
春末的北京,日光渐长,北京西二旗附近的一个寻常小区,柳色青青,春花烂漫。作家梁晓声就住在这里。这处住所,曾在梁晓声的散文《兄长》中被提及,是他多年前为患精神疾病的哥哥购置的。这个春天,《兄长》被收录进梁晓声的散文集《小人物走过大时代》,还是集子的首篇。
梁晓声写作的房间向阳,书桌不大,上面摆着几叠纸、四五盒铅笔和一包香烟。书桌旁有一张古朴的藤椅,那是梁晓声的爱犬“皮皮”陪伴主人的专属位置。书桌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半米高的托尔斯泰画像。
“作家是一种情怀职业,托尔斯泰为所有人写作,我愿意跟随在他的后面。”梁晓声端坐在书桌前,久久凝望着画像。
与新中国同龄的梁晓声,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个工人家庭。十几岁时,梁晓声阅读了大量俄国文学作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在他内心深处留下深刻印记。高中毕业后,梁晓声在北大荒度过了七年知青岁月,这段经历成为其日后创作的重要源泉。1977年,梁晓声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之余完全沉浸在读书与写作的世界中。后来,他凭借《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年轮》等一系列作品,成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
2010年,耳顺之年的梁晓声开始了长篇小说《人世间》的创作。抱着“好好写一部作品,向文学致敬”的朴素心愿,梁晓声每日坚持在书案前写作10小时左右。其间,日益加重的颈椎病不断纠缠着长期伏案工作的他。写到下部时,梁晓声确诊胃癌,为保证创作顺利进行,他选择保守治疗。2019年,70岁的梁晓声凭借该作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今年,这部115万字的作品经改编登上电视荧屏,引发追剧热潮。
这个春天,梁晓声特别忙,除了配合电视剧《人世间》的宣传,还相继出版了两本新作——散文集《小人物走过大时代》和长篇小说《中文桃李》。这棵“中国文坛常青树”,仍在开枝散叶、结出新的果实。
对于写作,梁晓声始终怀有一种理念,即“自我”并非永远挖不到底的一口深井。“作为作家,如果写作已经与其人生发生了密切、长久的关系,那么他的目光就应该更多地关注他者,他的笔一定要更多地写他者的人生和命运。”正因如此,梁晓声在创作中塑造了大量“他者”形象。从兄长到知青好友,从邻里发小到市井百姓……在梁晓声众多对他者的描摹中,时常可见“小人物”的身影。在散文集《小人物走过大时代》的后记中,梁晓声写道:“我之散文,自然也有不少写自己情感、情愫、情怀、情调和情绪的篇章,但更多却是写他者的——那些平凡却又引起我关注的他者。”
回收废品的小贩、买股票亏了钱的村妇、加班累病的年轻人……当被问及为何会如此关注这些平凡的他者时,梁晓声坦言,他对这些人的记录,近乎一种本能。“有时只是在路边见到,我就写下他们的故事。”同时,梁晓声也愿意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为朋友们多签几本书,帮老人多背一斤茶叶,类似的事情在梁晓声的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
“我的写作不必再装深刻。”如今,梁晓声不再刻意选择某个题材或某类人物进行写作。他认为与电影、音乐不同,文学本身不是一件关于技巧的事情。“文学一定要以寻常心来看待。”在梁晓声看来,文学创作好比包子铺里的面点师日复一日地做着包子,只为让顾客吃饱,又像是司机勤勤恳恳地接单、开车,大家都是在做好自己的工作。“用文字用故事展示人性中的真善美,让读者看完后能记住一些道理,这就够了。”
在电视剧《人世间》中,梁晓声客串一位法官。宣读判决书时,布景、灯光、道具皆融为真实情景,他看着剧中的周秉昆,想起其原型人物——自己过世的弟弟,不禁红了眼眶。在其长篇小说《中文桃李》中,也出现了“梁晓声”的身影。书中,梁晓声以自己在大学执教过程中与学生们的接触和见闻为基础,讲述了80后中文系大学生成长中的彷徨与坚守。在小说接近结尾处,梁晓声为“作家梁晓声”准备了一场签售会,并借小说主人公李晓东之口评价讲座为“老生常谈,太脱离现实,作家不解愁滋味”。
而现实中的梁晓声,仍在不断了解和记录青年人的所思所想,向大量文学青年伸出温暖有力之手。在北京语言大学执教时,梁晓声喜欢带着学生们阅读作品,让学生从文本中感受文学的力量。他与自己的研究生有一个名叫“梁师亦友”的微信群,每年还会与毕业的学生们聚会、聊天。4月,首届“梁晓声青年文学奖”颁奖,梁晓声向获奖作者赠送了签名版长篇小说《人世间》。“年轻的感觉真好,年轻人写的文学永远是具有最大可读性的文学!”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梁晓声感叹道。
“在通常年代,文学的底色应该是人间的四月天。”谈及自己的文学观,梁晓声用林徽因的诗概括:“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在文学的园林中,“一树一树的花”有先烈们的红色文学,也有鲁迅的投枪匕首,有刺玫,也有巨大的仙人掌,花开种种,皆为景观。
采访中途,梁晓声的一位毕业生带着厚厚一摞书前来拜访,梁晓声便熟练地一本本签了起来。爱犬皮皮伏在一旁的藤椅上,黑亮的双眸凝注着主人忙碌的笔尖。窗外,春光和暖,繁花正盛。
本文作者:郝泽华、谢俊彦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
来源: 东大街5号
梁晓声随笔集《不装深刻》:被生活淹没,文学就是他的呼吸
林林总总,记得梁晓声的许多样子。年轻时他细瘦、好读书,远远看去就像一个“惊叹号”。当他抱膝蹲在校园篮球架下看热闹的时候,这个“惊叹号”就把自己“折叠”起来了。其实,眼前的热闹与他的眼神无关,他的生活在别处。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在同一个学校——哈尔滨第29中学念书,那时我初三,他初一。学校是一栋简朴的三层红砖楼,在道里区抚顺街,街两边都是灰突突的平房。据说,抚顺街原是一条土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军车、坦克常在这里张牙舞爪地通过,老百姓们恨之入骨,入夜常在路上搞些陷阱,弄得车辆七仰八翻,日本军队头破血流。无奈,伪政府便运来许多不规则的大石头砌成路基,上面再铺上两条窄窄的水泥道。不过,我和晓声上学走的是相对的方向,他家住的是下坎,即地势较低的一大片贫民区,人称“地德里”,俗称“偏脸子”。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偏脸子”这个古怪的地名是怎样叫出来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这里太穷,老百姓见缝插针,搭个土坯房或偏厦子房,就算脸面了。在第29中学,我和晓声同校一年,但相互不认识。再见面,已是知青时代。当时,威名赫赫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多次办过有关新闻写作、文学创作之类的知青学习班,各师团许多青年才俊被吸收进来参加学习,晓声也来参加过。当时我已从基层调入兵团政治部,因为发表了一些诗作,便常到学习班去看看。和晓声聊起来,才知道是哈尔滨老乡,初中且在一个母校,关系自然就较为亲近了。有一年,我去黑河的一师一团搞调研,特意去团部看望晓声,那时我们都穿着“兵团服”,他的脚上却是一双在知青中很流行的黑条纹、有松紧的北京布鞋,显见他的生活已有了改善。晓声告诉我,他在团部的主要任务是为宣传队写节目,快板书、三句半、朗诵词之类。我们一边散步一边聊,我发现,那时晓声就对文学十分痴迷,反正聊到哪儿他都会拐回来,唯一的主题就是他的命根子——文学。多年以后,看到晓声的小说不断地涌现。下乡之初,一封家信就能引爆全宿舍知青的失声痛哭,长时间泡在这样的情境里,再加上从小经历的清苦家境,这一切把晓声全然淹没,那颗敏感的心自然无法平静。他几乎是本能的——从那片充满苦难和血性的生活大海中探出头来,文学就成了他顽强的呼吸。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他的呼吸。如今,翻读他的《不装深刻》,感受到的,依然是晓声从“偏脸子”、从北大荒、从读大学开始的激烈而执着的呼吸,透着他的深情和悟道。正如封面印着他的一句话:“活到今天,我的一个清醒是,再也不装深刻了。”我以为,这确是一个作家的“清醒”,正如歌德所说:“生活就是上帝的作坊,任何艺术创作都无法超越生活本身。”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有源泉才能源远流长,这是千古不灭的真理。众所周知,从改革开放伊始到世纪之交的那些年,由于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和影响,文学界出现了大量以“反思”为主题的作品,也被称为五四运动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以《班主任》《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很多优秀作品,因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和思想锋芒而广为传颂,甚至走到思想界的前头,《人民文学》等文学类刊物发行达到上百万册。文学,对全社会突破僵化的思想樊篱、拓展改革开放之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直面现实、发声先锐、启迪蒙昧,成为作家普遍的追求。但事物的发展常常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当作家特别执着于表达“先知先觉”“思想深刻”之后,文学的母体——即生活本身却被淡化了,作品的人物形象和艺术魅力也被大大弱化了,它们好似成了某种“工具”,成了作者手中的“真理放大器”。它们被制作出来,只是为了传递作者的“深刻”。故而许多评论家给这类作品下了一个结论:“思想大于形象。”在文学界举办的某一次研讨会上,我曾说,我们拿出时间来读一部文学作品,要的是一种感动的情绪、一次审美的体验、一段难忘的经历。只要感动了读者,阅读就是艺术享受了!至于作品的思考是否深刻,那是更进一步的、更高的要求。在我看来,梁晓声的作品一直保持着来自生活的底色,如同“人世间”的底层,如同“偏脸子”父老乡亲给予他的喜怒哀乐。在《不装深刻》中,他以笔记的方式,谈论了古今中外很多文学经典的阅读感受。让我惊讶的是,从文中可以看到,在青少年时代,他的读书清单与我的阅读范畴,大体是相同的。完全可以想见,在同一所中学就读的时候,在各自的家中,在北大荒的知青大宿舍里,在同一时间,我俩翻开的可能就是同一本书!因为那个封闭匮乏的时代,只有这些书。我们甚至还要深深记住那个时代,证明文明不死、文化不死、文学不死,灵魂不死。不过,从书中能够看到,自晓声进入大学教书,他的阅读就是“拿来主义”了,出于终生爱好也出于职业需要,他把中国和欧洲各国的浩繁书坛几乎深耕了一遍。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地道的“享乐主义”——因为我一直认为,阅读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有书在手,知识多多,古今中外都在一掌之中,就像猫有了九条命。故而我写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书籍做灵魂的枕头,人的一生就是个闲逛。”翻读《不装深刻》,几乎把我所有的阅读记忆都牵回来了。比如《浮士德》,宁可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也要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爱到疯狂而不能得的莎乐美,终于设法砍下所爱之人的头,从而留下一句名言:“现在,我终于可以吻你高贵的唇了。”这让我不禁想起曾倾倒整个罗马帝国的那位埃及妖后,有史家称:“如果她的鼻子长得短一点,欧洲的版图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总之,文学经典留给人类的不仅仅是伊甸园,还有道义、选择、警训和梦想,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文学给予你的王国,你就是国王。自然,史上还有浩如烟海的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普希金……还有中国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乃至曹雪芹、鲁迅、巴金、茅盾,等等。我们从小就受着这些巨星的照耀,引导着真善美的追求,就像我们每次听《黄河大合唱》都热血沸腾、无比激动,我们的灵魂该是怎样的昂扬和明亮啊!数字时代到来了,说到底,它就是计算时间成本的时代。时光一如既往,均速前进,是我们在闪变的数码列阵中徘徊或飞驰。但是请别忘记,我们拥有一个风光旖旎的精神家园,那就是书籍。人类共同价值、民族自强精神,都在源远流长的文化经典中得以传续和弘扬。那就让我们重读经典吧!经典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总结,更是人类精神最崇高的呼吸。人生在世,从始至终如同走了一个环形道,而阅读就是你的生命半径,半径愈大,走得愈远。那么,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一切都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壮丽风光,而经典就是敲门砖。年轻人尤其要记住的是,金钱每时每刻都在更换自己的主人,只有知识越攒越多且不会丢失。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阿里巴巴山洞,阅读经典就是在寻找钥匙。文/蒋 巍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