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精心挑选《哈姆雷特okt观后感》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02 18: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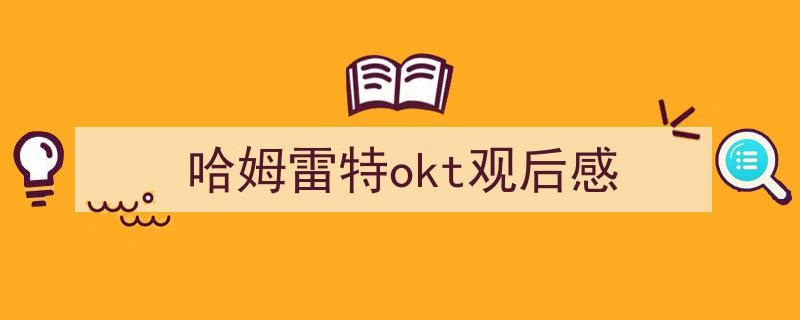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哈姆雷特(Okt版本或其他版本,这里假设指某个特定版本,如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版,或您观看的具体版本)的观后感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
1. "明确观看的具体版本 (Clarify the Specific Production):" "开头点明:" 在文章开头,清晰地说明你观看的是哪个版本的《哈姆雷特》,例如“我观看了XX剧院(或XX演员)主演的《哈姆雷特》,这部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能让读者知道你评论的对象。 "版本特色:" 如果该版本有独特的导演理念、舞台设计、演员阵容或表演风格,这些都是你评论的重点,要结合这些特色来谈。
2. "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 (Provide Necessary Context):" "剧情梗概 (简述):" 可以简要回顾《哈姆雷特》的核心剧情,特别是与观看的版本相关的部分,帮助不熟悉原著的读者理解你的评论点。但注意不要过多复述,重点是引出你的观后感受。 "理解复杂性:" 《哈姆雷特》本身就是一个复杂深刻的作品,涉及复仇、疯狂、道德困境、存在主义思考等。表明你理解这些核心主题,是进行深入评论的基础。
3. "深入分析关键元素 (Analyze Key Elements):" 这是观后感的核心部分。
比起那些意旨含糊的哈姆雷特 OKT版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2014年借戏剧奥林匹克之机,立陶宛OKT剧院版《哈姆雷特》来京演出两场,在事先并未蓄积广泛期待的前提下,获如潮好评。故此,该剧在3月再度北京演出,情势便今非昔比:不少遗憾错过前年演出的观众,满怀期待步入剧场;而当他们散戏而归时,对“该剧是否如预期般优秀”的评判,也出现了不再仿似前年的参差不齐。
好坏之见,本属主观,不必强求统一。也应承认,该剧此次从前年演出的小剧场国话先锋剧场移师大剧场解放军歌剧院,确实对其舞台冲击力有所分散与削弱。但作为一名在该剧前年演出后就通过各种渠道力荐、今年又入剧场“二刷”的观众,我私以为,产生参差观感的原因可能更多在于,对于“当我们在说OKT版《哈姆雷特》好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这一问题,其实我们并未真正厘清。
9张化妆台的使用
妙在未与原著皮肉分离
能够基本达成共识的是,OKT版《哈姆雷特》在微观层面,即对具体场景的原著解构与舞台再建构,确实具备令人刮目的高超水平。创作者通过对全剧舞美的核心元素,即那9张化妆台千姿百态的排列组合,别出机杼地呈现出了原著的各大场景,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创作者的舞台化呈现,并未与原著皮肉分离,反而丝丝入扣,让观众由衷惊叹“对,《哈姆雷特》就该是这副样子!”
举例而言:原著第一幕第二场,哈姆雷特与叔父(即新王)、母亲等人齐聚一堂,国王发表讲话,请诸君放下对旧王即哈姆雷特父亲骤亡的悲戚,拥戴自己继位。在不少版本中,创作者都会将这场戏直接呈现为堂皇的宴会,国王道貌岸然,哈姆雷特愤愤不平,席间暗流涌动。而OKT版《哈姆雷特》也有类似的处理——灯光大亮,化妆台横作一排,众人背对观众面对镜子,唯有国王站于台口发表讲话。但OKT版《哈姆雷特》妙就妙在,国王已将同样的台词用不同的方式“提前”表演了一遍——彼时除化妆台上的日光灯管惨淡发亮外,一片漆黑,国王一人歇斯底里地将化妆台拼成横排,口中念念有词,正是那段劝诸君弃旧喜新的说辞——国王人前故作威严人后惴惴不安,他需要在宴会前自我练习,将自责恐惧转换为无谓从容。化妆台变身宴会桌,得舞台形式之幻化;一文两用展现一人两面,切中原著内容之肯綮。
上半场追问“是否要暴力”
下半场展现“确实要暴力”
OKT版《哈姆雷特》更为惊为天人之处还不在于微观层面,而在于其于宏观层面对原著整体有着独辟蹊径的解读与诠释,创作者所得已不仅“树木”,更有“树林”。
OKT版《哈姆雷特》的主题,简而言之,即是暴力。中央戏剧学院沈林教授曾细致爬梳莎翁《哈姆雷特》原著的素材母本,得出结论,“一个野蛮时代血亲复仇的故事,要以符合基督教伦理的方式讲述,以打动文艺复兴时的文明人。”不管OKT版《哈姆雷特》的创作者对这一结论是否了解,至少他们的慧眼已观察到,所谓“正义战胜邪恶”的王子复仇,其实仍是一场血腥的宫廷屠杀——全剧起首还是表面平安无事的新王继位,但接下来以鬼魂之形跳出的旧王便戳破了潜藏的阴谋,按下了众人多米诺骨牌般相继殒命的按钮,直至剧终时一屋死尸全部投奔了旧王最先投奔的世界。于是在OKT版《哈姆雷特》中,新王与旧王可以是同一人在两面镜中的不同形象,被复仇者可以比复仇者更为年轻英俊,而角色之间的身体冒犯则稀松平常——没有谁是真正的正义者、胜利者,“暴力即真理”。
OKT版《哈姆雷特》的上下半场中,各有一个并无台词、阴魂不散的形象:上半场是一个红鼻头的鬼魂,下半场是一只站立的硕鼠。这两个形象即可为上下半场写下注脚:鬼魂很可能即是旧王乃至众人一切心中恶念的外化,他教唆着哈姆雷特等人尽快动手,并用自己的红鼻头讪笑着众人的盲目;而硕鼠则很可能延续了原著中的戏中戏《捕鼠器》的寓意,所谓“被捕之鼠”,未尽然只指新王,甚至包括坠入复仇之网的哈姆雷特等人,总之他们最终都如老鼠一般,沦为了死神的牺牲品。
沿此思路看下去,全剧的上半场其实是在追问“是否要暴力”,而下半场则在展现“确实要暴力”。原著中的名句“生存还是死亡”,在上下半场临近末尾各用不同的方式呈现了一遍:上半场“生存还是死亡”出现的时序与原著基本相同,但与原著不同的是,众人站在自语的哈姆雷特的侧后方,仿佛此刻他们就是哈姆雷特脑中的幻象,哈姆雷特对“生存还是死亡”态度尚在犹疑;而至全剧末尾,赤裸上身、一身血污的哈姆雷特在众人的死尸前,再度高喊出“生存还是死亡”,此时的他已然暴戾得坚决。创作者对哈姆雷特关于“生存还是死亡”态度转变的呈现,让原著这句素来神秘莫测的名言,成为了OKT版《哈姆雷特》的点睛之笔。
被所有人共同谋杀的奥菲利亚
奥菲利亚是解读OKT版《哈姆雷特》的关键之一。她首次登场,即手捧花朵,在化妆台上沿前行,这与原著中她疯癫后采撷花朵、攀援树枝,以至落水溺亡形成互文——奥菲利亚一出场,就已奔向死亡。确实,奥菲利亚是原著中最为可怜的牺牲品,她从未加害他人,却死在所有人前面;她的死本质上绝非意外,而是所有人共同参与的谋杀。该版本中,哥哥雷欧提斯对她的“忠告”仿若性骚扰,从旁窥视她的父亲波洛涅斯将象征贞洁的白裙熨好穿在她身上,更不用提新王王后躲在化妆台后窥伺奥菲利亚能否套出哈姆雷特的所思所想——在所有人眼中,最不重要的是奥菲利亚的天性与爱情,她只是他们股掌间的傀儡与棋子。由此看来,即便哈姆雷特用“我没有爱过你”这样的语言暴力打碎了奥菲利亚的心,但正如该版本中所呈现的,他对奥菲利亚自陈是个没用的人,将心中的悲恸挣扎化为一句“去尼姑庵吧”的劝告,以及尔后与奥菲利亚深情一吻,都表明在奥菲利亚的悲剧中,仅哈姆雷特一人,还对她心存善念与怜惜。
该版本中,奥菲利亚象征性地溺亡了两次:第二次是在全剧临近末尾,众人先后殒命之时,她被王后喷出的一口水结束了生命。第一次是她被派去试探哈姆雷特之前,她被众人托至化妆台上沿,蹑足前行最终失足跌落,随即化妆台后一盆水向前泼来;她在摆放有如灵堂的花簇中先所有人而死,众人却不以为意,甚至国王将杀死哈姆雷特的信交予吉尔登斯吞与罗森格兰兹的情节都被提前至此处,直至众人走后,奥菲利亚将她手中的花束高高抛起——上半场结束。这最终一抛,即是上半场的戏眼——奥菲利亚已死,屠戮正式开启。
涂上的白面是一种暗示
生存只是一场逢场作戏
“扮演”在OKT版《哈姆雷特》中,也是一个贯穿前后的重要意象。下半场一开场,即是原著中哈姆雷特指导伶人表演的段落,尔后,除哈姆雷特和霍拉旭外,众人涂上白面,开始演出戏中戏《捕鼠器》。而上半场,哈姆雷特也曾在新王继位的宴会上为自己涂上白面,强装喜悦;再之后,勾了黑眼圈的哈姆雷特还曾对镜自语,惊叹伶人在表演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物时全情投入。全剧末尾,所有角色落座桌前、集体殒命,除仍在世的霍拉旭,所有死者的白面都已被先后洗净,卸妆的纸巾与象征死亡的红布撒满舞台。似乎在暗示:“生存”只是一场逢场作戏,“死亡”才能使灵魂回归本真。人世就犹如用化妆台拼凑而出的化妆间,连接生死的渠道正如全剧起首,透过镜子对自己的脸孔追问:“你是谁”;而全剧末尾,白面霍拉旭将众人所坐化妆台的灯管次第关闭,又与全剧起首遥相呼应——死亡的黑暗终告降临,戏梦落幕,“此外仅余沉默而已”。
未对原著增扩一字的OKT版《哈姆雷特》,既能对原著有恰如其分的独到洞见,又能以脑洞大开的舞台语汇将其传神表达,优秀至此,实属凤毛麟角。虽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相比那些平铺直叙、意旨含糊的《哈姆雷特》,OKT版《哈姆雷特》确实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编辑:杨晶)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北京文艺网的立场,也不代表北京文艺网的价值判断。
OKT《哈姆雷特》:撕碎王子的千面
本号的宗旨是:「装逼为主,情怀为辅」。不定期更新,全凭作者主观喜好胡言乱语,书评影评乐评时评不一而足。如果尚合您的意,欢迎点击上方减负七关注。
(立陶宛OKT《哈姆雷特》中的场景)
目前为止在今年纪念莎翁逝世四百周年的演出季中,只挑了这部OKT版《哈姆雷特》来看。前些年上海已经上演过多个海外版本的《哈姆雷特》:有英国的TNT剧团、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的全球巡演、还有NTLive出品的卷福版现场录影,但这次立陶宛的OKT剧团依然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之前听说这个版本在原始剧本上做了极大程度的解构,所以我就很想看看这些英国以外的戏剧班底,能够把这一出耳熟能详的经典剧本玩出什么花样来。然而即便已经做好了大开眼界的心理准备,在观戏过程中依然被震慑得哑口无言。这部《哈姆雷特》在舞美上的巧思已经被许多人提及,诸如化妆镜的使用、色彩的隐喻、白噪音的声效等等,都无愧于顶尖水准。然而故事内核才是《哈姆雷特》的灵魂,也是四百年来戏剧人一次又一次复排、改编这部经典作品的意义,这一点上立陶宛导演Oskaras Koršunovas交出了一份非同一般的答卷。所以我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回味这部作品,才敢于落笔写下一点粗浅的看法。
(化妆镜和色彩都是戏中的重要元素)
讨论这部戏,总是绕不开那句著名的谚语: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人看到他的犹疑,有人看到他的高贵、有人看到他的深沉——这个角色之所以伟大也正是在于此。不同的导演,对哈姆雷特会有不同的诠释,但是其人物的复杂性无疑是刻画这个角色的基础。然而在OKT《哈姆雷特》中,所做却来得极其粗暴。他将一千个哈姆雷特全部撕碎,彻底剖开他作为一名王子的皮囊,只留下他作为复仇者的一面——疯狂、偏执,最终一步一步将自我毁灭。
从剧情角度来说,这版做了很大的改动。尽管台词本身没有修改(演员说的大概是立陶宛语,只能凭中文字幕来推断),但是大约一半左右的台词都被精简掉了,许多相对次要的场景也直接跳过,只留下一些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框架。剧情的顺序也被打散:新国王克劳狄斯针对哈姆雷特的阴谋被放在了戏中戏之前;奥菲莉娅投水的剧情在上半场出现了,而后在下半场又死了一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如此的改动,也是顺应了这部戏的主旨——去除那些表面文章,直指核心。如果说不熟悉《哈姆雷特》剧本的观众,很可能会看得云里雾里。而熟知剧本的观众,也会觉得不舒服——这种强大的舞台压迫感,完全打破了莎士比亚原始剧本中的古典韵味,而后被极具现代文明特征的冲突与焦虑感所代替。
(舞台上的角色们常常处于一种疯狂而偏执的心理状态)
在开场的戏中很快就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原剧本第二场戏,是克劳狄斯向群臣哀悼并宣布自己与王后结合,这一幕是十分典型的宫廷场景。而在OKT版本中,导演让饰演克劳狄斯的演员先是在独处中自言自语念出这段台词,演员,如同困兽一般在舞台上大吵大闹,独自忍受内心魔鬼的折磨与讽刺。然后他面向群臣,以国王的身份把这段台词又读了一遍。但也并不是带着国王的威严,而是疲倦、敷衍、漫不经心,毫不掩饰那种只是走走过场的态度。王后也是同样如此,原应假装一下的贞洁、善良、母爱被直接抛弃了,而是成了一个自私而不耐烦的中年女人。还有愚蠢滑头的波洛涅斯、直接被处理为同性恋的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只见复仇私欲而不见高贵威严的老国王幽灵……所有文明的外衣都被扯去,原本那些不体面的、不道德的、不能明言的、暗流涌动的、绝望偏执的东西与情绪直接被搬上台面。一场中世纪丹麦王室的宫廷阴谋,演变成人与人的互相撕咬。
所以这里让我想到一个疑问:在《哈姆雷特》中,人物之间究竟有没有感情?
首先是哈姆雷特/父亲/母亲/叔叔的四角关系。故事源于叔叔对自己国王兄长的谋杀,从而继承了王位,并且在尸骨未寒之际娶了嫂子。而后老国王的幽灵现身,将真相告诉了哈姆雷特,并指引他去复仇。其中,哈姆雷特与父亲、与母亲、老国王与王后、新国王与王后之间的感情都是值得探讨的。但无论莎氏原意如何,在OKT的舞台上,这些血亲之间只留下赤裸裸的欲望。老国王一出场就死死地掐住了哈姆雷特的脖子,而王后也对哈姆雷特毫无关怀之心,目睹他陷入疯狂后,只想尽早拜托他。而新国王和王后的“床戏”更是精彩,尤其是王后一身SM装束,堪称对文明的无情嘲弄——这些本应互相敬爱的王室血亲们,每天以冠冕堂皇的伪善相处,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自相残杀,动物本能,似乎比善与爱来得更普世一些。
(哈姆雷特与母亲对质的时候再次看到了父亲的亡魂)
原剧本中关于哈姆雷特和奥菲莉娅之间的爱情同样是十分暧昧不清的。哈姆雷特声称自己爱过她,然而从剧本的开始到结束,他并没有做出过什么真正表明自己爱意的事情。最后所谓的决斗,给人更多的感觉是荒诞而不是敬佩。所以这份爱情是否成立,值得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而奥菲莉娅对哈姆雷特的感情也带有一种无知而懵懂的气息。外界轻易操纵了她的感情,将其变为一个没有灵魂的角色,直到自杀才得以解脱。立陶宛导演在舞台上放大了这一角色。她刚出场的时候,穿着一袭蓝衣,这也是舞台上唯一一抹除了黑白红的色彩,动作和台词设计也极具鲜明的少女个性。然而蓝衣很快被褪下。之后她变得更美了,越来越美,被花团簇拥、被众人关注,然而这份美背后所代表的天真、贞洁却显得刺眼。英文中的innocence能更为准确地形容这一角色:清白、无辜、同时也是无知的。她压根不懂什么是爱,却反而成全了一种纯粹。
之前提到,这次导演特意安排奥菲莉娅在舞台上死了两次:第一次发生在上半场的结尾,她摇摇晃晃走过化妆台摆成的危道,最后坠落(舞台上喷出水花作为象征)。第二次则是在下半场,说了一堆疯言疯语后,被王后一杯水泼在脸上,再一次地“死”了。在她坐在花架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在莎翁原剧中,奥菲莉娅的死亡方式像极了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纳西索斯。这位美少年对自己在水中的倒影陷入了迷恋,最终投水而死。他既是美的象征与化身,也代表着对美的极端而偏执的追求。当我们谈论美的时候,习惯于附加一些品质使其崇高化,否则美丽本身会被认为是苍白空洞的,成为一种脆弱易碎的东西,遭人嫉妒并攻击的,最终化为梦幻泡影。这个世界容不下这样的美丽。所以奥菲莉娅和纳西索斯一样,死亡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被花团簇拥却眼神空洞的奥菲莉娅)
所以奥菲莉娅也好,哈姆雷特也好,或者剧中的其他核心角色。所有人都陷入了自己的捕鼠器中,所有人都在打造自己的绞刑架,走入各自的宿命。当你在设计别人之时,殊不知是在安排自己的命运。就在原剧本中,哈姆雷特设计了一场戏中之戏,也是是整个剧情最为关键之处。他导演着一群伶人,把叔父谋杀老国王并勾搭兄嫂的剧情在大庭广众之下上演了一遍,将畏罪的叔父吓得落荒而逃——这场戏的意义不仅是从叔父的表情变化中寻找谋杀的确凿证据,更是意在心理上对罪人进行精神折磨,从而满足自己的复仇心理。在OKT版中,导演将这种气氛推向了极致。没有伶人上台,原本属于伶人的台词直接从国王和王后这两个罪人口中念出来。但与此同时,哈姆雷特和奥菲莉娅也张嘴用口型读出了所有这些台词——导演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这宿命的隐喻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除此以外,导演还加了很多象征符号,其中颇有一些实在难以准确解读,譬如奥菲莉娅刚出场时显著的日本文化特征、上半场的黑色幽魂、以及被霍雷肖继承去的幽魂的红鼻子。只是符号太过纷杂缭乱,似乎有表达欲过剩的嫌疑,不仅观众们难以消化,也让表演本身有些许失衡。
(戏中戏的场景)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部戏依然足够优秀到让人在惊叹舞台奇观之余能够被它的内核深深打动。我记得观戏过程中,其中有一个场景让我非常不适。在那场戏中,舞台两侧的射灯经过45度角放置的化妆镜的反射直接照向观众席,其亮度之高,刺得人难以睁眼。从单纯的话剧表演来说,这显然是舞台上的大忌。作为一部在舞美设计上花了极大心思的戏,我不认为这是剧组的无心之失,很大可能上是蓄意为之。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观众?是向观众发起挑战?还是质询或者拷问?
我想这就是OKT剧团根据自己的理解,从四百年的剧本中挖掘出来的最核心的问题,并在最开始就由演员们在镜子前点破——你是谁?我们通常记得自己社会身份,而忘记了身为人类最本质的属性。舞台上的那些疯狂与偏执,与其说是批评,更像是为了提醒并且证明这种偏执病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即便我们以文明的名义建立起一种文化符号体系来掩饰自我,但是偏执精神始终根植于人类的骨子里——而这种偏执精神恰恰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必要方式,从而不被自己建构起的幻象所蒙蔽。这套文明体系毫无疑问给了我们安全感,但是有的时候,囿于安全感,会是一件危险而可怕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或崇高或纯粹的东西,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无可挽回的毁灭。
所以说,生存还是毁灭,这真是个问题。
(霍雷肖最终成了福廷布拉斯)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