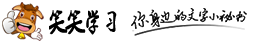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怎么写《聋哑读书笔记》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02 20:59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写聋哑读书笔记作文时应注意的事项的作文:
"点亮文字之光:撰写聋哑读书笔记的注意事项"
阅读,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而读书笔记,则是深化理解、沉淀思考的基石。对于聋哑朋友们而言,阅读可能需要克服额外的障碍,但通过精心撰写的读书笔记,更能将文字的力量内化于心,构建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那么,在为聋哑朋友撰写或指导他们撰写读书笔记时,应注意哪些事项呢?
"一、 关注内容理解,而非形式束缚"
首要原则是"以理解内容为核心"。笔记的最终目的是帮助读者巩固记忆、梳理思路、激发思考。因此,无论是手写、打字还是使用其他辅助沟通方式,都应优先保证对书籍内容的准确把握。切勿为了追求某种“标准格式”或“华丽辞藻”而牺牲了对文本意义的理解。笔记的形式应服务于内容,而非反过来。可以采用思维导图、表格、关键词、句子摘录等多种灵活形式,只要能有效呈现个人理解和思考即可。
"二、 注重个性化表达,尊重独特视角"
每个人的阅读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聋哑朋友在阅读时,其感受、联想和思考方式可能与听人有所不同,这同样是宝贵的财富。读书笔记应鼓励他们"真实地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而不是套用固定的模板或他人的观点。尊重他们的个人理解和情感体验,允许笔记
走近特教学校中的听障学生:有一种“消失”让人欣慰,有一种“失业”令人自豪
课间操,听障学生在玩耍打闹(2月23日摄)。(记者魏培全 摄)
文|《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弘毅
当生命的“耳机”被关闭,他们如何被重新“点亮”?
在福建莆田市特殊教育学校,有一群听障孩子,正在爱的鼓励下,尝试着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更值得欣喜的是,随着医学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如今的听障学生正在逐渐“消失”。
漫长的“点亮”过程
走进莆田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校园,远远地就能听到听障部的教室中传来“咿咿呀呀”的读书声。
这是一堂小学语文课,学习的是李白的《静夜思》。在外人听来,听障学生们发出的声音单调、毫无意义,但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老师却可以从中觉察出学生们细微的进步。哪怕孩子们在发音中分清了两个声母的区别,都会立即得到老师一个热情的“大拇指”——这是师生交流中最常见的一个手势,表示“很好”。
蔡黎萍老师已经在特教岗位上工作了近30年,送走了20多茬毕业生。她告诉记者:“和听力正常的孩子相比,听障儿童少了一种和世界对话的工具,需要更多的爱,才能点亮他们。”
在莆田市特教学校课堂上,对听障的孩子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使用手语时,孩子们依然要在课堂上发声,老师提出的问题。
“我们不希望学生只学会手语。他们熟练使用手语以后,就容易习惯手语交流,那样会失去很多感知这个美好世界的机会,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听障’圈子里。虽然孩子们开始朗读课文的发音并不准确,但是作为老师,鼓励他们大胆发声,是帮助他们迈出人生中的重要一步。”蔡黎萍说。
付出总有回报。孩子们在老师的反复鼓励下,从刚入学时只能羞涩地发出“嗯嗯啊啊”的声音,到毕业时大部人可以大方地边打手语边用简单语言和正常人交流。就这样,他们走出自卑的阴影,让人生拥有更多可能性。
小仙(化名)是一名小学二年级的听障学生,单看外表是个阳光向上的女孩,她喜欢跳舞,每次在律动教室,总是站在第一排,认真地瞪大了眼睛学习老师的舞姿。看到老师经过,小仙也会礼貌地大声喊出“老师好”。
然而,对于听障部的20多名教师来说,看到小仙这样的孩子天真烂漫的笑脸,心底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沉重。
“一方面,作为听障学生的老师,一旦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做好很难拥有其他教师一样的成就感的准备。每次开会,当其他学校的老师在讨论自己的教研成果和优秀学生代表时,我总是想到我们的学生。由于听力和表达能力的不完整,他们在很多方面的成长进步,都比听力正常孩子慢不少,也更难顺利地融入社会。作为教师,我们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能够拥有一个尽量更好的人生。”莆田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劲松说。
另一方面,老师们心里十分清楚,听障学生们还小,他们自己并不完全清楚命运给他们开了个多么残酷的玩笑。进入社会后,很多职业的大门不会向他们敞开,在未来的人生中,这些孩子也会遇到更多的坎坷。作为教师,只能把这种情绪藏在心底,把阳光的一面带给孩子们。
然而,这些孩子从未被放弃。如何鼓励孩子们正视自己,接纳自己,积极阳光地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成了教学研讨会上老师们最爱讨论的话题。
“在特殊教育学校里,听障学生们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享受着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社会对特殊群体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政府在对听障学生每年的生均公用经费的拨款是正常学生的10倍。对寄宿、寄午学生伙食补助,每个月还有一定金额的交通补贴。”吴劲松说。
活出自己的精彩
在莆田特殊教育学校,听障孩子们正在爱的教育下,越来越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老师们对一个叫庄志宇的学生印象特别深刻。
庄志宇的家境并不算好,家离学校也远,所以从小学一年级便开始寄宿。从小他就显得“文静”,当同学们在玩时,他总是静静地在教室的角落里看书画画。
上高中后,大部分同学准备参加专门针对听障学生的高考,对他们来说,考上大专就是一个“天大”的梦想。有一天,庄志宇用手语告诉老师,他要考本科,而且要考西安美术学院。老师耐心地向他解释西安美术学院的招生要求,分析了考试的种种困难。特别是个别考试课程学校没有开设,需要自学。
一次次的劝说,并没有让庄志宇放弃。每一次他都坚定,他一定要考本科,考西安美术学院。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教室的灯比以前更迟熄灭了,早上很早,就可以在校园看到这位低头看书的少年。
笔记、试卷、素描、油画草稿一天天变厚,一天天变高,临近高考时,它们堆起来已经和课桌一样高了。最后庄志宇以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和文化课成绩通过西安美术学院的招考,被工艺美术专业录取,成了学弟学妹们的榜样。
今年有好几个学生找到吴劲松:“校长,我也要努力,学专业知识,考上好学校。”
在莆田市涵江区美术家协会主席邓伯元的工作室,有一位特殊的画师——听障学生吴俊青。因为对听障群体不了解,又不会手语,一开始邓伯元不想破格招收聋哑人当画师,但是每年春节这个学生都主动登门拜师,前两年邓伯元以各种理由推脱,到了第三年经不住“软磨硬泡”勉强答应,让吴俊青来画室跟班学习一两个月。
没过多久,邓伯元发现自己“小看”了吴俊青。虽然听力和表达受限,但吴俊青身上有一股愿意吃苦的劲儿,认准了一件事后,就铆足了劲做好。“他每天最早来画室打扫卫生,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最难能可贵的是,其他人觉得繁琐无聊的工笔画,俊青反而具备独特的优势。他能够摒弃一切杂念,在画室沉下心一泡就是一天,无论是造型还是线条都一丝不苟。”邓伯元说,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吴俊青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作品已在省级美术比赛中多次获奖。
同样让老师们自豪的,还有1979年出生的陈志慧。毕业后,陈志慧学习美容美发,开了一家理发店,因为手艺好,价格合理,店里客人常常爆满。
近年来,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绘画、烘焙、美容等多门职业课程,陈志慧多次应邀回校教授学弟学妹们美容美发等技能。
“只要孩子们想学,作为教师,我们都会倾力去教。我们坚信,这些课程是一把把‘钥匙’,能够帮助听障孩子们打开未来人生的更多可能。哪怕只是学到了‘皮毛’,也许在走入社会后,就能经过自己的持续学习,完全掌握这一项职业技能。”美术教师余泽芹说。
为了树立学生们的自信,每周美容课程都有一批特殊的“忠实顾客”,教师们会主动来当学生们的“实验品”。有一次,有位老师看到一位学生因为肢体残疾,手指力量不够,手艺不好,没有“顾客”,便主动坐在了他的面前,打了个手语:“就你来给我理个发。”理好头发后,老师又及时给了他一个热情的“大拇指”:“很好!”
而烘焙课堂上,每当学生们亲手制作的一炉蛋糕完成,任课老师便将“作业”发到微信群中。学校教师们在群里“接龙”,纷纷买下蛋糕,作为对孩子们的鼓励。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孩子们树立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行,让他们以后能走好人生的路。”吴劲松说。
“没想到今年招不到新生”
去年9月招生时,学校没有学生报名。通过微信宣传,给相关学校校长们打了一通电话后,老师们发现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几十年来,学校第一次招不到适龄阶段的听障学生了。
回想10多年前招生,校门囗常常排起长队。因为名额有限,学校不得不从报名学生中挑选出一部分入学,不少聋哑学生因此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如今,随着国家的发展,对残疾事业的保障力度越来越大,对残疾人越来越关爱,听障儿童的数量正在逐年下降。
“没想到今年招不到新生。”在校工作30多年的一位老师感叹。
莆市残联康复科科长黄卫国告诉记者:“过去常说‘十聋九哑’,指的是如果没有进行人工干预,聋和哑往往是相伴的。新生儿一旦不幸有先天性的聋,错过了6周岁前语言发育的最佳‘窗口期’,即便进行人工耳蜗植入,他们也很难再学会开口说话。而如果在新生儿人群中进行全面的听力筛查,及时为无法听见声音的孩子们植入人工耳蜗,他们中的多数人就可以顺利建立和这个世界的联系,这就是如今的‘十聋九不哑’。”
记者了解到,人工耳蜗植入的手术和后期康复费用加起来不低于20万元,这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在免费人工耳蜗植入普及前,一些孩子很遗憾地错过了0-6周岁的“窗口期”,导致他们无法融入正常校园,而转入了特教学校。
事实上,为了实现“十聋九不哑”,近年来国家和各地投入了不少财力。黄卫国说,近年来莆田市对符合条件的0-17岁听力残疾康复训练补助应补尽补,有效提升残疾儿童生活自理能力。对于符合免费人工耳蜗植入的儿童,多年前就已经实现“申请即可植入”。在后续的康复训练下,大部分孩子不仅听见了声音,也都学会了开口说话,他们人生从此改变了。
对于莆田市特殊教育学校而言,随着听障班的学生越来越少,听障部的老师们也面临着一个新的课题:转行去教其他类型的残疾孩子。
蔡黎萍就是其中的一位教师。这几年,随着自闭症孩子数量增加,自闭症学生比例也在逐渐上升。她和同事们也正在积极学习自闭症儿童的教育新课题。“作为特教老师,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见这群孩子,关爱这群孩子,让这群孩子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虽然这种转型对习惯了听障教学的老师们来说并不容易,但是身为校长,吴劲松认为:“即使我们失业了,需要重新出发,但是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不用学手语,可以和正常学生一样享受精彩人生,我们一样感到自豪。”
原文刊于2022年3月3日《新华每日电讯》第12版,上图为版面图。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全国首位通过国家法律资格考试的聋人:盲隔离了人与世界,聋隔离的是人与人
手语翻译提醒她:“很多人看不懂手语,你能说一说讲座的内容吗?”
在五六十双眼睛的注视下,谭婷缓缓比画着自我介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说话时音量高,咬字重,尾音有些含混不清。
她脸上一直挂着笑。尽管戴着助听器,她依然无法听见任何说话的声音,尖锐的声响传入耳内,她才能感知到一丝细微的响动。对于这个28岁的聋人女孩而言,在这里,微笑是唯一的通用语言。
这是实习律师谭婷做的第一场普法讲座。她试图用文字、口语和手语三种方式,解释一个法律问题,“高空抛物有犯罪的可能性吗?”
聋人当律师,听起来似乎有些天方夜谭。与外界沟通的障碍,将这个群体隔绝在了主流生活之外。在听人(听力健全人)看来,“聋人听不见,说不清楚话,甚至无法说话,怎么和人沟通,帮人打官司?”
这个年轻的女孩却选择了这条“艰难、未知的路”。今年,谭婷成为全国首位通过国家法律资格考试的聋人。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她要克服的困难远不止“听不见”这一件事。
备考中的谭婷,每天几乎都最后离开律所。受访者供图
“法治荒漠”
3月30日下午,重庆大渡口区残联的一间会议室里仿佛分出了楚河汉界,区隔开打手语的聋人与听人(听力健全的人)。
手语之间的交流热烈,你来我往。谭婷讲“从不同楼层丢下一颗鸡蛋”的故事。聋人们的目光聚焦在她身上,不停打着手语回应。
听人反应各异,有人的目光不停在聋人之间流转,偶尔学一个手语动作,做个往上抛的手势,一边说,“丢出去”。有人坐直身子,仰起头,读着ppt上的字,上面是《民法典》里关于高空抛物的规定。
谭婷打手语的速度越来越快,表情搭配手上动作,渐渐无暇再顾及口语,只在飞速打完一句手语时,停顿高声问大家,“对不对?”
实际上,她接收不到任何声音的回应。
几位聋人是手语普法讲座的熟面孔了。以往的讲座,谭婷都会收到反馈,“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是违法的。”
这一次,一位聋人上前拉住她,兴奋地比画。告诉她,“生活中见到很多高空抛物,但他们完全不知道,高空抛物是违法的,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聋人获取信息似乎总是滞后许多,即便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很难触及到这些信息。一位聋人大爷手里攥着一张公交卡,谭婷打着手语问他,“没有领免费的公交爱心卡吗?”大爷面露疑惑,急切地打着手势,“什么是爱心卡?”谭婷便从包里翻出爱心卡和残疾证,一步步教他怎么办理,他咧开嘴笑,双手握拳竖起大拇指,往下弯两下。
谭婷接到过各样的咨询,聋人们不知道自己能享受哪些福利政策,比如生育补贴、残疾人补贴;遇到问题时,他们不知道应该找哪些部门求助。甚至有不少聋人问过谭婷,想离婚应该怎么做?去哪里能办理?
很难去统计,在全国,像这样的聋人有多少。“聋哑人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薄弱到一个无法形容的地步。”唐帅是谭婷所在律所里唯一会手语的听人律师,他的父母也是聋哑人,很多聋哑人喊他“唐法师”。
他看到的是,能与聋哑人无障碍沟通的律师,全国范围内寥寥无几。“聋哑人也想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参与法律生活,当他们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有门可诉,当他们触犯了法律时,可以弥补和补救。但这些对他们而言,非常非常难。”
在唐帅看来,聋哑人的圈子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远离了主流社会,他形容,这个圈子好比是法治社会里的一片荒漠。
普法讲座上,谭婷与一位聋人女孩交流。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
缺失一环的沟通
2017年,刚大学毕业的谭婷在网上看到唐帅招聘聋人助理的信息,她看过这位手语律师的报道,知道他帮助过很多聋人。
谭婷发去信息,“我能够来做点什么吗?”
当时,几乎每天都有聋人找来律所求助,发来线上咨询的聋人更是不计其数,而律所懂手语的律师只有唐帅一人,无暇顾及。其他听人律师尝试学习手语,往往今天学了几句,过几天又全忘了。
谭婷和几位聋人大学生就这样进了律所。她要做的是听人律师和聋人当事人之间的沟通桥梁。
但刚进律所,谭婷就感到了挫败。唐帅一看她打手语,便直摇头。她打的是特殊教育学校学来的“中国手语”(普通话手语),而唐帅打的是聋人圈里惯用的“自然手语”(方言手语)。
“这之间差别太大了。”唐帅说,自然手语是聋人依靠视觉进行的象形表达,而中国手语的词汇和语法是一套人为设计的体系,很多词语比画时使用的拼音字母,比如“TS”,可以代表“唐帅”,也能在不同语境里指称“泰山”“唐诗”等含义。
语法上的差异带来的歧义更甚,中国手语的语法更接近于听人的表达。譬如,你用中国手语比画“灭火”,聋人先看到灭火的动作,再看到“火”,“他可能以为火灭了,又着了。”
来咨询的聋人,只有少数人识字,发来的文字,是一串词语的组合。更多的聋人只能依靠手语,他们大多很激动,重复打着手语,“骗我,借钱,我。(我借钱给他被骗了)”。皱眉、撇嘴,喉咙不时发出声音,手势、身体动作幅度很大。谭婷打手语问他,你和他什么关系?他们会重复,“他,借钱”。
也有聋人告诉谭婷说自己被人打了,谭婷问他,什么时候被打了?他不上来,就讲一大堆事情,想到什么讲什么。
聋人的手语里涉及各种地点、人名的方言表达,谭婷很多看不懂,她不断打出自己猜测的意思,直到对方能看懂,两个人才能确认完成。
看懂一个聋人咨询的问题往往就需要几十分钟。转述给律师时,律师提醒她,漏掉了一些问题,一来一回多次,密密麻麻写了一整张纸,才能了解一个当事人大致的信息。
谭婷的法律书和记录案子的一些笔记。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
与听人律所的沟通,也让谭婷感到懊恼,“我自己知道,但我没办法说出来。”
因常年在特殊教育学校,平日里开口说话的机会少,谭婷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她的声带退化,吐字时声音含混连成一片。
很长一段时间,与正常人沟通的障碍让她陷入尴尬,去超市结账时,她看错了价格的小数位,收银员会“啪啪”拍几下收银台,台上的小物件都被震动起来。车上没有报站的字幕,她坐到了终点站,司机会冲到她面前,大吼着催她下车。
谭婷怯于开口,她听不到回应,只能从对方的神情里读出些许信息,沟通缺失了最重要的一环,她叹着气说,“盲隔离了人与世界,聋隔离的是人与人。”
初中时,一次放假回家,张口和父母说话时,她突然发现,父母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了,她口型夸张地喊爸爸妈妈,他们依然很茫然。
她一度崩溃,以为自己不能说话了。回学校后,她找到一位听人老师,张口说给他听,也读课本上的诗,老师鼓励她,以后可以多读出来。没有人真正告诉她,她的发音到底对不对,她只能使劲说,重复说,让自己保持说话。
直到有了手机,把语音翻译成文字的软件,才给了她实时的反馈。她用来练习发音,自己摸索着说,看文字翻译准确了,她便判断自己说对了。
起初翻译出来总是一串乱七八糟的文字,一个词要读上百遍、千遍,她才能看到准确的文字。纠正一些字的发音很难,现在她依然发不清楚l和N,S和SH的区别,口型相似的词语,更让她困惑,比如兔子和肚子,她只能囫囵发音。她无法判断发声音量的大小,说话总是很用力,往往感觉到嗓子肿痛,才意识到发声时用力过猛。
高冬梅律师记得,最开始哪怕谭婷说话很慢,她也只能猜出几个字,一句话需要她重复说两三遍,才能听懂。
“学习知识,会让我有安全感”
谭婷是在8岁时失去听力的。记忆里小学的教室墙上刚贴上标语,“请说普通话”,但“还没系统接触普通话,我就听不到了”。
时隔20年,谭婷关于声音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她只记得最开始是耳朵里的疼痛,慢慢听声音变得模糊了。医生诊断是中耳炎,在她的耳后和手上插上银针,治疗后情况更糟糕了,父母在耳侧大声说话,她几乎都听不见了。
父母带着她到攀枝花、昆明的大医院,医生诊断为神经性耳聋。
山村里没人知道,一个听不见声音的女孩该怎么上学,她只能辍学在家。过去一起玩捉迷藏的小伙伴,一见到她就跑了,村里人看着她,嘴巴开开合合,她“只感受到一片死寂”。事发后很长时间,女孩陷入了难以抑制的自卑情绪里,这个世界上只有她听不见?她一度以为自己是怪物。
白天父母去地里干活,弟弟去了学校,她一个人在家,翻家里的课本和字典,拼着拼音读,抄在纸上记下来,“做梦都想上学”。
再回到学校已是五年后。父母偶然得知西昌有接收聋儿的特殊教育学校,带着她去,学校只有一、二、五年级,13岁的她重读二年级。老师用手语上课,她才开始学习手语这门“第二语言”,很费劲地跟上功课。
特殊教育学校是在一所普通小学校园里,相隔一扇铁门。课间时,普通学校的学生路过,指着比手语的他们笑,长期在异样的眼光下,谭婷写道,“我们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奇怪的动物。”
学校是封闭式管理,外地孩子只能在寒暑假回家。谭婷不让父母来接,自己坐五个小时的大巴回家,老师叮嘱她,不要在外面打手语,一些坏人知道你是聋人,把你拐走了怎么办?
初中时她去了乐山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读,离家更远一点。有时候坐公交车,看到有人打手语,旁边的人会下意识紧紧捂住自己的包。
有一天,班里一位女同学没来上学,父母找来学校,谭婷才得知,女生失踪了。在公开场合打手语一度变成她的禁忌。
父母和她也只能通过文字交流。父亲只读了小学,母亲不识字,为了和她交流,母亲提出要跟着她识字,翻得皱巴巴的小学课本又派上了用场,有时候母亲学得不耐烦了,把课本丢在一边,摆手摇头,“太难了,不学了,”但过不了多久,她又会重新拿起课本,一笔一画描着字。
16岁时,谭婷在学校艺术团第一次接触到舞蹈。刚开始跳得很僵硬,同学打趣她跳起来像个机器人,她便把课间、周末都用来练习,甚至看书时也会压腿练基本功。
2009年,她被成都残疾人艺术团选中,参加了全国舞蹈比赛,还见到了跳《千手观音》的舞蹈家邰丽华。“周围的人肯定会有这样的声音,你声音都听不到,怎么去跳舞,可你看她们,还是可以跳得这么优秀。”谭婷说。
谭婷参加大学艺术团的手语舞表演。受访者供图
进入残疾人艺术团当舞蹈演员,是一条对听障人士来说已经较为成熟的路。但谭婷还是更希望能读大学,像普通人一样学习知识,以后也能从事脑力工作,“学习知识,会让我有安全感。”
考上大学时,谭婷记得,特殊教育学校旁边中学的老师很是吃惊,“聋人也能考大学吗?”谭婷说,“我们只是听不到,其他都和大家都一样,我们想做什么,也可以通过努力做到。”
成为律师
很难说清是哪个案子让谭婷决心要考法考,成为一名律师。
聋人的求助大多在下午或晚上,也有很多人在工厂打工,周日休息时发来视频,情绪都很激动。谭婷没办法独立给他们解答疑惑,等待律师答复的时间,有的聋人不肯挂断视频,脸上一直挂着很焦急的神情。遇上律师忙案子的时候,等待的时间更长。
有一次,有聋人表露出想不开的情绪,甚至有轻生念头,谭婷急得不行,但当时她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法盲,她能做的似乎只有陪他聊聊天。谭婷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她多学习一点法律知识,也许能更好地帮助他们。
经常有聋人来律所“报案”,有时是几个人,有时是几十个。谭婷记得,最多的一次来了两百多人,很多聋人抱着被子来的,他们把钱投资到一个名叫“龙盈”的公司,负责人是一位在聋哑人圈子中颇有影响力的聋人企业家。“他打着帮扶聋人的名义,告诉他们要带着大家赚钱,大家就相信他。”
谭婷与来律所求助的聋人沟通。受访者供图
律师们带着她和几位实习生,挨个向聋人收集信息和证据。她发现,很多聋人都没有保留证据的意识。她们和律师通宵整理材料,没地方住的聋人就整夜坐在律所里。
还有聋人拿着一堆照片,告诉其他聋人,自己在国外开公司,可以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只要能借钱给他,以后翻番还给他。很多聋人就相信了,哪怕自己没钱,去借钱也要借给他。来律所求助时,他们都还不明白“借”和“骗”的区别,他们只关心,“钱能要回来吗?”
涉及恋爱与婚姻方面的咨询也很多。有一个聋人向谭婷求助,他连续被网友骗婚四次,都是在网上认识的女朋友,还没见过面,对方都结婚为目的,喊他准备“彩礼钱”。等到他转钱后,对方便联系不上了。“同样的套路,他就这样被骗了四次。”
一位不识字的女性聋人,“被”嫁给一个健全人,多年来一直被家暴,她要离婚丈夫却不同意,别人告诉她可以去起诉离婚,她试了很多次,援助律师都告诉她败诉了。她找来律所,谭婷一看文件上写的是“撤诉”,谭婷问她,她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高冬梅刚接手聋人相关案件时,问过谭婷,为什么聋人容易被骗?谭婷当时的是聋人都很单纯。其实,聋人被骗都是有缘由的,“骗聋人的都是聋人。聋人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有些是因为对钱的渴望,他们找工作很难,生活很难,想快速得到钱,有的聋人则是渴望得到感情。”
谭婷说起,感觉心里很沉重,“我不知道怎么讲得让你们理解,我想为他们做些什么,这都是我学习法律的动力。”
较劲
2018年5月,谭婷和同期的4位助理下定决心备战法考,唐帅和律所律师的“魔鬼训练营”开始了。
上学期间,她们与社会之间像隔着一层屏障,灰色地带被过滤了。唐帅认为,聋人要成为律师,必须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会法律逻辑思维,“聋哑人的世界里只有两种颜色,黑与白,对与错,善与恶。我们要用很多的例子来打通他们的逻辑关,告诉她们有灰色地带存在。”
那段时间,唐帅一见谭婷,总要给她出个情景题,大多来自于他办过的案子,要求她说话作答。
高冬梅律师讲的是刑法,她把讲义用文字打在ppt上。她记得,谭婷几人当时很疑惑,犯罪的人要得到法律的惩罚,为什么律师要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谭婷想起大学时候看“杭州保姆纵火案”的新闻,不明白为什么律师要为这么残忍的人辩护,那时候她觉得“这个律师有点坏”。
高冬梅列举了很多冤假错案帮助她们理解。谭婷说,“现在能慢慢理解了,被害人的权益,犯罪嫌疑人的权益,都要保护。”
距离法考只有不到半年时间,考虑到文字讲课的进度太慢,律所的律师分别帮她们找齐刑法、民法等各种课程,让他们先自学,有不懂的地方大家再一起讨论。
听不见,谭婷只能依靠眼睛学习。要兼顾工作,凌晨五点多她便起床,抱着书在轻轨上刷题,到律所后对着电脑就是一天,有时一看到字就感觉眩晕。
下班后,谭婷继续学习,丈夫在律所做生活助理,他会借用唐帅家里的厨房做一盆凤爪,拿到地铁口摆摊,律所每个人几乎都尝过“充满爱的,特别好吃的凤爪”。
周末时,谭婷常去书店,她喜欢阅读,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样学习知识。受访者供图
到晚上十点,坐轻轨回家时,她还会抱着真题书刷题,律所离家远,他们得转四趟轻轨,担心错过站,丈夫要盯着报站的屏幕,到站喊她时,发现妻子抱着书睡着了。
第一次法考,五个人都没考过。通过法考客观题考试的只有谭婷一人,她的法考主观题成绩差了10分。
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有人决定退出这场“马拉松式”的学习。他们说越学越没有底气,学不懂;也有说过了三十岁了,要结婚了,经济压力比较大,打算先去找份工作赚钱养家。
这三年,律所里来来去去的聋人助理有三十余人,厚厚的法律教材和真题堆满办公桌,少则一个月,多则半年,桌上又空无一物。
坚持下来的只有谭婷与其他两位。唐帅记得,谭婷无数次红着眼睛来办公室找他,“说她觉得学习法律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魔咒,太难了。”后来,他一看到谭婷表情不对,马上说一句,“你想说什么我知道,不用说了,我告诉你,要放弃不可能。”
转过身,他找来谭婷的丈夫,打着手语告诉他,“你要多开导谭婷,在生活里多制造一点浪漫,她不坚持下去可惜了。”“真是和老父亲一样的。”唐帅调侃说。
其实,谭婷之前没真动过放弃的念头,但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学习,脑海里紧绷着一根弦,总有压力过大的时候。丈夫很少说些什么,只会默默地搬个凳子坐在她边上,陪着她看书。
第三次临考前,谭婷突然收到母亲确诊癌症晚期的消息,赶到成都的医院时,母亲的身上插着管子,翻个身都疼。这是谭婷第一次想放弃,她没办法离开母亲几天去参加考试。
母亲却强撑着拿手机打字,告诉她,“你必须要参加考试,你应该为自己、为社会而活,应该去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以后帮助那些底层的人。”
聋人真的能做律师吗?
实际上,在谭婷第三次法考成绩出来前,唐帅心里也没底,没有人敢打包票,聋人真的能学好法律吗?
法考成绩出来时,谭婷正在医院,她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母亲很高兴,写道,“以后要做个好律师,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作为第一个通过法考的聋人,谭婷开始受到很多关注。她收到一些在读的聋人学生的信息,“要好好学习,希望以后也学习法律,能加入这个团队”。
也有人问谭婷,“你听不到,怎么去开庭,难道要配一个手语翻译吗?”
“与其来问这个问题,不如想想,怎么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谭婷正色道,“聋人除了听,什么都能做。”
她解释,其实律师的很多工作都能在法庭外面完成,“我们是一个团队,我可以和听人律师一起办理聋人的案子,我学习了法律知识,能够更好地提供帮助。”
然而实际上,团队合作里的难题也显而易见。即使在团队里,因为听不见其他听人律师关于案情的讨论,对于案情的跟进很可能会因此滞后,她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一一沟通,填补这个“空洞”。
3月底,密集的采访找到谭婷,她忙到晚上才有时间点开手机,每天都有十几条新的好友请求,大多写着,“急事,我是聋人。”依然是婚姻与借贷相关的问题居多。
谭婷发现,由于不懂法律,等到很多聋人来律所求助时,事情已经变得很是棘手了。
3月30日傍晚,谭婷接到视频,一位聋人女生眉头紧皱,眼圈通红,不时捂着脸。不久前,女生的哥哥找到律所求助,妹妹被人强奸。家人都不懂手语,平时与女生的交流不多,直到女生生下孩子,才告诉哥哥自己的遭遇。哥哥马上去派出所报了案,这一举动吓坏了妹妹,她拒绝与家人沟通,什么都不愿意再说。
让谭婷意外的是,视频一接通,女生见到屏幕里的聋人姐姐,一下心防就卸下了。“可能是我能够站在一个聋人女孩子的角度和她沟通,并且我在律所工作,她愿意和我敞开心扉谈她的遭遇。”
谭婷才了解到,原来,事发后,女生一直遭到对方威胁,让她以为这件事情两个人都有错,她是做了见不了人的丑事,如果报警,她自己也会坐牢。
这是谭婷成为实习律师后,将全程跟进的第一个案件。唐帅告诉她,“很棘手,聋哑女孩遭到强奸的案子,几乎都错过了最佳的取证时间,缺少指证强奸的证据,很多聋哑人的案子,听他们叙述完犯罪手段,我们比他们还窝火。”
“类似这样的事情真的很多,没有人告诉过她们,遇到这些事情时,她们应该怎么做。”谭婷说,比起上庭辩护,聋人群体普遍缺乏法律和维权意识这一现状,显然更牵动着她的心。
她拍过几条普法视频,都是聋人咨询里常问的问题,解释“离婚冷静期”“重婚罪”以及“案底能不能消除”。但这样的普法视频只能辐射到很少一部分聋人, 她想用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些事,“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如果想去把它们做好,我需要更努力地学习。”
这样也被质疑,有人问唐帅,这是不是一场作秀,目的是要把谭婷打造成为律所的一个品牌。
“无稽之谈。”唐帅听到之后很“冒火”,“这不是个可以炒作的话题,也不是一个励志故事,谭婷会受到关注,是因为全国近3000万的聋哑人群体需要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
在他看来,“谭婷们”必然会出现,“现在有了聋人律师,以后也会有聋人法官、聋人检察官,甚至可能会出现专门处理聋哑人案件的法庭。到那个时候,沟通不畅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这个边缘群体形成的闭环才能被打破。”
谭婷没想那么远,她专注于眼下。继续学习法律,把口语练好,专心普法讲座和参与的每一个案子,“走一步看一步。”
“很多聋人看到我的行动,他们可能会更有勇气追求自己的梦想。”她在手机里录唱了一首歌,叫《消愁》,听不到曲调,她就用自己的声音哼唱。她最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于是可以不回头地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
文 | 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 | 李立军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