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一篇文章轻松搞定《清煤工作总结》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09 16: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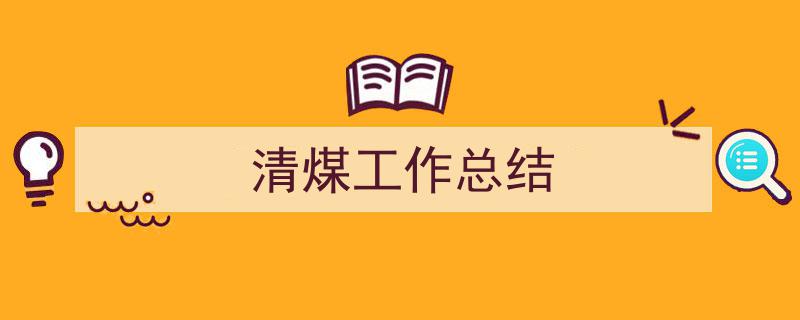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撰写一篇关于清煤工作总结的作文,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总结内容清晰、全面、有深度,并达到预期的目的(例如汇报工作、分析问题、提出改进等):
"一、 明确总结的目的和读者对象:"
"目的:" 首先要清楚这份总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向上级汇报工作进展?是为了团队内部经验分享?还是为了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不同的目的决定了总结的侧重点和语气。 "读者:" 考虑总结是写给谁看的?是领导、同事还是下属?不同的读者关注点不同,语言风格和内容的详略程度也应有所调整。例如,给领导的总结可能更侧重于结果、效率和关键问题,而给同事的总结可能更侧重于过程、经验和教训。
"二、 结构清晰,逻辑严谨:"
"标准结构:" 1. "标题:" 简洁明了,如“XX时间段清煤工作总结”或“关于XX项目清煤工作的总结报告”。 2. "引言/概述:" 简要说明总结的时间范围、工作背景、主要目的和总体评价。可以概括性地提及清煤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 "主要工作内容与过程:" "具体做了什么:" 详细描述清煤工作的具体任务、范围
煤价暴跌“砸死”煤老板:从赚两亿,到赔五亿
记者/张蕊
编辑/杨宝璐
运煤车在排队等候拉煤
最近一个月,于振文一直在考虑转行。从事煤炭生意几十年,他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被“刺激”过。从10月中下旬到11月初,短短10天之内,煤炭价格从顶峰直接被“腰斩”,他以亏损超过5亿元的代价,清空了手中囤积的几十万吨动力煤。“越来越不好做了”,他叹气道。
他并不是唯一想转行的煤老板。在2021年的这个秋季,动力煤从最高点2600元/吨跌破1300元/吨的行情,让人们经历了什么叫心惊肉跳。在深一度近期的采访中,不少煤老板表示“估计明年会更难。”包头煤炭贸易商王安平低价卖光手里的存煤后,给自己放了长假,他打算四处走走,寻找新的投资项目。
12月3日,2022年度全国煤炭交易会在山东日照举行,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交易会中长期合同的签约,首次实现了发电供热用煤全覆盖。据了解,合同中明确要求,核定能力在30万吨及以上的煤炭生产企业原则上均被纳入签订范围,而需求方要求发电供热企业除进口煤以外的用煤100%要签订中长期合同。
“这意味着,终端用户可以直接和煤矿联系购煤,省下了贸易商环节。”鄂尔多斯煤炭贸易商徐清波表示,这或许意味着,作为煤炭贸易商的“煤老板”,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
截至12月28日,煤价仍在下跌
价格暴跌,“砸”中了囤煤商
12月15日上午,于振文一早就到了办公室。他打开电脑,来自生意社的数据显示,这一天秦皇岛港5500大卡的动力煤价为1075元/吨,相较于最高位的2580元/吨,下跌了将近60%。
办公室里很清净,这和两个月前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基本上没有要煤的了。”就连手机也安静了很多,不用再随时充电。
于振文还不习惯这种落差,计算亏损成了他现在每天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作为山西一家煤炭贸易公司的“一把手”,他的工作重心是分析政策,判断煤价走向, 控制采购和销售的节奏,“在哪个价位赶紧买,哪个价位快速抛”。
这一个多月以来,于振文一直在反复复盘自己当时的操作,“政策出来之后,完全没想到价格会直接砸得这么厉害,当时想着观望一下,没有马上降价销售,吃了大亏。”他总结道。
都是不甘心在作祟。在今年国庆假期,每天找他买煤的企业和个人都很多,到假期结束时,他之前囤的所有煤已经卖光,赚了近2亿元。当时,他觉得煤价肯定还会涨,又准备了几个亿的资金,打算大干一场。
彼时,拉煤都是预付款,即便如此还不一定能买到。有时候定好的煤会被其他人高价“截胡”。于振文就碰到过“撬煤”的,原本订好的2万吨煤1550元/吨,被对方以每吨高出100元的价格拉走了。他甚至没时间生气,就又投入到下一场“抢煤”大战中。
于振文的公司有20多名业务员,他们的工作除了联系购煤的客户,还需要维护跟煤矿的关系。跟于振文公司合作的煤矿有20余家,他告诉记者,往年并不需要总跑煤矿,订多少煤,打个电话矿上就会直接发货,但今年,不跑煤矿就意味着搞不来煤,“煤矿既不会把价格定死,也不会保证你能拉到多少煤,只能根据产能来分配。”
从9月初起,涨价就变成了常态。拉煤也开始需要排队。最紧张的时候,在矿上排三天三夜都拉不到一车煤。而即使是通过招投标采购的煤,煤矿说不卖就不卖了。
“往年拉煤排一天队,就算是时间很长了。他(煤矿)不卖给我,我就只能给客户退款。”于振文告诉记者,以往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在煤价持续上涨的日子里,每天看着价格“蹭蹭蹭”往上涨,于振文觉得全身的血也“蹭蹭蹭”往头上涌。他惜售,卖出去的量一直不多。到10月中下旬,他手里的煤已经在港口囤了50万吨。“每吨100元,总价就是5000万,每吨200元,总价就是1个亿。” 有段时间,他晚上都睡不着,整宿盘算自己囤的煤能挣多少钱。
据生意社的数据显示,10月8日,环渤海动力煤的市场价1800元/吨,至10月19日,最高已涨至2600元/吨。以此计算,于振文手里的煤值近13亿。
如果不干预,煤价还会涨
在10月下旬以前,于振文的手机24小时不关,客户半夜打来电话,他也会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很忙,很累,但很兴奋。”于振文称,当时他一度以为煤价会上探至3000元/吨。
于振文称,每吨煤的运费、人工等成本加起来差不多270元,假设坑口价若是1400元,那每吨煤起码要卖到1670元,才能保证不亏。但一直以来,港口价的上涨速度远不如坑口价上涨的速度快,因此,煤老板们通常都是把煤运到港口之后囤几天,等港口价涨起来再卖。他们和客户所签的合同,也取消掉了“违约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条款,“谁也不敢承诺能多少钱给多少吨煤。”
鄂尔多斯煤炭贸易商徐清波同样表示,那段时间他在和客户签合同时,不会把价格“锁死”,一般都注明是“随行就市,以煤矿调价函为主”。
“涨价之前,煤矿都会发涨价函,我们就把涨价函发给客户,如果客户能接受新价格,合同就履行,如果接受不了,合同就不履行了。”徐清波介绍道。但如果煤价在运输过程中跌了,那么到了客户的目的地之后,对方因此拒绝收煤,这个损失也只能由煤老板自己承担。
徐清波称,如果没有行政干预,煤炭市场的价格肯定还会继续涨,他甚至看不出价格何时才能刹住车。在他看来,如今价格持续下跌是因为煤矿供应增多,“国家鼓励煤矿释放产能,产能上来了,煤价自然要下跌。”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煤炭价格短期涨幅过高,是因为需求增长快,供不应求造成的。“中国基础能源供给以煤为主,煤炭价格太高,对下游影响会比较大。”
在煤炭网分析师赵玉伟看来,每年的九十月份,本该是煤炭市场的淡季,但今年淡季不淡,反而出现大幅上涨,明显是供应不足造成的。“不管是增速还是产量,供应方的增速都大幅低于需求方。”
一组来自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我国能源需求持续快速增长,1-10月的发电量同比增长10%,其中火电增长增长达11.3%。2021年1-10月全国原煤产量33亿吨,同比增长4%,远低于同期火电发电量增速。
“很多企业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情况,在价格低位时储备不足,有需求的时候,供给又不足,价格就是这么被推高的。”赵玉伟说。
西部一家煤矿正在向外运输煤炭
“几千万、一个亿地往下掉”
转折出现在10月19日。
当天下午,国家发改委组织重点煤炭企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召开今冬明春能源保供工作机制煤炭专题座谈会,研究依法对煤炭价格实施干预措施。
看到新闻中“价格干预措施”时,于振文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想到白天以2600元/吨的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的煤价,“不甘心”还是在心里占了上风。
同日晚,国家发改委官信上连发三篇关于“整顿煤炭市场价格”的文章,于振文也看到了,但根据几十年的经验,他判断煤价还会保持上涨,不会一下子被打下来。这一观点被不少煤老板赞同,他们普遍认为“供应不足,需求还是很大”。于是,第二天上班,于振文告诉公司的销售人员,正常采购和发货,如果有煤矿有煤,可以多要一些。
然而于振文没注意到的是,当晚动力煤主力合约(即成交量最大的合约)大幅低开,很快就封死跌停。就连动力煤其余合约也全部跌停,焦炭、焦煤同样不例外。
第二天,环渤海动力煤价继续小幅下跌。彼时于振文还笃定,煤价会很快再涨起来。然而到了10月22日,环渤海5500大卡的动力煤报2350元/吨,较前一日又下跌了200元。
这一天,于振文的资金账户缩水了1个亿。虽然心痛,但他还是强压下了清库存的念头,“那时候我还觉得煤价会反弹。”他回忆道。
然而煤价却自此开启了一路下跌模式。每天看着账户资金几千万、一个亿的往下掉,于振文开始失眠,价格一跌再跌,囤的煤却卖不出去了。“没人要,大家都在观望。”
生意社的数据显示,到11月1日,环渤海5500大卡动力煤价跌至1290元/吨,较最高点已是“腰斩”。
翻覆只在几天之间,10月16日之前,客户们拿钱都买不到煤,10月19日之后,就没有人买煤了,徐清波此次侥幸全身而退,“我是直接从煤矿拉出来就卖,不囤。”他介绍道。他的经营模式是找二十余家优质煤矿签合同,然后根据客户的要求分配购煤指标,“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但利润空间低。”按照徐清波的说法,从他手里售出的煤,一吨最多也就赚20元。
但他不少朋友损失惨重,“客户一夜之间都消失了,现在只有老朋友会打电话寒暄一下,问问煤价如何。”
“此次煤价暴涨,不排除有人为炒作的嫌疑。”林伯强表示,煤炭供需关系,要从供需两端同时入手,这是解决短期矛盾的唯一办法。
10月中下旬,徐清波去了一趟包头的煤炭工业园。他发现,那里囤煤的人很多,“基本都有几万吨。”他分析,大家都想高价出,当价格开始跌的时候,需求一下子减少了,再想出手就困难了。
王安平今年赔了1000多万,此前几个月,他陆续囤了5万吨煤,平均收购价约为1500元/吨,加上运费、人工等成本,他需要卖到1800元/吨才能略有盈利,由于抢到煤不容易,他决心等个好价格。
在煤价刚开始下跌时,王安平就在第一时间以低于市场价50元的价格卖掉了手中的存煤。“如果不是跑得快,现在得多赔好几千万出去。”王安平颇为庆幸。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越往后,煤越不好卖。11月份以来,于振文和公司的业务员每天都在打无数个电话找客户,电厂招投标的时候,他们也会悉数主动投标,就这样赔着本卖,半个月后,他们卖完了囤积的煤,亏损超过5亿。
博弈新格局,煤老板出局
11月30日,西部一家煤矿下发了今年最后一次调价函,将5500大卡的动力煤调至950元/吨,这比10月17日开始执行的1370元/吨,下降了420元/吨。“此前的价格确实有些高。”该煤矿的销售经理李安和表示,最高价公布后,直接找上门的客户一下子少了50%,购买的主体变成了刚需客户,就是所谓没有库存的企业。
对于今年的煤炭市场,李安和觉得,是煤炭紧缺造成产销都不平衡。“比如一个矿井年产核定产能是330万吨,每年就只能销售330万吨。”李安和说,国家有规定,煤矿在完成每年的产能后,就不能再产,也不能再销,只能维持检修状态。目前李安和所在的公司就处于前期库存全部卖光,今年产能也已经完成的状态,“从上个月开始,就在检修设备了。”
但毫无疑问,在今年的煤炭市场上,煤矿是最大的赢家。据徐清波了解,不少煤矿在前10年亏的钱,今年1年全赚回来了。
李安和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今年煤矿都不亏,老矿机煤矿都能盈利。成本低的新矿机煤矿盈利甚至可以翻番。往年我们收支基本持平,有时候还略亏,今年不仅盈利,利润也是近几年来最好的。”由于来拉煤的煤老板都付现金,煤矿今年现金流很充裕,“往年都是承兑,把煤卖出去半年后,才能拿到钱。”
也有头疼的地方。往年这时候,李安和就已经进入了出差高峰期,不仅需要去要账,还要去谈新一年的合同。“合同基本上这时候就确定下来了。”但今年,他的客户还有不少没签订明年的供煤合同。
李安和称,这背后是煤矿与各大用煤客户之间的博弈。“有些企业还想等等,看价格能否往下压,但也有企业怕明年买不到煤,就签了合同。”李安和告诉记者,“往年我们得签合同才能把客户约束住。要是不签,心里就没底,怕第二年生产出来的煤没人要。”
12月28日,环渤海5500大卡动力煤市场价最低已经跌至860元/吨。于振文往港口发了8000吨煤,他不敢再多发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因为疫情,王安平没能走得太远。现在,他每天都在研究最近火爆异常的“元宇宙”,从概念到游戏,“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他希望在“元宇宙”这个“风口”中,能分得一杯羹。
(应受访者要求,除林伯强、赵玉伟外,其余采访对象为化名)
【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北青深一度】所有,今日已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家授权,任何第三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缘起缘灭40载石炭井矿务局
1960年年初,宁夏煤矿管理局一纸公文递到了煤炭部。事情就这么落定了——石炭井矿务局诞生。目的是很明白的,就是要在贺兰山北段和中段煤田上,搭起属于这片土地的煤炭大幕。前前后后,许多人事随之而入,原煤田建井工程公司撤销,这场属于石炭井的历史就这么开始了。谁能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
时间甩到2000年。重组如潮,石炭井矿务局摇身一变成了太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张纸又定了无数工人的命运。四十年一晃而过,有多少人来过,有多少事被时间搁浅,最后都只剩些许字迹。父辈们一身煤灰走来,又转身在别处落脚。早年的热闹如今只留下一些标签,谁还记得当年人声鼎沸,谁又能说得清他们真正经历了什么?
说起矿区,三块已经投产,一个还等着。东西横躺了四十多公里,南北拉开最多二十六公里,面积大得吓人。煤呢?真正算得上的含煤地块有九十多平方公里,到头来能采的不到一半。名单翻开,石炭井、李家沟、马莲滩、呼鲁斯太、汝箕沟,个头各不同。
石炭井最初气势正盛,南北拉起十来公里宽,东西不过两公里,煤挺精也挺杂。李家沟卡在东边六公里,1984年因为地质太乱关停了。三矿,资源枯竭,提前谢幕。现在还剩下什么?有的时候,真说不上来。
呼鲁斯太更靠西,地界都探到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去。三十六平方公里煤田,本该大有作为,实际就乌兰井田一家归石炭井管。六个井田,剩的都还只是底色。汝箕沟跟过山车似的,越往西越窄,煤质也不是一家独优。白芨沟、大峰名下归属上写着石炭井,唯有汝箕沟井田是宁夏区里自己玩的。旁的地方或团队自己凑钱开点小法,根据公开数据,这一带井田性质、产权相当混乱。
白芨沟开了十五年,被改名卫东矿,马莲滩暂时搁那儿。零零碎碎的小煤窑在浅煤赶早,主要供大武口电厂,正儿八经的开发还没开始。我说这些,是因为矿区划定很漂亮,但实际谁拿下的,谁还在犹豫,都说不清。
职工来源讲起来更是绕,人来人往,队伍像是没尽头。1958年底,大同矿务局干脆派了几百人来,工人和干部都有,不分昼夜赶路先安顿在渤力海的土坯房里。那些年条件苦?苦得都不想再细说。
一年后,徐州、大同、兰州、石嘴山一共搬来了两百多干部、三百多工人。大炼钢铁那年,连带了一千四百名农民工一块过来。招工横幅还没落地,平罗火车站聚满了来自天南地北的自流人员,三千多人。有人说,这种招法杂乱无章,人员素质起落不定。我倒觉得,不经历混沌哪看得到清明。
山东济南军区来了两百官兵。到了1965年,东北三大煤局和各大矿校也有动作,成建制的队伍整齐划一地开赴石炭井,七千五百多人拖家带口。学生分配来三百多,孩子气还没散,安全帽压得头痒。听说有人如今还念叨着那时候的大院、同学、夜灯,人生轨迹早定死了。
1966年辽宁本溪和阜新齐发力,两千九百名工人开拔进一矿。河南也搞了回轮换工,一千八百人,工农一肩挑。军人转业壳子脱掉,被时代捡去当了工人,也许有个别人心里是不乐意的。三矿还专门从“西海固”捞了两百名“老三届”,想着年轻人有劲头。结果呢,也没见谁冲出头。天津市第四人民医院连夜南下,一口气把530口人全搬过去,医院改了名,从此宣传里天天挂着“服务煤矿”四个金字。
不断补充的还有宁夏、河南招的“亦工亦农”(有的说是“半农半工”),有一说一,这帮人穿得土,干得愣,谁管?没人管。
矿区扩张快,人员调配更快。不消十七年,井矿一座座造起来,还顺带建了个露天煤矿,还有大武口洗煤厂,烟煤、焦精煤、太西煤一样不落。有人总结,石炭井成了西北老二,只输铜川。全国看,有没有前例?没有。整个流程国家只投了五个亿,别人得花二十。真有点奇迹的意思。
1989年,石炭井矿务局冲进全国前五百强工业企业榜,排299。又过几年,九零年建局三十周年大会热闹非凡,王福林局长现场宣布“生产煤炭10252万吨,掘进129万米,创了24.85亿工业产值,上缴利税2.6亿。”听到这些数据,多少人心里头还是有点发麻的。
大会还给两千多名老职工颁了证书,说他们三十年不离不弃。大家都说风光,实际上谁心里能真的高兴?有人觉得自己白白奉献三十年,工资却不涨。也有人觉得建设石炭井的一代最苦、最光荣。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或许也分人。
1995年,石炭井前进到全国产业榜第213名。跟当年比,似乎蒸蒸日上,实则人心涣散,有人觉得待遇更好了,发展危机却也从另一个方向逼近。时代变了,年轻人多想离开。三十年风雨,只剩企业分布示意图挂在墙上冷冷地提醒,“这就是曾经我们的全部?”
细看矿区的分布,不难发现规划永远领先于现实。每个区块都有自己的难题,地质搞不定的直接关门,资源枯竭的再多投入也无力回天。乌兰井田算是幸运,有稳定产量,汝箕沟就不行了,产权不清,管理混乱。大峰矿好时候没赶上,过几年说关就关。马莲滩矿,一直悬着,多年等不来一个确定的规划。
我曾经以为,每一个井田的名字背后都有一段英雄史——后来却发现更多是平淡的忍耐和无奈。矿工们的故事很杂,命运拼在一起,也很难说清谁对谁错。有人说国家没有亏待他们,有人觉得这点工资不算什么。总之无人满意。
回想起初期铺天盖地的调度、招工、大迁徙,其实大多数人只是追着一口饭吃。所谓理想,落在现实里,都得让位于矿井的出煤量。走廊上老照片发黄,仪表台的灰尘擦不掉。
今天再看这些老数据,这些奖章证书,也不过是厚重的历史尘埃。企业重组、新的体制轮换,大多数老人早已退休。孩子们大多远走,谁还会关心矿区里的老房子?新一代也许连石炭井三个字都念不准,企业早就不像当年那样沸腾了。
但我其实也想过,如果没有这场剧变,石炭井会不会依然热闹繁忙?或者早已和别的地方一样,被时间慢慢吞没。说到底,还是活在那一刻的人最清楚什么叫迁徙、什么叫根,什么又是归属感。
石炭井的记忆停留在诸如电厂的轰鸣、运煤火车的长笛,还有临时搭建的宿舍片区。人们大多不谈过去。只有老照片里还能看到工人罢工、孩子们放学后在废弃井田边玩闹的样子。这份历史,属于所有默默无声的人,也属于还在等一份答案的后来者。
全篇走下来,该说的、没说的都已成历史皮影。大部分人也许再不会回头,煤灰早就洗净了。然而石炭井的故事还未彻底终章,翻开一页就会遇到新的人和事。到底什么是归宿,什么是失落,也分时候,也难有定论。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