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手把手教你写《烧饼的日记》,(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15 14: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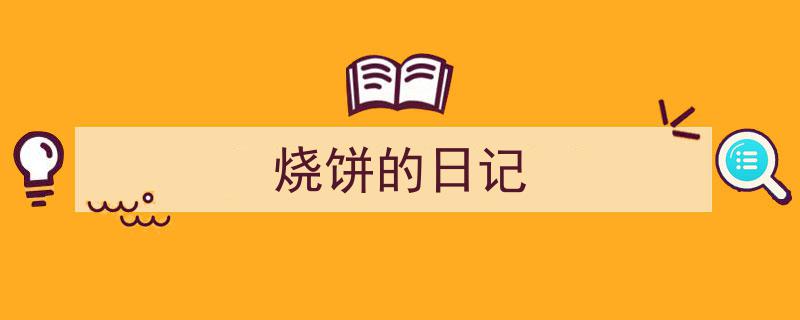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烧饼的日记作文,想要写得好,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
1. "明确中心思想 (Clear Central Theme):" 你写这篇日记,最想表达什么?是对烧饼美味的赞叹?是对制作烧饼过程的观察?是对某个与烧饼相关的回忆或情感?还是仅仅记录一次吃烧饼的经历?确定一个核心思想,能让你的文章更有重点,不跑题。
2. "选择具体的切入点 (Choose a Specific Focus):" 烧饼的种类很多(比如油酥烧饼、葱油烧饼、芝麻烧饼、地方特色烧饼等),制作方法也各异。你可以选择: "一次特别的吃烧饼经历:" 比如某次旅行中吃的、朋友亲手做的、或者某个特定场合吃的烧饼。 "对某种特定烧饼的喜爱:" 详细描述你最喜欢的烧饼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喜欢。 "观察制作烧饼的过程:" 如果有机会看到或参与制作,可以描写这个过程,突出细节。 "烧饼带来的回忆:" 它是否让你想起了童年、家乡或者某个人? 选定一个点,深入挖掘,而不是泛泛而谈。
3. "注重感官描写 (Focus on Sensory Details):" 日记是记录个人感受的,调动感官是关键
关于烧饼的日记
手里捧着一个烧饼,滚烫的。
不顾那熨坏嘴皮的温度,先咬上一口,芝麻香四溢。无论我多么谨小慎微,嘴角总是会沾上那么几粒芝麻,顾不得旁人的眼光,先享受我和烧饼的独处。烧饼不大,面上满满的芝麻粒儿,酥脆香口,别人三两口就解决完的事,我则是咬一口,停一会,既是咀嚼,也是延长这幸福的时光。
很多老北京说,每回想家了总是盼望能吃上一口烧饼。他们好这一口情有可溯,毕竟是自小如此。可是我呢,打小不吃、不爱面食,更别说饼了。这烧饼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呢?
为了搞清楚我这幸福感从何而来,跑去搜集资料。这烧饼历史悠久,据说是汉代班超时从西域传来的。竟然是舶来品,种类繁多、做法各异:咸甜浓淡,外酥内软,薄厚皆有。可是,这似乎无法解答我的疑问。
远在南方的家人听说我竟发现这等美事,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寄了几个烧饼回家。这会,我似乎弄明白了这幸福的答案。
烧饼是周末买的,等快递到了南方的家已经是三天后的事了。那天下了班,拖着疲乏的身子,怀里抱着沉重的笔电。光是身子累也就算了,一边盘算着明天的工作,心里的杂事一边像热粥遛缝似的把脑袋灌得满当当。经过单位旁的烧饼店,小铺子里的做饼师傅干得热火朝天,铺外面的食客排着一小长遛等待。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也就排上了。
后来,就发生了篇首的那一幕。现在坐在这敲打键盘,我似乎明白了。这幸福感是一种味觉唤起的记忆。就如同有的人伤心了爱吃巧克力,生病难受了爱喝一碗热乎的疙瘩汤,亦或是看文的你们,当深夜孤独寂寞饿,脑袋胃肠中萦回的那一种属于自己的美味。这种美味不是文字,他带给你的感觉我无法用文字描述,也没必要。因为这种幸福感很实在。
如何实在?
吃烧饼的小故事还没完,来一段插曲说不定能把事说透。
在我怀着无比幸福,和我的烧饼徜徉在槐花满地撒,尘土漫天扬的帝都。手机短信来了,是家人品尝烧饼后的感想。就两字:难吃!详细的解释有如下关键词可供参考:干、硬、痛苦。
所以,烧饼的幸福感是很个体的感受。可是,人们通过美食唤起对未来的憧憬,通过吃来实践这一追求,吃饱喝足后感叹一二,然后继续努力生活。
这感受,何等相似。只不过是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罢了。
我们都是一辆火车,一路狂吃、狂吃、狂吃、狂吃……
文 棉花儿
图 Angie Androit循CC协议使用
--------------------
你知道吗,什么解雇又叫「炒鱿鱼」?炒鱿鱼是广东话俗语,就是被公司裁员的意思。那个年代老板只提供住的地方,棉被都要自备,因此被解雇的时候,当然要卷起自己的铺盖走人。在炒鱿鱼时,鱿鱼被加热后会慢慢卷曲,和卷铺盖的动作相似,因此炒鱿鱼就成为被公司裁员的代名词。另一传说来源是以前香港的老板如打算裁员,会在每年所有职员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加一道炒鱿鱼以慰劳大家,并暗示会裁员。
订阅:微信搜深夜谈吃
微博:@深夜谈吃
投稿:tougao@tonightfood.com,你与吃的故事,讲给十万人听
深夜谈吃是覆盖千万受众的WeMedia自媒体联盟成员。微信搜索wemedia了解详情。
大学生返乡日记:藏在油酥烧饼里的哈尔滨年味记忆
你吃过层层起酥、香气四溢的油酥烧饼吗?
作为在北京上学的地道哈尔滨人,每年冬天最冷的时候,总是格外思念家乡烤的热气腾腾的油酥烧饼,好在总是能够定时收到母亲千里以外的一大包“礼物”,满怀欣喜地打开,咬上一口,却因为不再酥脆、变得软塌塌的外皮和冷掉的内馅而失落不已。
寒假到来,踏上回乡的旅途,回到熟悉的冰天雪地,更为品尝心心念念的味道。要去的小铺子并不远,从老楼出来,一路横着穿过两条马路,拐进副街再走几步就到了。这家自我出生起就坐落在街上的店铺,名叫“地八油酥烧饼”,少说也有近30年的历史。北方这些不起眼小镇的食杂店和饼店,曾有过一段漫长的国营历史,那时候的命名,按照成立的先后顺序分别命名为第一、第二……直到第九,一晃30年,从国营到私营,不少商铺渐渐消失,留下来的也通通把“第”改成了“地”。虽几经地址变更,始终没变的,是那口口相传了许多年的难忘味道。
扫码、推门,疫情防控使得店内的烟火气少了几分,阿姨似乎看出了我是面生的人,热情地向我介绍起来:带小芝麻点的是糖的,上面带一圈焦褐色酥皮的是油盐的……听着这熟悉的东北口音,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会心的微笑,这些都是刻在饮食记忆里的“暗号”啊!
回到家,吃着烧饼,一下子就又将记忆拉回从前。那时候的地八门口的小石子路,门边上似乎总是会支起小棚子,摆上几个小桌子,似乎总在等待工厂工人们的到来。从老轻合金厂下班的工友们,三三两两在桌旁坐下,要上几个麻辣饼,拿着塑料小勺大口大口地喝着豆腐脑,惬意地谈天说地,甩去满身的疲惫,临走时再咕咚咕咚喝上一小瓶荔枝汽水,打一个舒服的饱嗝,再慢慢踱回家。
只可惜,不知从何时开始,小镇中的年味,开始和那些时光里的老味道一起,一点点地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了起来。原来饼铺前每逢过年门前长队如龙的景象,似乎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了。原来店内摆在正中间的一盘盘油酥烧饼,也已经被更多种类、花花绿绿的各式糕点所替代。
但我似乎还是最钟爱老式油酥烧饼的味道,不仅仅是因为它那百吃不腻的口感,更是因为那一口烧饼中藏着从前小城过年前那令人怀念的热闹与忙碌,和人们冻红的脸上洋溢的幸福。那时候并没有可以一键下单的网购、外卖软件,并没有诸多可以外送的店铺、餐馆,大家都会在年前争着抢着上街购买年货,大街上始终是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以前在年前,冒着严寒,去排上半天的队,买上一两斤烧饼,在排队的时候顺便和老朋友寒暄几句,再心满意足地带着好不容易排到的“战利品”离开,是一件特别有仪式感、成就感的事情。
我们年轻一代似乎更加习惯了快递员、外卖员基础的敲门声,开门接过食品,再关上那一道可以与外面世界悄然隔绝的门,很多过年期间该有的烟火气息,不知不觉地在“砰”的一声的关门声中淡化了。大批拆掉搬迁的店铺旧址上建起了越来越高的楼层,在碰不到几个老熟人的宽阔马路上抬头望向各家各户的窗户,很难再找到以前家家户户都会挂在阳台的红灯笼了。
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好,小城里那些拔地而起的商厦是明证。我无比欣喜地看到小城的人们过上了比以前更加便利、快捷的生活,似乎动动手指、滑滑屏幕,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我也总是觉得怅然若失:那些轻而易举就能享受到的美味,似乎已经不再包含着那份踮起脚、搓着手、眼巴巴地望着出炉的喜悦。小城冒着热气、咬一口就流糖的油酥烧饼,总是能在一瞬间复苏人关于年味儿的记忆,让人无比怀念起那些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年节岁月。
一家人匆匆地吃完喝完,收拾桌子时我望向窗外冷冷清清的街巷,似乎才蓦然明白,那一口咬下去满嘴留香的油酥烧饼,让人心心念念的不只有那期盼了许久、回味了许久的老味道,更让人挂念的,是藏在那油酥烧饼里面的年味记忆。创造着新年俗的我们,忘不了这些滋养过几代人的旧年俗。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