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写作《时政观后感3000》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21 1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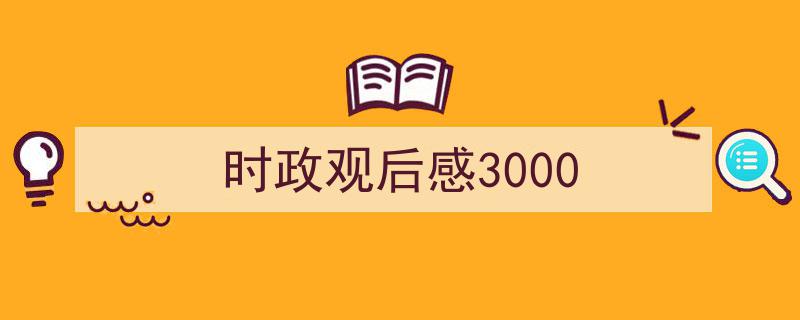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3000字的时政观后感,需要你不仅要有对时政事件的深刻理解,还要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论据来支持你的观点。以下是一些写作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选题与立意:"
"选择有深度、有意义的时政事件:" 避免选择过于琐碎或争议性不大的事件。选择那些具有普遍意义、能够引发思考、反映时代特征的事件,例如: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科技创新、国际关系、环境保护、民生问题等。 "明确你的观点和立场:" 观后感不是流水账,也不是简单的赞同或反对。你需要明确表达你对事件的看法,并给出理由。你的观点可以是支持、反对、辩证看待,或者提出改进建议。 "立意要高远,要有现实意义:" 你的观点应该不仅仅停留在事件本身,还要能够联系到更广阔的背景,例如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类命运等。要思考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影响,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二、结构与逻辑:"
"结构清晰,层次分明:" 3000字的篇幅需要合理的结构安排。建议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开头总述事件背景和你的总体观点,中间分几个部分展开论述,每个部分围绕一个分论点展开,最后总结全文,重申观点并升华主题
读毛泽东《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有感
信息洪流中的"土喇叭":《时事简报》的当代启示
1931年春天,毛泽东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写下《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一文时,恐怕不会想到,这篇看似简单的指导文章,会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信息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抖音、微博、朋友圈构筑的现代传播图景中,毛泽东关于"《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的论断,意外地成为一面照映当下传播困境的明镜。当我们被淹没在信息的汪洋中却依然感到"知情的饥渴",当算法推送的同质化内容不断强化我们的认知偏见,回望那个油印小报作为主要信息载体的年代,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某种超越时空的传播智慧。
《时事简报》在当时的实践中展现出惊人的传播效率。毛泽东特别强调内容要"十分之九是本地事实",要求"字要写得大,要看得清楚",这些细致入微的要求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永恒的传播真理:有效传播必须建立在对受众认知习惯和实际需求的深刻理解之上。在中央苏区,识字率极低的农民群众通过这种大字报式的简报,"看得出神""听得有味",这种传播效果令今天的许多新媒体运营者羡慕不已。反观当下,我们的信息平台虽然拥有精准的用户画像和复杂的算法模型,却常常陷入"精准的无效传播"怪圈——数据告诉我们用户"喜欢什么",却很少关心他们真正"需要什么"。
毛泽东对《时事简报》"三天出一张,一个月出十张"的出版频率规定,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一种传播诗学。这种节奏既保持了信息的时效性,又避免了信息过载,在"及时"与"适度"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当代人每天接收的信息量相当于一份170份报纸,但绝大多数信息如过眼云烟,留不下任何痕迹。《时事简报》的启示在于:真正有效的信息传播不在于数量的多寡,而在于能否在受众心中引发共鸣与思考。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或许更需要这种"节制的美学",让每一则信息都有被认真对待的可能。
《时事简报》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的"在地性"。毛泽东要求简报内容必须与当地群众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甚至具体到"某某村"的层面。这种极致的本土化传播,创造了一种奇妙的认知图景:农民通过了解隔壁村庄的斗争故事,自然而然地理解了全国革命的宏大叙事。当下全球化的信息网络中,我们反而失去了这种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路径。国际大事与明星八卦充斥着我们的屏幕,而我们却可能对所在社区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重建信息传播的在地维度,或许是破解当代人"近处的盲视"的一剂良方。
在话语风格上,《时事简报》遵循"不做文章,只登事实"的原则,这种朴素到近乎笨拙的传播方式,反而成就了其独特的说服力。毛泽东特别反对"形容词语太多",认为这会减弱简报的实效性。反观当下的公共传播,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形容词通胀"——各种修饰语、夸张表达充斥媒体,导致语言的表意能力不升反降。当所有事情都被描述为"震惊""颠覆""史诗级"时,语言就失去了区分重要与琐碎的能力。《时事简报》提醒我们:去掉浮华的修辞,事实本身的力量往往最为持久。
当代传播生态面临的核心困境之一,是技术赋权与认知退化的悖论。一方面,社交媒体理论上使每个人都拥有了发声渠道;另一方面,算法推荐和圈层效应又使不同群体间的认知鸿沟日益加深。毛泽东当年面对的"群众保守观念"问题,在今天以更复杂的形式重现——信息茧房中的认知固化。破解这一困境,或许需要借鉴《时事简报》那种既通俗又不失深度的传播智慧:不居高临下地"启蒙",而是从群众的生活经验出发,引导他们看见更广阔的世界图景。
重读《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最打动人的是其中蕴含的对普通民众认知能力的尊重与信任。毛泽东把简报定位为"促进群众文化教育的有力工具",这种将信息传播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的观点,远比当下将受众简单视为"流量"或"消费者"的传播理念更为深刻。在注意力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传播者与被传播者的关系日益异化为捕获与被捕获的关系,重建传播活动中人的主体性,恢复信息与人之间的滋养性而非剥削性关系,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传播伦理课题。
站在5G时代的门槛回望,《时事简报》就像信息洪流中的一座灯塔,提醒我们有效传播的本质从未改变:真实的内容、适度的节奏、贴近的表达、对人的尊重。这些原则不会因为技术迭代而过时,相反,在技术越发达的时代,这些基本原则越显珍贵。当代传播者需要的不是对旧形式的简单模仿,而是对那种传播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在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中,重新找到连接人心的方法论。
当我们在元宇宙的边缘徘徊,在算法的迷宫中寻找出路时,那个革命年代油墨飘香的《时事简报》,依然在诉说着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理:最好的传播,永远始于对受众真实生活的理解,终于人的觉醒与成长。这或许就是这篇写于烽火年代的文章,给予信息时代最珍贵的启示。
七律·观韩政坛剧变有感
七律·观韩政坛剧变有感
戒严令下万民寒,
弹劾声中宝座残。
股海翻波吞玉阙,
票箱藏垢染金冠。
昔时青瓦台前客,
今作囹圄月下叹。
莫道权高能蔽日,
民心自是最公判。
赏析:
从诗体创新与现代性表达看《七律·观韩政坛剧变有感》的突破与坚守
古典诗词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对既往范式的刻板复制,而在于在格律的框架内回应时代命题。《七律·观韩政坛剧变有感》作为一首关注国际时政的现代七律,既未脱离唐诗宋词奠定的诗学根基,又以独特的视角、新锐的意象和跨文化的观照,打破了传统咏史题材的疆域,展现出古典诗歌形式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若跳出对具体唐宋诗作的比附,从诗体功能的拓展、现代意象的嫁接、国际视野的融入三个维度审视,更能窥见其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架起的桥梁。
一、诗体功能的现代拓展:从“咏史”到“观今”,突破地域与时代的边界
唐诗宋词中的七律,多以本土历史、家国命运为书写对象。杜甫的七律写安史之乱中的中原烽火,陆游的七律叹南宋偏安的山河破碎,文天祥的七律诉宋亡后的孤臣血泪,其“史”的范围始终未跳出华夏文明圈。这种以“本土史”为核心的书写传统,在《七律·观韩政坛剧变有感》中被悄然突破——诗人将目光投向邻国政坛,以“他者”的政治动荡为镜,照见权力运作的普遍规律,让七律的“咏史”功能延伸为“观今”的国际视野。
这种突破并非对传统的割裂。事实上,唐宋诗词本就有跨越地域的观察基因:王维出使边塞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岑参在西域吟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们以异乡风光拓展了诗歌的空间维度。此诗则将这种“空间拓展”转化为“政治观察”的跨域性,其“戒严令”“弹劾”等现代政治术语,与唐诗中“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战争叙事虽内容不同,却共享着“以诗记录时代变局”的精神内核。
更值得关注的是诗体功能的“当代性”转化。传统七律的批判多指向历史沉疴,如杜牧《过华清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讽刺的是百年前的骄奢;而此诗直面“正在发生的历史”,“股海翻波”“票箱藏垢”等描述,将金融市场波动、选举舞弊等现代政治现象纳入格律之中,让七律从“历史的回响”变为“现实的回声”。这种转化暗合了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理念,却比白氏的“新乐府”更具时效性——它不再是对往事的追溯,而是对当下的即时书写,使古典诗体获得了介入现实的锐利锋芒。
二、现代意象的创造性嫁接:让“金冠”与“票箱”在格律中生长
唐诗宋词的意象体系,多植根于农业文明与传统社会:“明月”“杨柳”“孤舟”“驿站”等意象,承载着古人的生活经验与情感密码。而《七律·观韩政坛剧变有感》的显著特色,在于将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标志性意象,无缝植入七律的格律框架,形成古典形式与现代内容的奇妙融合。
“股海翻波吞玉阙”中,“股海”这一现代金融意象的出现,堪称对传统“江河”意象的创造性替代。唐诗中“黄河之水天上来”写自然伟力,“大江东去浪淘尽”叹历史苍茫,而“股海翻波”则以资本流动的汹涌,喻示现代社会权力与财富的交织博弈。“吞玉阙”的夸张手法,既延续了李白“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气魄,又让“玉阙”这一传统宫殿意象,与“股海”代表的现代资本产生碰撞——前者是权力的象征,后者是利益的载体,二者的“吞噬”关系,精准揭示了当代政治中资本侵蚀权力的深层矛盾。
“票箱藏垢染金冠”则更具现代政治符号意义。“票箱”作为民主选举的标志性器物,本应象征民意的纯洁,而“藏垢”二字直指其异化;“金冠”作为权力的隐喻,本应代表责任与荣耀,却被“染”上污浊。这种对现代政治符号的解构,与宋词中“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意象张力异曲同工——辛弃疾以“吴钩”这一兵器意象写壮志难酬,此诗则以“票箱”“金冠”写制度异化,都是借具体物象承载抽象的社会批判。
尤其巧妙的是意象的“格律适配性”。七律要求颔联、颈联对仗,“股海”对“票箱”、“翻波”对“藏垢”、“玉阙”对“金冠”,不仅词性工整,更在意义上形成“经济—政治”的对应,既遵守了“词性相对、平仄协调”的古典规则,又让现代意象在格律的约束中获得了诗性表达。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智慧,恰如苏轼在词中“以诗为词”的创新——不是打破格律,而是让格律成为承载新内容的容器。
三、权力哲学的诗意表达:在“民心公判”中重铸古典民本思想
唐宋诗词中蕴含的政治哲学,多以“民本”为核心: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民生关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意识,构成了古典诗歌的精神底色。《七律·观韩政坛剧变有感》的深刻之处,在于将这种民本思想置于现代权力运作的语境中,以“民心自是最公判”的结论,完成了对古典政治智慧的现代诠释。
“昔时青瓦台前客,今作囹圄月下叹”的命运对照,看似写个体的兴衰,实则暗含对权力本质的思考。青瓦台作为韩国权力中枢,其象征意义与唐诗中的“金銮殿”“紫宸殿”相通,但诗人并未停留于“荣枯无常”的传统感慨,而是通过“囹圄”的结局,指向“权力失控必遭反噬”的现代政治逻辑。这种思考比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历史循环论更具现实针对性——它不再将兴衰归因于“天命”,而是归因于“民心”的向背,使古典的“天道循环”观转化为现代的“民意裁决”论。
尾联“莫道权高能蔽日,民心自是最公判”更是对古典民本思想的升华。“权高能蔽日”脱胎于李白“总为浮云能蔽日”的忧思,但李白的“浮云”喻指奸佞,而此诗的“权高”直指权力本身的膨胀;更关键的是“民心公判”的提出,将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朴素愿望,转化为“民意决定权力合法性”的现代政治理念。这种转化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对“民为邦本”思想的时代发展——在古典诗词中,“民心”多是被动的“载舟覆舟”之水,而在此诗中,“民心”成为主动的“公判者”,这一变化既呼应了现代民主理念,又让古典诗歌的政治表达获得了新的思想深度。
从以上角度看,《七律·观韩政坛剧变有感》的价值,不在于对唐宋诗词的简单模仿,而在于它证明了古典格律的弹性与包容力。当“票箱”与“玉阙”在对仗中相遇,当“股海”与“明月”在平仄中共存,当“民心公判”的现代理念借七律的声韵流传,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首关注国际时政的诗作,更是古典诗歌在当代的一次成功“突围”——它告诉我们,只要能回应时代的追问,承载人类共通的情感,古老的诗体永远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