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一篇文章轻松搞定《新华书店作文》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23 0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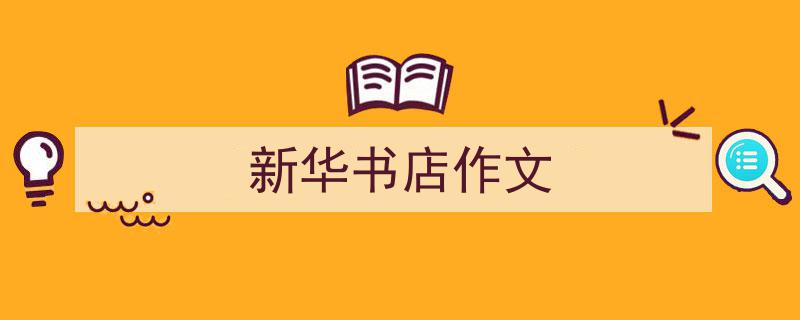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新华书店的作文,可以有很多角度和侧重点。为了写好这篇作文,你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
"1. 明确写作目的和中心思想 (Clear Purpose and Central Theme):"
"你想表达什么?" 是想描绘新华书店的"历史变迁"?"建筑特色"?"文化氛围"?"人们在书店里的活动"?还是想表达它对你"个人成长"的意义?或是探讨它在"数字时代"的"角色和挑战"? "确立中心思想:" 你的作文应该围绕一个核心观点展开。例如:“新华书店,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城市文化记忆的载体。” 或者 “即使面对电商冲击,新华书店依然以其独特的魅力维系着人们的阅读情怀。”
"2. 选取合适的写作角度和内容 (Choose a Suitable Angle and Content):"
"角度:" "记叙文角度:" 可以写一次去新华书店的经历,如挑选书籍的乐趣、在某个角落安静阅读的时光、参加书店活动的感受等。 "描写文角度:" 重点描绘新华书店的内部环境(琳琅满目的书架、柔和的灯光、特定的区域如儿童区、电子阅览区)、外部建筑风格、书店的日常景象(顾客的多样性、店员的忙碌)等。 "议论文角度:" 可以讨论新华书店的社会价值、文化意义,
“我在书店,遇见了鲁迅先生”
我与北京图书大厦
北京过去有四个著名的书肆,就是东城的东安市场书肆、南城的琉璃厂书肆、西城的西单商场书肆和东城的隆福寺街书肆。
当时我家离西单商场书肆很近,从太平桥大街,往东穿过劈柴胡同,就到了西单商场书肆。
这个书肆面积很大,排列着许许多多书摊,那时书摊都是私营的,一家一个书摊,一户一个门面,各显其能,服务周到。新书旧书,线装精装,中文外文,诸种版本,各色各样,琳琅满目。
我常去淘的多是旧书、工具书等。我上中学用的教科书,大多淘的是旧书,因为便宜。
记得《三S平面几何》,淘一本七八成新的,价钱也就相当于新书的1/4或1/5。
还有工具书,如精装布面袖珍本《四角号码新词典》只要1块钱,省点伙食尾子就能买一本。
后来买中华书局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1963年版),精装本、道林纸的,书价是18元,我爱不释手,却买不起。每次去摸摸,遗憾空手回。
后来混熟了,问库存几本,书店老板答:“两本。”我说:“剩一本时告诉我。”
于是我开始攒钱。
半年多以后,书店老板告诉我:“还剩下一本了。”我说:“请给我收起来。”
过了不久,钱攒够了,我去把书取回。
我还淘了“四部备要”本的《说文解字注》等。从此,《四库全书总目》《说文解字注》就成为与我相伴数十年、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后来在西单商场旁边,开了一家新华书店,这自然是我到西单必去看书、买书的地方。
我搬到北新华街北口的房子居住以后,离西单还是很近,从北新华街北口,穿过长安街马路,过了电报大楼,就到了西单新华书店,所以周末常去淘书、看书。
随着城市发展,西单商场改造,1998年5月18日,新盖的北京图书大厦,开始营业。
营业面积1.6万平方米,有图书多达几十万种,后拓展音像制品等至40余万种。这里图书品种多,服务又好,曾踞全国各书店图书销售榜的魁首。
我到过全国各地的许多书店,他们都赞誉北京图书大厦是全国第一书城。
我的《明亡清兴六十年》讲稿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书。记得当时电视首播与书店售书同步进行,中华书局和北京图书大厦联合在图书大厦举办《明亡清兴六十年》的新书发布与签名售书活动。
2007年2月11日(星期日)早上书店开门前,我们就到了图书大厦,见门前已经排起长龙似的队伍。我们从侧门进入图书大厦之后,直接到新闻发布与新书签售处的八楼。
上午9点,书店大门一开,排队的人群有序地进入图书大厦。
队伍从八层楼道顺序往下排,七层、六层、五层、四层、三层、二层、一层、地下一层、地下二层、地下三层,又开始转圈排队,没有警察,没有保安,虽然人员爆满,却是井然有序。
记得有一位先生排队购书并请我签名,我抬头一看,这位老先生年纪很大。
这使我肃然起敬,连忙站起来说:“请问您高寿?”:“八十二。”
我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排队?”:“我来晚了一点,从地下三层开始往上排。”
我立刻请书局和书店的同志给老先生搬把椅子坐,并给老先生递瓶矿泉水。
这么大的年纪,从地下三层顺着楼梯,一级一级地爬,爬了十一层楼,是多么让我起敬,多么让我感动,又多么值得我学习,多么激励我前进!
在排队签名的读者中,有从广州、深 圳坐飞机来的,有从昆明坐火车来的,也有从西安、沈阳、兴城、抚顺、天津、石家庄等地坐火车来的……
这不是我个人的魅力,这是中华民族爱读书、善学习的力量,这是改革开放人们精神振奋和社会风貌的一次展现。
藏着一家图书馆的书店
“书非借不能读也。”这句话固然是至理名言,但如果出现在一家书店里,那就有点儿古怪了,这不是拆自己的台吗?
然而,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六楼,便有这样一行标语。
原因其实很简单——王府井新华书店别开生面,居然在自己的店堂里面藏了一家图书馆,找到“书非借不能读也”的标语,便找到了这家面积不大却充满书香味道的小馆。
我问过书店的管理人员,为什么在这里开一家图书馆,不影响营业吗?
那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温和地一笑,说:“来的都是爱书的人,怎么会影响营业呢?”
抬头看去,果然是一群安静的读书人,颇有人埋了头,读到得意之处惬意地伸个懒腰,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
至于营业……我看到有老先生走出图书馆,便顺手捎上两本书,递到柜台上让店员包了带走。
那份闲适自然,就像是老北京茶馆的客人,临走叫伙计包二两香片带回家去一样。
我忽然想,这家书店的老总莫不是故宫出来的?单霁翔院长的手段便是让你先看,看完了顺便再买点儿故宫的文玩带回去,硬是把文化做出了效益,还不带一丝烟火味儿。
我问同去的女作家林特特有什么感受,她说当然有,不过你先说。
我说我的感受,就是仿佛回到了童年。
那时候我经常来王府井新华书店,但可不是来买书。当时囊中羞涩,难得有这样一家大的书店,早上进去看书,到人家关门才依依不舍地出来,一个星期天就这样过去了。至今在那里读过的书还记得清楚呢。
“光看不买,人家没有赶你?”特特问。
“没有赶过。”我说,“那时候看书都小心翼翼,生怕把新书给人家看脏了没法卖,像我这样看书的人不少,店员从来不管,从你身边走过,就像没看见一样,这份看不见,其实给了我们这些兜里没钱的读书人一份难得的尊严——他们尊重读书的人。”
说完了,我问特特:“你呢?”
特特说了个不相干的事情。她当年是在中国书店工作过的,说刚进书店,便见到一位白头发的老店员,给他们这些新人一一介绍店里的情况。末了,特特知道他在书店里已经工作几十年了。
“几十年,遇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吗?”特特问他。
老先生想了半天,说:“几十年前啊,我也刚到这里——自然,那时候店名也不叫‘中国书店’,年纪小,下午的时候一不留神在柜台上睡着了。
“被掌柜的叫醒,很是惶恐。却见掌柜的是陪着一位有翘胡子的先生进来挑书,那位先生便和蔼地摸了摸我的头。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鲁迅先生。”老店员说完了,坐在和煦的阳光里,不再说话。
“那时候,我才觉得原来我离鲁迅先生的距离,竟然也只隔了身边这位老人。”特特说。
一瞬间,我们都沉默了,都不大想说话,而阳光,一如当年那个温馨的下午。
似乎,这是个不相干的故事,可是那份悠远的书香,却仿佛从那个下午,一直传到王府井书店的小小图书馆来。
作者:阎崇年,萨苏,本文摘自《遇见一家书店》。
我的精神家园——新华书店
如今每到一个城镇我都习惯去看看那里的新华书店,长时间地驻足欣赏毛主席那遒劲有力、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新华书店”,心中总会涌出一种朝拜圣地的感觉。说起新华书店,我的故事说也说不完,她是我一生的精神家园。岁月如梭,如果要我说一生中首先要感谢谁?当然要感谢新华书店,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因种种原因,只身一人从福州到山高水寒的僻远山区周宁县读书,靠免学费和助学金读完中学。那时候物质非常匮乏,生活非常艰难,我穿的是人民武装部救济的棉衣,吃的是地瓜米饭,喝的是萝卜叶子汤,唯一的享受是读书。那时候周宁一中藏书很少,我每天下午四点多就跑到县城唯一的一间新华书店看书。从学校一路跑去,周边都是水田,从学校到街心要穿过一条田埂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生怕新华书店关门了。路上我仿佛看到店里的图书,向我款款走来,每一本书的作者向我深情地打招呼,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我向往的大师。每天在书店里的时光是最愉快的,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
当时书店里只有一个售货员,她是福州人,我称她为福州依姐。她让我随便看,有好书时,她说这些好书每次只进货两三本,有一本是要送给县文化馆的,所以我读时要好好保护和珍惜。我倦缩在书架下读书,每每忘了时光流逝,当店里亮起汽油灯时,那便是打烊了。依姐就会轻声细语地对我说:“依弟,该回去了,明天再来。”她个子很小、瘦弱,但很温柔,总是微笑着说话。
至今回忆起那家书店,真的很小,门前是一条石板路,过几间店面有一个专供挑夫休息的驿站。傍晚,市声渐起,从福安翻山越岭来的挑夫就聚在那儿喝茶,嘻笑着,大碗大碗吃着米豆腐。一抹斜阳照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我回首望望那间书店,亮着昏黄的灯光,像是我远离的家,福州依姐就像是我早年病逝的妈妈。
福州依姐每天都向我介绍店里来的新书。在书店里我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普希金诗集》《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等等。读书时,我会走进另一个世界,接触到一个个世界上最健谈的人。新华书店,带我去到一个不同的国度或不同时代,跟我讨论一些从来不知道的问题。那时,完全被带入了书中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发现自己是最幸福的人。读都德的《小东西》,我泪如雨下,读到最伤心的时候几乎气息闭塞,这是因为我从小有类似的生活经历。当然书也给我带来了生活的力量和勇气,我永远忘不了,那时候读伏尼契的《牛虻》时无比激动的情景,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心潮澎湃。
我在书店天天看书的事,也传遍了小小的周宁县城关。有一天来了一个人,特别好奇地问我的经历和爱好,当我向他叙说自己的身世时,他流泪了。他说他名叫林如成,是县税务局的干部,单身汉,比我大十多岁,也喜欢书,要和我交朋友,于是我们成了忘年交。书友真是最好的朋友。他涉猎群书,喜读名著,家中有许多藏书,后来他还经常邀我到他宿舍里玩,一边围炉吃烤马铃薯,一边交流读书心得,忘记了尘世中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怡然自得。纵论世界之广、宇宙之大,此时却仿佛只有我们和书的存在。我起先叫他为老师,他动情地说情愿我把他当做朋友,因为只有朋友间才无话不谈,而师生中间始终有一种隔膜。在以后的数年间,我们一起在书的海洋里更自由,更无拘无束,更加找到真正的自我。至今六十多年了,我还珍藏着他为我在书店里买的莎士比亚的剧作《哈姆雷特》和《亨利五世》,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当时每册才一元钱,现在却是我书房里的宝贝。如今他已经九十多岁了,我们之间仍然保持书信及微信往来,兴致勃勃地谈读书的愉悦。
有一次,我在新华书店读到《郭沫若文集》中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剧本后,我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郭沫若先生,信上还抖胆请求他把不用的藏书寄给我。十多天后,不曾想郭老真的让他的秘书寄来了一大摞书,其中有他的新作诗集《百花齐放》《雄鹰集》等等。他的秘书用非常工整的钢笔字写一封信给我,信中说:“郭沫若院长收到你的来信,很敬佩你求知的精神,郭院长叫我寄上十几本书,希望你学习进步!”这封信用中国科学院的特大信封寄达,轰动了周宁一中。当时的老校长詹其道先生还特地为此事约我到校长室谈了一个下午。
高中毕业,我考进了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中文系有很大的图书馆,我习惯地衷情于新华书店,每当周末我总是要从长安山上徒步赶到大桥头的新华书店,一呆就是半天。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多读书。在漫长的学习生涯中,我总觉得书店其实不是店,是我们栖居的精神家园。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不只是这些,书店模样应是天堂的模样。有一次我年老的父亲破天荒地来信说,约我周天到聚春园吃小吃。我乘车到东街口,忽然看到东街口那间新华书店,便拐了进去,一去就舍不得离开,害得我老父亲久等不遇,生气地回家。后来老父亲问我这件事,我说,我倘佯在书店里好像有着将自己渺小的灵魂腾飞起来的感觉,忘了一切。父亲听了,大为不解,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荒唐!”
毕业后当了语文老师,逛书店更是生活的一种享受。我第一次领了工资,家里人叫我去添置蚊帐被褥,可是我将这些钱买了《青春之歌》《红楼梦》《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古代散文》《辞源》等。家里人大为光火,说我是书呆子,其实坐拥书城是我的梦想。有一次到北京开会,坐绿皮车两天两夜到了北京火车站。我带上行李直奔长安街新华书店,因为早上六时到北京,乘车到长安街,书店还没开门,我坐在书店门口等待,看着长安街上冉冉升起的太阳、匆匆的行人,我感到一种无名的幸福。那一次,一口气买了三十几本书,硬扛着、气喘嘘嘘地赶去招待所报到。会议代表们看我狼狈的样子,笑着说,有听说痴的,都没看到你这样痴的。
早年间,市面上闹书荒,买书很困难,我逛新华书店买书凭票供应。无奈之下,只好找到我教过的学生,他是大桥头新华书店的负责人。他给我走了“后门”,让我走进供书的仓库去挑捡,然后偷偷地给我开发票让我从小门出去。想当时买书象偷书一样,至今还暗中发笑。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以为新华书店正是我们思想的半亩方塘:我一生的经历正是凭着阅读,文明得以传递,智慧得以传扬,使我们得以成长。我有两本小书《作文智慧》《老根说字》获华东和福建优秀图书奖,我终于能在全省各地新华书店开了十多场讲座。从蹲在书店角落里默默地看书,到堂堂正正地登上书店的讲台,有一种难以言表的自豪!
我的一生与新华书店结下了不解之缘,书店是一座城镇的文化名片。她有着一种文化的静水流深的底蕴,保留着读者对历史的情感,感受到文明世界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婉转和体贴……这记忆中还有一种过往的甜蜜。如今我已近八旬,但一看到那大气磅薄的四个大字:“新华书店”,心中总会忍不住地呼喊:“永远的新华!永远的书店!”(王立根)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