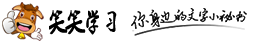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格策美文教你学写《摘槐花日记》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24 06:1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摘槐花”的日记作文,可以注意以下几个事项,让你的作文更生动、具体和有感染力:
1. "明确日记的视角和基调:" "是记录事件,还是抒发情感?" 你是侧重于描述摘槐花的整个过程,还是更想表达槐花的美丽、摘槐花的乐趣、对童年/家乡的怀念,或是和家人/朋友一起活动的温馨? "基调是什么?" 是轻松愉快的,充满童趣的?是略带伤感或怀念的?还是对劳动过程的体验和思考?明确基调有助于选择合适的词语和描写方式。
2. "抓住“槐花”的特点进行描写:" "视觉:" 槐花是什么颜色的?(通常是白色或淡黄色)是什么形状的?(小小的、呈圆锥形)花朵密集还是稀疏?阳光下的槐花是什么样子?夜晚或雨后的槐花又如何? "嗅觉:" 槐花有什么特别的香味?(浓郁、清甜、沁人心脾)这种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是怎样的感觉? "触觉(如果可能):" 摘下来的槐花摸起来是什么感觉?(轻盈、柔软、有点绒毛状)
3. "生动描绘“摘”的过程:" "准备:" 你是怎么准备去摘槐花的?(大人带路?自己
那年我上树摘槐花,女同学在树下喊:你再不下来,我长大就嫁给你
1
那家新开的香水店,门脸不大,藏在一条刚被雨水洗刷过的巷子深处。
玻璃门上挂着风铃,有人推门,就叮铃作响,声音清脆,像极了小时候挂在窗檐下的那串贝壳。
我走进去,并非为了买香水。
只是因为路过时,一阵风从门缝里挤出来,裹挟着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蛮横地撞进我的鼻腔。
那味道,清甜,又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青涩,像……像槐花。
对,就是槐花。
店员是个年轻女孩,穿着棉麻长裙,声音温和,问我需要什么。
我摇摇头,说随便看看。
目光在一排排精致的玻璃瓶上逡巡,它们在暖黄色的射灯下,折射出琥珀般的光泽。每一个瓶子里,都囚禁着一个春天,或者一个夏天。
我的手指最终停在一瓶淡绿色的液体前,标签上用法文写着什么,我不认识。但瓶口渗出的那缕香,和记忆里的味道,重合了。
「能闻闻吗?」我问。
女孩笑着点头,取出一张试香纸,轻轻一喷。
雾气散开,那股熟悉的、霸道的甜香瞬间将我包裹。
太像了。
像得让我一瞬间有些恍惚,仿佛脚下踩的不是光洁的木地板,而是松软的、混着泥土和落叶的土地。
耳边也不是店里舒缓的音乐,而是蝉鸣,是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喧闹,是她清脆又带着点焦急的喊声。
「你再不下来,我长大就嫁给你!」
2
记忆里的那个夏天,天总是很蓝,云很白,太阳也格外毒辣。
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仿佛要把整个夏天的力气都用尽。
那时候我们还在上小学,下午的课总是昏昏欲沉。数学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粉笔末像雪花一样簌簌落下,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粉笔灰和旧书本混合的味道。
我的魂魄早就飞出了窗外,落在了操场边那棵巨大的洋槐树上。
那棵树年纪很大了,树干粗壮得要两个孩子才能合抱。它的枝叶繁茂,像一柄撑开的巨伞,为我们遮蔽了半个操场的阳光。
更重要的是,五月一到,满树都会开满白色的槐花。
一串串,一簇簇,像雪,像云,也像女孩子裙边精巧的蕾-丝。风一吹,整个校园都浸在一种甜得发腻的香气里。
那香气,对我们这群半大的孩子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因为那意味着槐花饭、槐花饼、槐花炒鸡蛋。在那个物质并不丰裕的年代,这是无上的美味。
放学的铃声一响,我便第一个冲出教室,书包往地上一扔,猴子似的蹿上了那棵老槐树。
我从小就擅长爬树,手脚并用,灵活得像只壁虎。粗糙的树皮硌着手心和膝盖,留下火辣辣的印记,但我毫不在意。
越高处的槐花,开得越盛,也越干净。
我骑在一个结实的树杈上,视野豁然开朗。能看到红色的教学楼,飘扬的国旗,还有树下那群仰着头、叽叽喳喳的同学。
他们像一群嗷嗷待哺的雏鸟。
而我,就是那个凯旋的猎手。
我摘下一大串最饱满的槐花,得意地冲着下面晃了晃,然后精准地扔进一个女生的竹篮里。
「给!」
树下爆发出一阵欢呼。
我能清晰地看到林响站在人群的最外围。
她和别的咋咋呼呼的女生不一样,总是很安静。她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蓝色连衣裙,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系着红色的蝴蝶结。
她没有像别人那样伸手去接,只是仰着头,静静地看着我。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的眼睛很亮,像含着一汪清泉。
我心里莫名一动,又摘了一串更大、更漂亮的,只为她一个人扔了下去。
「林响,这个给你!」
槐花串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不偏不倚,落在了她的脚边。
她没有立刻去捡,而是皱起了眉头,似乎有些生气。
「你快下来!太高了!」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穿透了周围的嘈杂。
我当然不肯。
男孩子的虚荣心在那个年纪,比天还大。在喜欢的女孩子面前,更是要表现出十二分的英勇。
「没事儿!这点高度算什么!」我拍着胸脯,又往上爬了一截,去够一串开在枝桠最顶端的槐花。
那里的花,白得像雪,没有一丝杂色。
「喂!你听见没有!」她好像真的急了,声音也高了起来。
我偏不作答,只顾着小心翼翼地攀爬。脚下的树枝发出轻微的「嘎吱」声,像是在抗议我的体重。
树下的喧闹声小了下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聚焦在我身上,有担忧,有羡慕,但更多的是期待。
就在我马上要够到那串花的时候,林响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豁出去的决绝,还有一丝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音。
「周扬!你再不下来,我长大就嫁给你!」
整个世界,在那一瞬间,安静了。
只剩下知了还在不知疲倦地叫着。
我脚下一滑,差点从树上掉下来。
我最终还是从树上下来了。
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那句惊天动地的「嫁给你」,而是因为教导主任闻讯赶来。他那张黑如锅底的脸,比从树上掉下去还可怕。
我被罚站在办公室外面壁思过,耳朵里灌满了「危险」、「不听话」、「再犯就请家长」之类的训斥。
林响和一群同学,抱着那篮子槐花,悄悄地等在走廊的尽头。
等教导主任的咆哮告一段落,她才小步地跑过来,把一包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进我手里。
「给你的。」她低着头,脸颊红得像天边的晚霞。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几个刚蒸好的槐花饼,还冒着热气。白色的面饼里,点缀着青绿的槐花,散发着一股清甜的香气。
我捏起一个,咬了一口。
软糯,香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槐花饼。
「你……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吗?」我一边吃,一边含糊不清地问。
她的头埋得更低了,几乎要戳到胸口。
「我……我那是……那是瞎说的!谁让你不下来!」声音细若蚊蚋。
「哦。」我应了一声,心里却有点小小的失落。
但很快,这种失落就被槐花饼的甜美味道冲淡了。
那天之后,「长大就嫁给你」成了我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
同学们偶尔会拿这件事开玩笑,一看到我俩走在一起,就起哄地喊:「新郎官!新娘子!」
每当这时,我都会装作毫不在意地挺起胸膛,而林响则会羞得满脸通红,追着那几个起哄的男生打。
我们的关系,似乎因为那句童言无忌的承诺,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我们会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我家和她家只隔了一条巷子,那段路,我们总是走得很慢很慢。
我们会聊很多天马行空的话题。聊天上的云为什么会变,聊河里的小鱼晚上睡在哪里,聊长大以后,是当科学家好,还是当飞行员好。
她问我:「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想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她欲言又止,「那你还回来吗?」
「当然回来!」我拍着胸脯保证,「等我赚够了钱,就回来盖一座大房子,院子里种满槐花树。」
我没有说出口的后半句是:然后,就把你娶回家。
她听了,眼睛亮晶晶的,像是落满了星辰。
「好,我等你。」
那个夏天的风,总是带着槐花的甜香。那个夏天的承诺,也像是被蜜浸过一样,甜得让人心安。
我们以为,夏天会一直持续下去,槐花会一直开着,那条回家的路,我们能一直走下去。
可夏天终究会过去,槐花也会有落尽的一天。
小升初,我们被分到了不同的班级。虽然还在同一所学校,但见面的机会,肉眼可见地变少了。
初中的学业开始变得繁重,堆积如山的作业和应接不暇的考试,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走了我们所有的课余时间。
我们不再一起放学,因为各自都有补习班。
我们不再有时间去聊云和鱼,因为有背不完的公式和单词。
偶尔在走廊里遇见,也只是匆匆地相视一笑,点点头,然后擦肩而过。
那句「长大就嫁给你」的戏言,也渐渐被遗忘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像一颗落了灰的糖果,失去了最初的光泽。
我依旧是那个调皮捣蛋的男生,会因为上课看小说被老师罚站,会因为和同学打架被请家长。
而林响,一直是那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她的名字,总是出现在光荣榜的最前列。她是老师眼中的骄傲,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
像两条原本平行的线,不知从何时起,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
中考前夕,学校的气氛紧张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每个人都埋首于书山题海,为了一个虚无缥缈却又至关重要的未来,奋力一搏。
有一天晚自习后,我在车棚里碰到了她。
她正在费力地给自行车打气。夜色很浓,只有一盏昏黄的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走过去,很自然地接过她手里的气筒。
「我来吧。」
她没有拒绝,默默地站在一旁。
气筒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最近……学习很累吧?」我没话找话。
「嗯,还好。」她的声音有些疲惫。
「想好考哪所高中了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爸妈想让我去市里读。」
我的心,猛地沉了一下。
市里,离我们这个小镇,有三个小时的车程。那意味着,我们将要去到完全不同的世界。
「哦……挺好的,市里的教育资源好。」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发慌。
气打满了。我把气筒还给她。
「谢谢。」
「不客气。」
我们之间,又陷入了沉默。
良久,她才开口,声音很轻:「周扬,你还记得吗?小时候……」
「记得。」我抢着,生怕她觉得我忘了,「你说,长大要嫁给我。」
她噗嗤一声笑了,像是卸下了所有的重担。
「你还真敢说。」
「我有什么不敢的。」我梗着脖子,「你敢说,我就敢听。」
她看着我,眼睛在夜色里闪着光。
「那你……可要努力考上市一中啊。」
「一言为定。」
那晚的月亮很圆,月光洒在回家的路上,像铺了一层薄薄的霜。
我骑着车,心里却像燃起了一团火。
为了那个虚无缥缥的约定,为了能和她站在同一片天空下,我第一次,有了想要拼命努力的念头。
5
那是我人生中最努力的三个月。
我戒掉了小说,戒掉了游戏,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我把英语单词贴满了床头,把物理公式写在了手心。吃饭的时候在背历史,上厕所的时候在想数学题。
我妈都觉得我魔怔了,偷偷问我爸,我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憋着一股劲。
那股劲,叫林响。
我时常会想起她在路灯下的眼神,想起她说「那你可要努力考上市一中啊」时的语气。
那句话,像一根鞭子,在我懈怠的时候,狠狠地抽在我的心上。
出成绩那天,我紧张得手心冒汗。
当我在查询网站上,看到「市一中」三个字出现在录取学校那一栏时,我几乎要跳起来。
我做到了。
我第一时间就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响。
我冲到她家巷口,却看到一辆搬家公司的卡车停在她家门口。叔叔阿姨和几个工人,正往车上搬着家具。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看到林响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抱着一个纸箱。
她也看到了我。
她的表情有些复杂,有惊讶,有不舍,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歉意。
「你要……搬家?」我艰难地开口。
她点点头:「嗯,我爸工作调动,我们全家……都搬去市里。」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原来,无论我考不考得上,她都注定会离开。
原来,我拼尽全力的追赶,从一开始,就只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什么时候决定的?」我的声音有些干涩。
「中考前就定了。」她低着头,「我……一直没找到机会跟你说。」
我还能说什么呢?
说我为了你,头悬梁锥刺股?说我以为我们还能在同一所学校,继续那段没走完的路?
这些话说出来,只会显得可笑和幼稚。
我们都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可以在槐树下肆意许下诺言的年纪。生活有它自己的轨迹,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约定而改变。
「挺好的。」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以后就是城里人了。」
她没说话,只是把怀里的纸箱抱得更紧了。
搬家公司的卡车发动了,发出沉闷的轰鸣。
「我要走了。」她说。
「嗯。」
「到了市里,我给你写信。」
「好。」
卡车缓缓开动,她上了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车窗摇下来,她探出头,对我挥了挥手。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卡车越开越远,直到消失在巷子的尽头。
空气里,仿佛还残留着一丝槐花的香气。
只是这一次,那味道里,多了一丝苦涩。
6
高中的生活,和我想象中一样,又不太一样。
市一中很大,很漂亮,有我从未见过的图书馆和体育馆。这里的同学,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都很多才多艺。
我像一颗被扔进大海的石子,激不起半点浪花。
我收到了林响的第一封信。
信纸是淡蓝色的,带着一股好闻的墨水香。她的字很娟秀,就像她的人一样。
信里,她讲了她在新学校的生活。她的新同学,她的新老师,还有市里那些我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
她说她很想念小镇,想念那棵老槐树,想念……槐花饼的味道。
我回了信,给她讲我的高中生活,讲我交了哪些新朋友,讲我们篮球队又赢了比赛。
我们像两个交换日记的笔友,用最原始的方式,分享着彼此的青春。
信件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那段日子,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去收发室看有没有自己的信。每一次看到那个熟悉的、写着「周扬(收)」的信封,我的心都会漏跳一拍。
我会把她的信,翻来覆去地看很多遍。揣摩她写下每一个字时的心情。
我们聊过去,聊现在,却很有默契地,避开了未来。
那个关于「长大就嫁给你」的约定,也再没有被提起过。
它像一颗被埋进土里的种子,在看不见的地方,不知道是已经腐烂,还是在悄悄地生根发芽。
高二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我收到了她寄来的一个包裹。
打开一看,是一条灰色的围巾。手工织的,针脚算不上细密,甚至有些歪歪扭扭。
包裹里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
「天气冷了,注意保暖。这围巾我织了很久,别嫌弃。」
我把围...巾围在脖子上,很暖和,带着一股阳光的味道。
我能想象出,她坐在窗前,笨拙地摆弄着毛线针的样子。
我的心,在那一刻,被一种温热的情绪填满了。
我立刻跑到邮局,给她寄去了我们小镇最有名的特产,酱板鸭。
我想,我们之间的那根线,并没有断。它只是被拉得很长,很长,但依旧坚韧。
高考结束,我填了南方一所大学的志愿。
而林响,则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校。
我们之间的距离,从三个小时的车程,变成了一千多公里的路途。
我们开始用起了QQ和手机,联系变得方便了许多,但不知为何,心与心的距离,却好像更远了。
在QQ上,我们聊天的内容,渐渐从日常琐事,变成了「在吗」、「吃了没」、「早点睡」这样的客套话。
打电话时,也常常会陷入尴尬的沉默。听着听筒里彼此的呼吸声,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们都有了新的生活,新的圈子,新的朋友。
她会和我说起她们学校的樱花节,说起她参加的辩论社,说起那些我完全不了解的人和事。
我也会和她讲我们学校的卧谈会,讲我和室友们通宵打游戏,讲那些她可能并不感兴趣的笑话。
我们都在努力地向对方的世界靠近,却发现,彼此的世界,已经有了无法逾越的壁垒。
大二那年暑假,我回了一趟小镇。
那棵老槐树,因为学校扩建,已经被砍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崭新的实验楼。
我站在原地,怅然若失。
好像心里某个重要的东西,也跟着那棵树一起,被连根拔起了。
我给林响发了条短信:「我们学校那棵槐树,被砍了。」
过了很久,她才回复:「是吗?真可惜。」
短短的五个字,客气,又疏离。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怀念的,或许并不是同一棵树。
我怀念的,是那棵树下的少年时光,是那个仰着头看我的女孩,是那句掷地有声的承诺。
而她怀念的,或许只是槐花饼的香甜。
仅此而已。
那年冬天,我没有再收到她织的围巾。
那年春节,她也没有回小镇。
我们的联系,渐渐地,就断了。
QQ头像变成了灰色,再也没有亮起过。手机号码,也成了一串躺在通讯录里,再也不会拨出的数字。
我们就像两艘在黑夜里航行的船,有过短暂的交汇,然后,便朝着各自的航向,渐行渐远,消失在茫茫的海雾里。
再次见到林响,是在十年后的一场同学婚礼上。
婚礼办得很热闹,在小镇最好的酒店。很多年没见的同学都来了,大家推杯换盏,聊着各自的近况。
我被几个老同学拉着灌酒,聊着工作,聊着家庭,聊着那些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梦想。
就在我喝得有些微醺的时候,一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回头,看到了她。
她瘦了些,头发烫成了时髦的卷发,脸上化着精致的淡妆。穿着一条得体的香槟色长裙,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成熟、干练的气质。
和记忆里那个穿着蓝色连衣裙、扎着麻花辫的女孩,判若两人。
但只一眼,我还是认出了她。
「林响?」我有些不确定地叫出她的名字。
她笑了,眼角的细纹清晰可见。
「周扬,好久不见。」
那一瞬间,我有些恍惚。
十年,原来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我们被安排在同一桌,身边坐着一群已经不太叫得出名字的同学。
大家都在高声谈笑,只有我们之间,隔着一层尴尬的沉默。
还是她先开了口。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
「在省城,一家设计公司。」
「哦,挺好的。」
「你呢?还在北京?」
「嗯,在一家外企做HR。」
「那也很厉害。」
对话简短,客套,像两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
我们聊了聊新郎新娘,聊了聊小镇的变化,聊了聊各自的家庭。
我知道了她已经结婚,丈夫是她的大学同学,在北京有房有车,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她也知道了,我有一个谈了三年的女朋友,准备明年结婚。
我们的人生,都在按部就班地向前走着,只是,彼此都不在对方的轨道上。
婚礼进行到一半,司仪开始搞气氛,让大家上台分享和新人的趣事。
一个喝多了的男同学,突然指着我们这边,大声喊道:
「说到趣事,我可得说说周扬和林响!你们还记得不?当年周扬爬那么高的树,林响在底下喊,说要嫁给他!」
全场哄堂大笑。
我的脸,瞬间烧了起来。
我下意识地去看林响,发现她的脸也红了,但不是害羞,而是一种略带尴尬的局促。
她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笑着对大家说:「小孩子不懂事,瞎说的,大家别当真。」
她的丈夫就坐在她旁边,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他揽过林响的肩膀,半开玩笑地说:「那可不行,这辈子你可是我的了。」
大家又是一阵善意的哄笑。
我端起酒杯,将杯里的白酒一饮而尽。
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像一把火,烧得我五脏六腑都疼。
我终于明白,那个夏天,连同那棵槐树,那个承诺,都彻彻底底地,死掉了。
它死在了时间的洪流里,死在了我们各自奔忙的人生里,也死在了她那句云淡风轻的「瞎说的」里面。
婚礼结束后,我一个人走到酒店外面的花园里。
夜风很凉,吹散了些许酒意。
我点了一根烟,看着烟雾在夜色里袅袅升起,又很快消散。
身后传来高跟鞋踩在石子路上的声音。
是林响。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她问。
「出来透透气。」
我们在长椅上坐下,隔着一个人的距离。
「刚才……不好意思啊,」她说,「没想到李伟会提那件事。」
「没事,都过去了。」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本来就是句玩笑话。」
她沉默了。
良久,她才幽幽地开口:「其实……也不全是玩笑话。」
我愣住了。
「那时候,我是真的怕你从树上掉下来。」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脑子里一热,就那么喊出来了。」
「后来,我给你写信,给你织围巾……其实心里,一直都记着那句话。」
「我总在想,等我们上了大学,毕了业,稳定下来……也许……」
她没有说下去。
但我都懂。
只是生活,从来都不会按照我们写好的剧本上演。
我们都太年轻,年轻到以为一句承诺,就能抵得过千山万水的距离,抵得过似水流年的冲刷。
「我老公,对我很好。」她忽然换了个话题,语气里带着一丝幸福的暖意,「他很踏实,也很有责任心。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他帮我占过座,我请他喝过奶茶,一来二去,就在一起了。」
「我女儿很可爱,眼睛像他,鼻子像我。她最喜欢听我讲故事。」
她说的这些,都很平淡,很琐碎,却是我从未参与过的,属于她的十年。
「挺好的。」我说。
这是我今晚,对她说的第三遍「挺好的」。
每一次,都发自真心。
「你呢?」她问我,「你女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了想,说:「她很爱笑,有点迷糊,做饭很好吃。我们……打算明年春天就结婚。」
「那也挺好的。」她也笑了。
我们相视一笑,像是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友,在为对方的幸福,感到由衷的高兴。
那些曾经的悸动,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情愫,那些被时间尘封的遗憾,在这一刻,都化作了释然。
我们都没有错。
只是,在人生的某个岔路口,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然后,遇见了不同的人,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那棵槐树下的约定,就像一场年少时的梦。
梦醒了,我们都得回到现实,继续自己的人生。
「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她站起身。
「我送你。」
「不用了,我老公在门口等我。」
她朝我挥挥手,转身离去。高跟鞋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渐行渐远。
我坐在长椅上,又点了一根烟。
我想起很多年前,她也是这样,在巷子口,对我挥手告别。
只是那一次,是开始。
而这一次,是真正的,结局。
10
从那家香水店出来,我的手里多了一个小小的纸袋。
里面装着那瓶,有着槐花味道的香水。
我没有打开它,只是把它放在了书架的最深处,和我那些泛黄的旧信,放在一起。
生活依旧在继续。
我和女朋友结了婚,在省城买了一套不大不小的房子,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阳台。
春天的时候,我会在阳台上种一些花花草草。
妻子问我,为什么不种一棵槐花树。
我说,阳台太小了,种不下。
其实,我知道,有些东西,只能活在记忆里。
有些味道,一旦被复刻,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
我偶尔还是会想起那个夏天,想起那棵高大的槐树,想起那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女孩。
想起她仰着头,用尽全身力气喊出的那句话。
那句话,像一颗时间的琥珀,将我整个少年时代最美好的瞬间,都封存了起来。
它无关爱情,无关承诺。
它只是一个坐标,标记着我再也回不去的,那个纯真、热烈、无所畏惧的年纪。
那年我上树摘槐花,她站在树下。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一切,都刚刚好。
读点|时光悠悠,那些吃槐花饭的日子真让我怀念
文|黑王辉
到了春天,故乡的槐花便零零落落开了,转眼之间,竟稠稠密密开满了枝头。望着粉白粉白的花儿,我肚里的馋虫儿就被勾了出来,然后不住咽着口水。
蒸菜里面,我是最喜欢槐花的。像榆钱、婆婆叶、面条菜、红薯叶,我都喜欢吃,但是不上瘾,而槐花,吃着是能够让人上瘾的,吃了还想吃,总也吃不够。那种香喷喷、甜丝丝的感觉,让我胃口大开,直到把肚子吃得鼓腾腾的还意犹未尽。
我小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就出去打工了,只在过年时才回来一次。短暂相聚之后,过完年,便又匆匆上路了,留下我和爷爷,相依为命过着日子。
爷爷很疼我,他赶集打面榨油的时候,总要给我捎回来一些吃食。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爷爷在一旁慈祥地笑着,用他那粗糙的大手摩挲着我的头。
我意识到什么,拿出油条,说爷爷你吃,爷爷摇摇头,说你吃吧,爷爷不喜欢吃油腻的。
我硬把油条塞到他嘴里。
爷爷笑了,说,你这傻小子!
春天一来,我就嚷着缠着爷爷去勾槐花给我吃。爷爷找来一根长竹竿,把镰刀绑在竹竿上,扎死、捆紧,以防镰刀掉下来。然后走到槐树下面,瞅准花开得密并且枝子不粗的一束,用镰刀一划,带花带叶的树枝便飘落下来。
我欢喜地跑过去,用手捋槐花,由于花比较多,一捋就是满满一手。不一会儿,就能捋个半篮子。
回到家里,我烧火,爷爷打水淘洗槐花。槐花捞起时,泛着湿漉漉的清香,我忍不住,抓了一把塞在嘴里,大嚼着。
爷爷哈哈大笑,他给槐花拌了面,洒上盐水,摊在箅子上。这时,水基本上也烧温了。等水烧开冒着冉冉蒸汽的时候,我就急不可耐,要掀开锅捞出来吃,却被爷爷阻止了。他说,焖一会儿,蒸透了再吃。
几分钟以后,爷爷把蒸好的槐花从锅里盛出来,浇上捣碎的蒜泥,再淋些香油,就可以吃了。
我盛一大碗端给爷爷,爷爷说你先吃。
我说你先吃吧,我再盛。
说着,我又盛了一碗。我们俩就坐在门槛上吃起来。
时光悠悠,那样的日子真让我怀念。
我稍稍大了些,爷爷也渐渐老迈,他已经拉不动树枝了。再捋槐花的时候,我就爬上树,从树上折断树枝,扔给爷爷,他坐在树下捋。
我问爷爷够吗?爷爷说够了够了,也留些给别人,我便“哧溜”一下从树上溜下来。
爷爷看着我笑,说真像我小时候。
能跟爷爷小时候一样,我觉得很高兴。
爷爷老去的速度让我们都意想不到。那年,爷爷竟然患上了食道癌,吃不下东西,每天只能喝一些稀粥。还好,那时父亲和母亲都已经回来,留在家里照顾他。
春天来临的时候,院墙内外开满了白色的槐花。我去看爷爷,他指了指窗前的槐树,笑了。
我会了爷爷的意,赶紧爬上树,捋了些槐花,让母亲蒸熟,我端给他。爷爷嗅了嗅,吃了两口,噎得脖子脸通红,不住地咳嗽着。我连忙拍他的后背,才终于吐了出来。
我呜呜哭着,爷爷也老泪纵横。
终于,他没能熬过那个春天,永远去了。
又是春天,槐花稠稠密密堆在枝上。槐花凋零以后可以再开,而我亲爱的爷爷,一去之后永远就不再回来了。
吃着自己蒸的槐花,突然就觉得没有了那时的味道。
(壹点号 读点)
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不代表齐鲁壹点立场。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