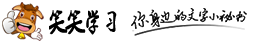手把手教你写《楚辞摘录读书笔记》,(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29 22:14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楚辞》摘录的读书笔记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内容充实、结构清晰、见解深刻:
1. "明确核心:聚焦摘录内容"
"选材精准:" 仔细选择你想要摘录和分析的《楚辞》篇目或诗句。确保所选内容具有代表性,能够体现《楚辞》的某个特定主题、艺术特色或思想情感(如浪漫主义、爱国情怀、对自然的描绘、哲学思辨等)。
"摘录清晰:" 将选定的原文摘录清晰、准确地呈现出来,可以使用引用格式(如加引号)。确保没有错漏。
2. "深入理解:把握内涵"
"背景知识:" 了解《楚辞》产生的时代背景(战国时期,特别是楚国)、作者屈原的生平遭遇和思想情感、以及《楚辞》独特的文学风格(楚辞体,如运用香草美人、神话传说、长短句、楚地方言等)。
"逐句/逐篇解读:" 对摘录的内容进行仔细研读,理解字面意思,更要挖掘其深层含义、象征意义和情感色彩。思考作者想要通过这些词句表达什么?
3. "结构清晰:逻辑严谨"
"引人入胜的开头:" 可以从《楚辞》的整体魅力、你所选
穿越千年风云,《楚辞》的编订奇谭:一场诗魂的“炼金术”
一、引子:千年前的“诗人大战”——《楚辞》的神秘面纱
如果你以为古代文学只是枯燥的文字堆砌,那你就out了!《楚辞》这部作品,既是诗人们的“狂欢派对”,也是文化史上的“奇幻冒险”。它像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战国时期的文化天空,却也经历了无数次“洗牌”和“炼金术”。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部“诗魂宝典”的神秘面纱,聊聊它的编订过程——一场跨越千年的“编辑大作战”。
二、《楚辞》的起源:天马行空的诗意天地
先说说它的“血统”。《楚辞》并非一部单一的作品,而是由许多诗歌、传说、神话、杂记拼凑而成的“文化拼图”。传说中,最早的“楚辞”由屈原、宋玉、贺知章等人创作,但实际上,直到战国后期,这一“作品集”才逐渐成型。
在那个战火纷飞、诸侯争霸的年代,楚国的诗人们像一群“文化狂人”,把对国家、对生命、对天地的感悟都写进了诗里。于是,“楚辞”逐渐成为楚国文化的“代名词”。
三、编订的“幕后故事”:从零到一的奇幻之旅
那么,这些散落在各地的诗歌是怎么变成一本“正式的作品集”的呢?这就像一场跨越千年的“编辑奇谭”。
1. 早期的“草稿”——零散的诗歌碎片
最初,楚国的诗人们只是随手写写,诗歌像是流动的云,飘在民间和宫廷之间。这些诗歌大多散见于竹简、帛书、铭文,形式各异,内容丰富。有的诗歌还带有神话色彩,有的则直抒胸臆。
2. 传承与整理——“编辑者”的出现
到了战国中后期,楚国的文化学者开始意识到,这些零散的诗歌如果不整理,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散失。于是,他们扛起了“整理大旗”。
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的“楚辞编辑者”其实就是一些“文化猎人”,他们在各地搜罗、摘录、整理这些诗歌。最著名的“编辑者”之一,或许就是后来被尊为“楚辞之父”的屈原。
3. 采集、筛选、润色——“炼金术”般的编辑过程
这些“编辑者”在整理过程中,不仅仅是简单地把诗歌拼凑在一起,还进行了大量的润色、补充和改写。为了让作品更具“整体感”,他们可能还加入了神话故事、寓意解释,甚至“增添”了一些自己的创意。
这就像一场“炼金术”,把普通的诗歌碎片变成了璀璨的文化宝藏。
四、《楚辞》的成书与流传:一部“文化奇书”的诞生
经过一番“炼金术”般的编辑,《楚辞》逐渐成型。最早的版本大约在战国晚期出现,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了祭祀、神话、爱情、政治等诸多主题。
随后,随着秦汉时期的“书籍整理运动”,《楚辞》被逐渐整理、校订,成为“楚文化”的代表作之一。汉代的学者们对《楚辞》的研究更是深入,他们不仅保存了原有的作品,还不断添加注释、解读,让这部作品得以流传千年。
五、现代“再编辑”:从古籍到现代解读
到了今天,关于《楚辞》的“编订”已经不止于古人之手。现代学者们如同“文化炼金师”,不断对《楚辞》进行校勘、整理、注释。
《楚辞》的版本繁多,有《九歌》《远游》《九思》等经典,也有各种注释本、译本、研究集。每一次“再编辑”,都让这部古老的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六、趣味点缀:编订背后的“趣事”与“趣味”
你知道吗?在《楚辞》的编订过程中,也不乏一些“趣味事件”。
比如,有学者曾试图“还原”《九歌》的原貌,结果发现,很多“神话”故事在不同版本中竟然“互相打架”!有人调侃:“这就像古代的‘神话大乱斗’!”
还有一些“段子”流传:有人说,屈原在整理《楚辞》时,曾经因为“诗稿太多”,一度“心情郁闷”,甚至“差点”把自己写的诗稿“全扔了”。幸好,他的好友们及时“出手相救”,才让这部“诗魂宝典”得以留存。
七、结语:穿越千年的“诗魂”之旅
从零散的诗歌碎片,到战国的“炼金术”,再到今天的“版本大战”,《楚辞》的编订过程,宛如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奇谭”。它不仅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是后人不断整理、解读、创新的结晶。
每当我们翻开《楚辞》,仿佛能听到那千年前楚地的风声,感受到诗人们那炽热的情感。它像一条穿越时空的“文化隧道”,带领我们领略那个充满神话、爱情、理想与悲怆的楚国世界。
后记:让我们为那些“炼金术师”们鼓掌!
正是他们的努力,让这部古老的作品得以流传千年,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未来,我们也许会用更现代的“编辑工具”去重新解读它,但那份“诗魂”永远不会变。
所以,下次翻开《楚辞》,别忘了,这不仅仅是一部诗集,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炼金术”奇谭!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记得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这段“诗魂奇谭”!下次我们再聊古代那些“神奇的编订故事”,敬请期待!
伏俊琏 | 写本时期文献的摘录和附益
摘 要 : 春秋之前的写本文献主要是“官府文献”,其功能是“典藏”,用于国家重要典礼或贵族的“六艺”教育。战国以来,用于士人交流的“非官府文献”开始流行。这类文献在文本形态上的主要特征是它的流动性,而摘录和附益是流动性的主要表现形式。摘录,就是对已有文献选择抄录和改写。附益,则是在原文献前面、后面或中间增加相关内容。写本时期由于使用情境的改变、使用方式和使用目的不同,文本的功能随之变化,从而引起文本形态和文体特征的改变。 关键词 : 写本时期;文本形态;摘录和附益;文体变化 本文所说的“写本时期”,指北宋之前主要以抄写形式记录文化的历史阶段,可分为简帛写本时期(先秦到5世纪)和纸写本时期。“文本”,指某种载体(如简牍、绢帛、骨片、砖石等)上面刻画的文字、符号或图像;“文献”指有意义的文本、图像等;而狭义的“文献”则指自具首尾、意义大致完整的文字文本。 简帛写本时期,又可分为先秦时期和汉魏晋时期两个阶段。先秦时期,春秋之前的文献主要是“官府文献”,由于最早的文字是沟通人与神的符号,因而早期文献具有神秘性和神圣性,由有特定身份的祝、巫、史掌管,他们或传示神的意旨给人,或把人的愿望上达神灵。现在所见最早的文献是甲骨卜辞,它只是早期官府档案的一部分。留存至今作为“书籍”的先秦官府文献是“五经”(《诗》《诗》《礼》《易》《乐》),它的主要功能是“典藏”,其使用限于国家重要典礼或贵族的“六艺”教育。 春秋中期以来,私学大兴,百家自由争鸣,文本的制作、文献的传承和交流也更为便利,私家著述渐次流行,“非官府文献”因此生成并广为流传。 “口传”是早期文献的主要流通方式,商末周初箕子佯狂而歌,用“唱诵”的方式把《洪范》传给周人,就是典型的例证。《诗经》中的部分诗,尤其是《雅》诗和《颂》诗,本是神圣祭祀仪式上的歌辞,较多地保留了原始形态。《左传》《国语》明显带有瞽史讲诵的特征,二书的作者都传为左丘明,可见左丘明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以讲诵形式传承历史的“瞽史”左丘氏。文献由口传而“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是其形态的固定化,甚至脱离了它的现场语境,但书于载体可以使其超越时空,咫尺之内,获得流布千里、传之后世的效果。 早期文献载体的容量大都比较小,像甲骨卜辞,已知最长也就一百余字,如《甲骨文合集》137号所录武丁时期的一片卜辞,刻于龟甲的正背面,有三段文字,过去的研究都作为三则独立的卜辞,后经黄天树研究,认为三则验辞记录的文义前后相连,实为一篇卜辞,字数达154字,“是目前所见字数最长的一篇卜辞”。最长的钟鼎铭文是2003宝鸡出土的逨盘,记载单氏八代辅佐十一代周王的家族史,有铭文372字。其他如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西周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291字,藏于陕西宝鸡周原博物馆的周恭王时期的“史墙盘”铭文284字。 甲骨文是殷商时期(少数为西周时期)王朝贵族用以占卜的记录,金文则主要是西周时期铸于青铜器上的铭辞,用于祭祀之用,具有纪念碑性质。据文献记载,殷商时期已经有《书》《志》等典籍,这些典籍是用简册作为载体的,《尚书·多士》记载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和“典”就是以简牍为载体的书籍。甲骨文中有“册”“作册”,“作册”是书写的史官。相较于甲骨文和金文,简牍容量就大多了。至今尚未出土殷商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简牍,无法直接了解当时简册的大小。但传世文献中这一时期文本大致可以证明,如《尚书》中“诰”“誓”类文献,字数都不多,以今传本统计,《胤征》约310字,《汤誓》约180字,《仲虺之诰》约410字,《汤诰》约310字,《伊训》约420字,《高宗肜日》约110字,《西伯戡黎》约160字,《微子》约290字,《牧誓》约320字,《酒诰》约850字,《梓材》约320字,《蔡仲之命》约310字,《君陈》约450字,《毕命》约560字,《康王之诰》约340字,《文侯之命》约270字,《费誓》约230字,《秦誓》约310字。长一点的像《太甲》不足800字,《说命》不足千字,《泰誓》千余字,都分为上中下三篇;《尧典》约1600字,后来分为两篇(《尧典》《舜典》),成书时间当在战国时期;《盘庚》约1600字,分为上中下三篇。《禹贡》约1550字,考虑到本篇内容是分别介绍九州的面积、水利、土质、赋税、进贡的物品和贡道路线等,本来是作为九篇,原始文本当成书于西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有所增订。《洪范》约1340字,因为是陈述治国大法,所谓“洪范九畴”,所以也应当是九个部分。 今本《逸周书》各篇的字数也不长,列表如下(见表1)。 现存《逸周书》残字少句的情况比较多,以上的统计仅说明大概。各篇成书的时间不一样,而千字以下的短章大都是春秋早期之前成书的。千字以上的篇章多数是官府的“秘籍”:《世俘解》《时训解》《谥法解》《官人解》虽成书于西周时期,但都是“法令”类要籍。《史记解》据本书《后序》作于穆王时,为左史戎夫所作。《周祝解》“通篇悉为韵语,似铭、似箴,盖直开老氏《道德》之先,匪特作荀子《成相》之祖”。《武纪解》是兵书,清代学者认为是《太公》的逸篇。《王会解》铺排描写周王会合诸侯于明堂的盛大场景,清人认为是西周晚期“追想盛事”之作。这些都是官府的“宝训”。《太子晋解》作于周灵王时期(春秋中后期),是用“五称而三穷”(五打三胜制)问答比赛形式写成的一篇论辩体俗赋。因此,春秋之前的文章,每篇以数百字为多,这也是一件写本的容量;超过千字的文章,是国家的法令要籍,是典藏类文献。 战国时期,私学兴盛,私家著作大量涌现,文章的篇幅也加长。像《孟子》7篇,《梁惠王》有5100多字,《公孙丑》4800多字,《滕文公》近4800字,《离娄》4500多字,《万章》近4900字,《告子》近5000字,《尽心》近2400字。我们根据出土的战国简牍推测,流通领域(与“典藏”相对)的简牍写本,以编连40至60枚简的比较多。按一般一枚简抄写40—60字计算,一件写本长则可抄3000多字,短则千余字或数百字,而“牍”“方”上的文本更短。所以《孟子》7篇都要分为上下篇,也就是说,每篇抄在两件写本上。《老子》五千言,也抄在两件写本上,分为上下篇。《庄子》内篇,《逍遥游》约1300字,《齐物论》约2700字,《养生主》500多字,《人间世》2800多字,《德充符》1700多字,《大宗师》近2800字,《应帝王》1000字多一点。学术界一般认为,《庄子》内篇为庄周自著。庄周与孟轲是同时代的人,但庄周是一位自由独立的学者,且有隐士的风格,不像孟子有弟子随从,更没有万章那样的学生作为合作著述者,所以庄子文章较孟子短小。而最长的《齐物论》《德充符》,本不是原来的规模,是汉代以后增补上去的。如《齐物论》有“夫道未始有封”一章(今本存220字),《音义》引崔譔云:“《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班固时流传的《庄子》是52篇,此章不仅没有在《齐物论》中,而且不在《内篇》。可见《庄子》《孟子》的成书有较大差别。《荀子》《韩非子》中,有荀卿、韩非自著者,有后学的材料汇编。可以确定为荀子自著的《劝学》《修身》《不苟》《非相》等篇,都在1500百余字。《韩非子》中,他自著的《说难》1400多字,《孤愤》1600多字,是标准的战国文章长度。《五蠹》4700多字,是五部分的组合,每一部分抄在一件写本上。《说林》《储说》是“说”类材料的汇编。《说林》约6800字,分上下篇。《储说》篇幅多达36000多字,分为《内储说上》《内储说下》《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6篇,每篇约6000多字,篇中有诸多小标题,可见由很多小篇章组成,有一个渐次编集的过程。日本学者太田方说:“内外、左右、上下,非有他义例,以简编重多故耳。”到汉代司马迁著《史记》“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则每篇4000多字。简牍写本时期一件写本的规模,大致如此。因为当时文献以单篇形式流传,以若干“单篇”组成一部“成书”,事实上仍以“单篇”(一件写本)为流传的基本单位,“单篇”之间的次序最易紊乱,所以,孔子整理五经就是从讨论序次开始:《书》有序,《诗》有大小序,《易》有《序卦》。排序,讨论全书内部次序的合理性,是我国最早的学术研究范式。 摘录,就是对已有文献选择抄录,或根据自己的需要抄录。书籍由官府走向一般士人,主要由于全社会、尤其士人阶层的“书籍崇拜”。“书”是西周贵族教育的“六艺”之一,掌握了书,就可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读书就成为他们重要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方式。读书是为我所用,自己需要什么就抄什么。同样的书,一个人的抄本不同于另一个人的抄本,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抄录同一种书,也可能不一样。 我们用早期《老子》的流传写本进行说明。根据出土文献,《老子》是战国秦汉时期流传很广的书籍。近50年来,出土了六种《老子》的早期写本: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三件战国中期的竹书,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两件西汉早期帛书,2009年北京大学收藏西汉中期的竹书。郭店楚简《老子》有三组,简本的字迹相同,当为同一佣书人所抄,所抄内容没有重复,也没有标题。第一组的重点是探讨道与修道,第二组的重点是修道和道在社会中的运用,第三组的重点是道在社会中的运用。在“修道”的意义方面,第一组和第二组关系密切,在“道的运用”意义方面,第二组与第三组关系密切。这三组《老子》与今本差异较大。 ▲郭店楚简《老子》(荆门市博物馆藏 ) 这三组《老子》出土后,学术界流行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就是认为从战国到西汉前期,是《老子》成书的几个重要阶段。楚简本是《老子》早期的形态,与《史记·老子列传》所载老聃相对应,是老聃口述的传本;帛书本和汉简本是《老子》定型之后的抄本,与《史记·老子列传》所载老莱子、太史儋有关系。这实际上是认为《老子》成书于西汉时期。李学勤认为,《老子》一书,在战国早期已经定型了,楚简《老子》的三个写本都是《老子》的摘抄本。我们读李先生的论证,再看其他学者的讨论和补充,认为这种说法是符合史实的。 《老子》是战国早期“养生”格言的汇录,因为春秋以来,战乱频仍,人的生命危如悬卵,《庄子》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人人都生活在神射手后羿的射程之内,“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敏感的士人自然会思考全身远祸的方法。而《老子》中“道”“德”正是这种方法的高度凝练。到了汉初,道家与黄老思想相结合,成为王朝倡导的意识形态。马王堆出土两种帛书《老子》,甲乙本都和相关文献抄录在一个写本上。甲本抄有《老子》《五行》《九主》《明君》《德圣》五篇作品,研究者认为“当抄写于汉初高祖之世”。乙本抄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老子》五篇作品,研究者认为“抄写年代可能在文帝时期”。由甲乙本所抄《老子》内容和同抄文献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战国楚简《老子》的主旨是个人“生存之道”,则帛书《老子》的主旨已经转变为“君人南面之术”。 山东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书《王兵篇》,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一篇早已散佚的作品,但是在今本《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等篇中可以找到《王兵篇》中的部分段落和大量内容。因此,可以认为,《王兵篇》是一篇较为完整的作品,《管子》各篇是摘录《王兵篇》而形成的新文本。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也很典型。《春秋事语》抄写在24×7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字体为古隶书,处在由篆变隶之间,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当是秦末的写本。存文16章,每章都提行另起,前面有墨点分界。纪事的年代从鲁隐公到三家分晋,与《左传》相当。所记史事除两件外,其余都可以在《左传》《管子》《史记》《公羊》《谷梁》中找到线索,尤其与《左传》关系最为密切,帛书《春秋事语》16章中有15章的叙事见于《左传》。如帛书第十章《吴人会诸侯》一章,与《左传·哀公十二年》“鲁哀公会吴于橐皋”一章所叙事相同,《左传》200字,帛书110字。从叙事层次、情节详略、句式词语等行文要素看,帛书是从《左传》简化而来。这种体例的著作,裘锡圭、李学勤都认为可能是《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中《铎氏微》一类的书。《汉志》著录有《左氏微》2篇,《铎氏微》3篇,《张氏微》10篇,《虞氏微传》2篇。这个“微”字很有意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铎椒为楚威王太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微”就是删繁就简,“抄撮”成篇幅短小的书;“微”还有简体短小、持读容易的意思。所以裘锡圭说:“《春秋事语》显然也是这一类著作或其摘抄本。” 古人在摘录的过程中,可能要改写或增加一些成分。这也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重要方法,《史记》中《本纪》《世家》有诸多内容,都是摘录改编前代史书而成。随着书籍篇幅的增大,摘录删节的新书也越来越多。东汉初年,杨终曾“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把52万多字的《史记》删成十余万言,仅摘录了五分之一多。《后汉书·荀淑传附荀悦传》记载,“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辞约事详,论辨多美”。荀悦的自序也说“缀叙旧书,以述《汉记》”。《汉书》有百篇之多,摘录改编成纪年体30篇,还不足原书三分之一,不仅大删削,体例也完全改变,成为另一文体。 六朝以后,摘录的书越来越多。《隋书·经籍志》就著录多种这类著作,史部“杂史”类有“钞撮旧史,自为一书”者,如张缅撰《晋书钞》、葛洪撰《汉书钞》等,子部“杂家”有无名氏《杂事钞》、庾仲容撰《杂书钞》、无名氏《子钞》等,集部“总集类”就更多了:无名氏《集林钞》、沈约撰《集钞》、无名氏《妇人集钞》、无名氏《赋集钞》、谢灵运撰《诗集钞》、无名氏《六代诗集钞》《乐府歌辞钞》《古歌录钞》等,所谓“钞”(抄),都是指摘录删改。 摘录实际上是一种改编,它体现了摘录者的选择取舍标准,比如荀悦《汉纪》对《汉书》有诸多改动,我们举一个与文学史相关者。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载,淮南王刘安入朝,给武帝献上新近完成的《内篇》,武帝“爱秘之”,又“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文中的“离骚传”《汉纪》改作“离骚赋”。颜师古《汉书注》说:“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却认为《汉书》本来就作“傅(赋)”,“传”是“傅”字的形误。“使为《离骚赋》者,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若谓使解释《离骚》,若《毛诗传》,则安才虽敏,岂能旦受诏而食时成书乎?”其实,《汉书》作《离骚传》是对的,《汉纪》改为《离骚赋》错了。这是后人对西汉人的“传体”误解的缘故。西汉的“传”就是“泛论大义”,相当于后世的主题说明,所以《周易》的《系辞》西汉人叫《易大传》。刘安的《离骚传》的主要部分保存至今,就是班固《离骚序》引用的“《国风》好色而不淫”一段,《史记·屈原列传》也全文抄录下来。这明显是“传”体而不是“赋”体,因为赋体首先要押韵。《资治通鉴》对前代史书的摘录、改编,也是这样的,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就是讲他摘录改编的理由。所以,《通鉴》既是一部编年史,也是一部包含着研究和阐述史学发展的史学史。那些《赋集钞》《诗集钞》《六代诗集钞》《乐府歌辞钞》更是在选择中体现对文学的看法,对文学发展史的看法,在精选中体现选录者的思想倾向和审美情感,是古代特有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 ▲ 萧云从绘、门应兆补绘《离骚图·九章·惜往日》(清乾隆四十七年绘本) 附益,就是在原文献前面、后面或中间增加相关内容。附益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对文章作者的追寻。把作者的生平介绍和评论文字附益其上。古典时期,书籍富有神圣性和神秘性,不容易得到,所以读书是一种高级的奢望和享受。读其书,必先思其作者,士人如此,帝王也是如此。秦王政读《孤愤》《五蠹》之书,直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汉武帝读《子虚赋》感慨万端:“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正是《孟子》所说读其书,要知其人。余嘉锡《古书通例》曾说:“司马迁《史记》所作诸子列传,大抵为读其书有所感而发。”这是很有启发性的卓见。《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管晏列传》重点是写管子佚事、管仲和晏婴之间的深厚情谊,概说管子书的重要思想,不像是有意为传记。《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很多学者认为“前后矛盾,首尾错乱”,尤其是中间情绪激动而发为感慨的一节,与人物传记的要求不相符。其实,这是太史公把刘安的《离骚传》附益其中,借以抒发抑郁的激愤感情。司马迁是一个感情容易激动的人,我们读《史记》,总能感受到他感情激越:面对历史上的圣贤英雄,他无限敬仰,读其书也是经常“废书而叹”。对于孔子,他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因此,读其书,记其事,书其感想,附益于原书之上,所谓附骥尾而不朽。 附益的第二种方式是读后感。读后感的方式多种多样,或对原书加以评论,或对原书内容进行总结。对原书评论,有的是引用前人时贤的话进行评论,有的是读书者直接进行评论。先秦书中记载某件事,结尾常用“君子曰”或“孔子曰”加以评论,正是这种方式。比如《左传·隐公元年》引用祭仲评论共叔段居京的事,《隐公三年》有“君子”论周郑交恶、宋宣公知人及石碏谏卫庄公的事情,《隐公四年》记有众仲论州吁、“君子”评石碏大义灭亲事,《隐公五年》有臧僖伯谏如棠观鱼事、“君子”论郑败燕师事,不胜枚举。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的体例是先摘录《左传》等典籍的叙事,再在后面加以评论,评论的文字有时比原叙述史事的文字还要多。如第七章《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 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夫人荡舟,禁之,不可,怒而归之,未之绝,蔡人嫁之。士说曰:蔡其亡乎。夫女制不逆夫,天之道也。事大不报怒,小之利也……是故养之以□好,申之以子□,重以名势,三□□□礼。今蔡之女齐也,为□以为此,今听女辞而嫁之,以绝齐,是□怨以□也……桓公率师以侵蔡,蔡人遂溃。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 从“士说”曰以下,都是评论。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说:“这十六章的文字,记事十分简略,而每章必记述一些言论,所占字数要比记事多得多,内容既有意见,也有评论,使人一望而知这本书的重点不在讲事实而在记言论。这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是一种固定的体裁,称为‘语’。语,就是讲话。语之为书既是文献记录,也是教学课本。” 读后感有时是对原书内容进行总结,这些总结文字可放在前面,类似于现代的编者按或内容提要。《公孙龙子·迹府》篇开头第一段: 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白马为非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则形不当与,言形则色不宜从;今合以为物,非也。如求白马于厩中,无有,而有骊色之马,然不可以应有白马也。不可以应有白马,则所求之马亡矣。亡则白马竟非马。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 《公孙龙子》为后人辑缀而成。《迹府》篇汇集公孙龙子事迹,当然不是公孙自著,弟子后学汇集其师言行于一篇,是战国诸子成书的常用形式。这一段文字,经谭戒甫考证,是东汉桓谭所作,附益在《公孙龙子与孔穿相问难》一篇前,同抄在一件写本上,构成一个整体。 以上两种附益的方式与原文融为一体,不容易判断。周秦诸子书中有一些内容是记载著者身后之事,这些都是后世读其书者的附益,但宋以后的学者,常借这类附益的材料判定原书是后世所作,甚至判为伪书,这是需要细致研究的。 附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一篇独立的文章附在后面,形成一题多篇的形态。《逸周书》中的《王会》篇,记成王盟会诸侯之盛典,是一篇典型的官府秘籍。此篇当为西周后期史官四散带到民间,而写本的制作者在抄录完此篇后,又把内容相类的《伊尹朝献》抄在其后,这件写本就包括了记载周朝盛典的《王会》和记载商朝盛典的《伊尹朝献》两篇。但读者很早就发现本非一篇,所以有标注:“《伊尹朝献》,《商书》,不[在]《周书》,录中以事类来附。” 今本《荀子》有《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隐”和一篇《佹诗》。这两组作品,作于不同时期,第一组“隐”作于齐宣王在位荀子初至齐稷下之时,第二组诗作于荀子初次到楚国任兰陵令,又离开楚暂至赵国期间。附“诗”于“隐”之后,是因为这两组作品都是韵诵体,符合“不歌而诵”的形式标准。《荀子·尧问篇》通过历史事实的叙述,表现治国理念,如选贤任能、明辨是非、赏罚分明、以身作则和重视教育等原则,但末尾有“为说者曰”一段,用四言韵语的对话体形式论辩“荀子不及孔子”,感情激动,愤世嫉俗,是荀子弟子为其师护法的“杂赋”附益于正文之后者。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 2022年) 《韩非子》的第二篇《存韩》,是韩非子到秦国后给秦王政上的书,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存韩》包括三篇文章:韩非子给秦王政的上书,李斯给秦王政的上书,李斯给韩王安的上书。李斯的两篇上书附在韩非《存韩》篇之后,要理解《存韩》,李斯的两篇上书至为重要。三封书是完整的一个整体,但题目是《存韩》篇,作者是韩非子,后面两篇是附益。 这种附益的篇章,如果没有明确的标志,最易混淆。如《庄子》这部书,《汉书·艺文志》著录52篇,今传本是郭象校定的33篇。按篇数计算,汉代以来,《庄子》散佚了19篇。根据考证,一部分所谓散佚的篇章其实并没有散佚,而是后人调整改编时附益在其他各篇中。如其中有一篇《惠施》,《北齐书·杜弼传》记载,杜弼曾“注《庄子·惠施篇》”。今本《庄子》没有《惠施》篇,学者遂断定《惠施》篇散佚了。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老子与庄子》认为,《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或即北齐杜弼所注《惠施篇》”。《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专讲惠子的学说,故武内义雄以为就是杜弼所注的《惠施》,是后人附益到《天下篇》。汉代《庄子》52篇中有《子张篇》,今传本没有此篇,学者以为是散佚了。王叔岷《庄子校诠》发现今本《盗跖》包括《盗跖》和《子张》两篇,是晋人郭象把《子张》附益到《盗跖》篇,变成了一篇新文本。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简本《盗跖》证实王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 ▲《汉书·艺文志》(“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北宋刻递修本 ) 《楚辞》的成书,经过宋玉、刘安、刘向和王逸多位学者的编集,现代学者对此也有深入讨论。其中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往往和文本附益有关。《悲回风》一篇,在《九章》中字数最多,从王逸《楚辞章句》以来都认为是屈原所作,宋代学者开始怀疑屈原的创作权,近现代有学者认为是宋玉、唐勒悼念屈原的作品。但他们都把本篇作为完整的篇章理解。张树国认为本篇从开头到“宁溘死以流亡兮,不忍为此常愁”共48单句为屈原所作;自“孤子吟而抆泪兮”到结尾共62单句为西汉末扬雄所作的《畔牢愁》,是刘歆等整理《楚辞》时附益在《悲回风》之后。与之类似的还有《远游》,《远游》是《楚辞》中的名篇,被文学史家称为“游仙诗之祖”。这首长诗过去都认为是屈原所作,当代学者刘永济、游国恩、胡小石、赵逵夫等讨论了诗中多袭用《离骚》句子的情况,研究了诗中表现的神仙家思想与屈原的作品相抵触,而与秦汉方士飞升之意思相同,并考证诗中出现的仙人“韩众(终)”是秦始皇时期的方士,因而认为《远游》是汉武帝中期之前的作品。在此基础上,张树国考证《远游》的结构,发现这首诗实际上是两篇的组合,从开头到“高阳邈以远兮,余将焉所程”50句,为淮南王刘安的作品;“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到诗的末尾共64句,为扬雄的《广骚》附益到刘安作品之后。虽然,张先生认为《悲回风》为屈原作品附益扬雄《畔牢愁》,《远游》为刘安作品附益扬雄《广骚》,这个结论还可以讨论,但他提出的“附益说”却很有启发意义。 《史记·屈原列传》有“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其中屈原与渔父问答一段,也是附益于史传中,且连接得天衣无缝,要不是《楚辞》中有《渔父》一篇保存至今,我们不会知道它是附益的。《史记·滑稽列传》是汉成帝时褚少孙增补的,其中东方朔“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议论”一段,见于《汉书·东方朔传》,是东方朔的作品《答客难》。若非《汉书》明确标注此文为东方朔所作,我们便无从得知——这其实是褚少孙将东方朔的作品增补于列传之后的附益之作。 出土简牍文献中这种附益的情况比较多,这与当时的写本形制有关。根据近数十年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写本,一件写本上抄录数篇文章者居多。前举郭店楚简中第三组《老子》与另一篇《太一生水》竹简的形制、书体均完全相同,整理者说“原来可能与《老子》丙合编一册”,就是说一件写本抄了两篇文章。但是研究者很少把这两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其实,《太一生水》是附益在《老子》后的文章,就文义讲,它是对《老子》“修道”主题的引伸与发挥,从天道说到人事,环环相扣,等于是《老子》读后感一类的东西。只有把抄在同一写本上的这两篇文章联系起来,才能发现这件写本表现的思维逻辑、贯穿全部的文脉线索、整体主题。 摘抄与附益,是写本时期文献生成的重要方式,它根植于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和方法,表明对既有文化的继承,也包含着丰富的创造性在其中,它本质上是面对既有知识结构,适应社会变动和文化发展而调整的新文本形态。它既是中国文化连续性的基石,因而留下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年轮,埋下了真伪交织的复杂特质。今日重审这些文献,需要以动态眼光审视其层累过程,同时借助考古发现与跨学科方法,捕捉流动的文本中蕴含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真实。 李零曾经这样描述写本时期的文本形态:战国秦汉好像气体,隋唐时期好像液体,宋以后则是固体。文本形态的最终呈现是不同的“文体”,所以写本时期文本形态的变化,是这一时期文体变化的重要标志。使用场合情境的改变、使用方式的不同、使用目的不同,其功能也随之变化,导致摘录、附益、改编等文本形态变化,从而引起文体的改变。 我们以“传”体为例进行说明。先秦时期“传”作为文体,与“经”相对,其功能是解经。战国以来,有经师之“传”,有瞽史之“传”。经师之“传”多讲述“经”的本真之义,流为文体,就是《尔雅》《毛传》这样的典雅训诂体。瞽史之传以讲述故事为主,流为文体,就是《左传》《韩氏外传》这样的故事体。孔子及后学解经时,还使用了一种“泛论大义”的“传”,流为文体,就是《周易系辞》这样的提要体。为了讲诵的音韵和谐、节奏分明,瞽史之传还有一种韵诵体形式,《尔雅》《易传》中还保留了一些。《周易》乾卦《象辞》:“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尔雅·释训》也记录了先秦的“韵语之传”,如:“子子孙孙,引无极也。颙颙卬卬,君之德也。丁丁嘤嘤,相切直也。蔼蔼萋萋,臣尽力也。噰噰喈喈,民协服也。佻佻契契,愈遐急也。宴宴粲粲,尼居息也。哀哀凄凄,怀报德也。”以上就是“传”之四体:故训体、故事体、提要体、韵诵体。 到了西汉中后期,经师把原有的“故训体”和“提要体”编为一体,以《毛诗故训传》为名,学者又简称“毛传”,“传”遂包括“故训”在内。西汉时期,为了标明句读段落,经师以符号划分经文的“章”和“句”,形成“章句”,见于出土的阜阳汉简、安大汉简及海昏侯汉简中的《诗经》简;后来在此章句形式基础上,逐渐增加训诂注释、史事引证和概括章旨,形成与“故训传”类似的“章句”。前述《汉书》称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王逸《离骚经叙》说刘安作的是《离骚经章句》,“传”与“章句”为同一体裁。西汉中后期的“章句”内容繁杂,《汉书·艺文志》说这种章句“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桓谭《新论》讲有一位名叫秦近君的经师,“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真是繁琐至极!这样大的篇幅,在那个以简牍为载体的时代,很难抄录在写本上,只能口头传授。到了东汉中后期,“章句体”逐渐变得简明,赵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 “传”之“四体”本来互有交错,所以“泛论大义”的“传”与集“故训”“传”为一体的“传”易于混淆,最典型的例证是前述王念孙混淆了西汉的“传”体与“训诂”体的不同,认为刘安所作的《离骚传》与“训诂”为同一种文体,断言刘安不可能一天之内完成《离骚传》,他完成的只能是“约其大旨”的《离骚赋》。这里又派生出了“赋”,就是前述之“韵诵之传”,以韵语释经的“传”。《离骚》在西汉受到普遍的喜爱和尊崇,称之为“经”,其解“经”之“传”大致有两种方法:一是模仿其体裁,解释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也模仿屈原的思想情感,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都是这一类;二是对词语的释读,释读的方式,采用的是以诗解诗法。如王逸《楚辞章句》把相关对词语的解释分别安置到对应的原句之下,我们把附益到《抽思》各句之下的句子集辑出来,就成为另一首诗:“哀愤结縎,虑烦冤也。哀悲太息,损肺肝也。心中诘屈,如连环也。”可见,由附益“经”而衍生出来的“传”体,本身又成了一大文类,滋生出了诸多文体。 文体的频繁变化,是应对社会发展变化、知识迭代更替的结果,也是知识储存和传播方式变化的结果。简牍写本时期文体的变化较大,主要原因是由于文本制作和流传的限制,小范围内师弟相传方式的限制。同时由于看重文体的实用功能,势必限制文体对美的追求。东汉以来,纸本的出现,书写载体和容量大为增加,交流也越发频繁,使文化越来越普及,掌握文字的团体越来越庞大,这就要求有共同遵守的规范,这种约定俗成加剧了文体的定型。对审美的追求,加之对受制于现场情境的实用功能的减弱,文体就趋向稳定。所以3—11世纪,不但有相对稳定的文体形式,而且有成熟的文体理论。但从敦煌写本反映的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化看,唐五代时期民间文体非常繁杂。就文学文体而言,除了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说唱文学,例如变文、讲经文、曲子词、俗赋、通俗诗外,还有大量的民俗应用文、宗教应用文,尤其是佛事应用文等。很多是我们在《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传统文体学著作中找不到的。这种应用型文体主要是当时社会下层民俗活动和宗教活动的反映,蕴含着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这种新的文体,是我们认识中古时期民众的精神世界、知识结构、生活追求和审美趋向的弥足珍贵的资料。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中国文体学研究 ” 责任编辑:张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