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推荐《家里的故事 作文》相关写作范文范例(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31 1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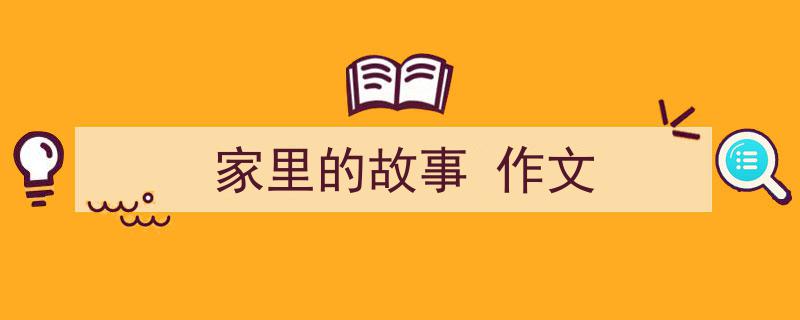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家里的故事,首先要明确你想要表达什么,然后围绕这个核心来组织内容。以下是一些注意事项和建议,希望能帮助你写出一篇感人、生动、真挚的作文:
"一、 构思与立意 (Planning & Theme):"
1. "明确中心思想 (Clarify the Central Theme):" 你想通过这个“家里的故事”表达什么?是亲情之爱、家庭温暖、成长的烦恼、长辈的智慧、某个难忘的瞬间,还是家庭的变化?确定一个清晰的主题,让你的文章有灵魂。 2. "选择合适的切入点 (Choose a Specific Angle):" “家”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不要试图写尽所有。选择一个具体的事件、一个人物、一个场景或者一种感觉作为切入点。比如: "一个具体事件:" 家庭成员间的争吵与和解、一次成功的家庭旅行、一次生病时的照顾、一起做的某件事。 "一个特定人物:" 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中的一个,讲述与他们相关的故事。 "一个特定场景:" 家里的某个角落(如厨房、书房、阳台)、某个节日(春节、生日)、某个习惯(一起吃饭、睡前故事)。 3. "确定故事的情感基调 (Determine the Emotional Tone):" 你希望文章是温馨的、感伤的、幽默的、温暖的,还是带有反思的?基调的统一有助于感染读者。
"二、
“倭寇未灭 誓不生还”:家书里的抗战记忆
作者:张丁(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研究馆员)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关于抗战的档案、文献及口述史料中,家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本是私密的文字,经过战火的摧残,劫后余生,被尘封在一个个家庭中。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随着各种纪念活动和抢救家书项目的开展,那些尘封的记忆被打开,还原了一幅幅关于那个时代的鲜活画卷。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收藏的关于抗战地家书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中国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舍弃个人和家庭的大爱,一次次让我们感动、敬佩。
1932年10月3日,周平民、周健民致父母亲家书。作者供图
周氏兄弟:“为救国而死,是死得光明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到半年,东三省沦陷。1932年,日军重兵进攻上海,遭到中国军队顽强反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掀起了抗日的浪潮。
此时,正在上海的周平民、周健民兄弟,报名参加了“上海青年自愿决死抗日救国团”。两兄弟是四川内江人,哥哥周平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地农民运动的骨干。受哥哥影响,弟弟周健民也走上了革命道路。1930年8月,县委机关遭敌人破坏后,两人秘密前往上海。“决死团”成员在江苏昆山和无锡培训后,于1932年8月北上,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两兄弟随蒙边骑兵队奔赴开鲁抗日前线,被分配在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开鲁办事处工作。10月3日,他们联名给远在四川的父母写了一封家书。信中说,他们已到达热河省重要城市赤峰,当地民众对抗日队伍极其欢迎,资助了枪械、马匹、皮大衣等军用物资。行军途中,健民患病,已经痊愈,两人均不在战斗一线,希望父母不要挂念。信末坦言:“热河边境已失去一大块地,中国前途极为危险。”
1933年2月初,周健民等人随军开赴鲁北前线,由于此次行动被汉奸刺探获悉,周健民不幸中弹牺牲,时年18岁。不久,日寇进犯热河。3月,热河省会承德失守,热河全境沦陷。周平民随“决死团”主席黄镇东赴上海。6月12日,周平民给外甥百均写信,谈到弟弟健民的牺牲:“这回你二舅舅在打日本鬼子的最前线死去,他为救国而死,是死得光明的……以后努力读书,将来长大了,好替你二舅舅报仇。杀完日本鬼子汉奸叛逆,把已失的东北四省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手中夺回来,以完成你为救国救民而牺牲的二舅舅的遗志。”同年冬,周平民赴南京投考军事学校,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9月14日,吴瑞致父亲家书。作者供图
吴瑞:“决心与倭寇拼命到底”
日军占领热河后,觊觎华北,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重,爱国学生发出呐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36年3月9日,贵州省三穗县滚马乡下德明村的23岁青年吴瑞离别家人,报名从军。经过训练后,吴瑞被编入陆军13师34团2营4连。“七七事变”后第八天,正在汉中留坝县驻防的吴瑞,给两位哥哥写信,介绍了敌我在北平的冲突,表示:“我师现驻斯地,一方面赶筑飞机场,一方面积极准备。但将来能不能北上与倭奴一拼,还是惟命是从。如果本师北上,临行再告。”
不久,13师接到了赴沪抗日的命令。9月14日夜,在行军途中,吴瑞自知此去上海凶多吉少,提笔给父母双亲、两位兄长、妻子写下3封家书,安排家事,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儿纵因杀矮(倭)寇而牺牲,可是有代价的,有光荣的,决不是平常之病死或亡国后被矮(倭)寇之铁蹄踏死。种种无价值之死,我觉得是无趣味的。所以这次我得到前线上去,我决心与矮(倭)寇拼命到底,所谓‘矮(倭)寇未灭,誓不生还’。纵然死了,我很痛快,很干(甘)心,死后二十年后又做好汉。”他给两位哥哥写信,请他们替自己料理家务,为老人尽孝。在给妻子的信中,他明确表示,“在我的决心,誓不生还的”,对家事做了四点安排,包括侍奉父亲、教育孩子,担负更多家庭责任等。
吴瑞所在的陆军第13师于9月底抵达上海,立即投入淞沪战场。他们奉命在嘉定县陈家行—广福—孙家宅一带构筑防御工事,与日寇久留米师团对峙。日军认为我军立足未稳,立即发动猛烈进攻,遭到顽强抵抗,伤亡300余人却寸地未得。此后,敌增派第九师团第33、36联队,发起水、陆、空立体突击,阵地有的被突破,但我军组织反击,以血肉之躯收回。有的阵地白天丢失,晚上夺回,形成激烈的多日拉锯战。13师74团2营4连坚守广福10余日,时年25岁的吴瑞等拼死抵抗,最后全部壮烈殉国。
乔周冕,摄于1935年前后。作者供图
乔周冕:“执笔亦等于执枪也”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和济南后,为了打通南北战场,沿津浦铁路向徐州发起进攻。次年春,中日军队以台儿庄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大会战。战场上也活跃着记者的身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以笔为枪,向人们传递战场新闻,鼓舞着军民的斗志。乔周冕就是其中的一位。
乔周冕,1909年生,河南省偃师县夹沟乡人,“七七事变”后在开封《河南民国日报》担任评论员。1938年3月31日,他在写给父亲、叔父的家书中,介绍了敌我军队在徐州会战的情况,表明自己即将到徐州担任“特派战地记者”,并表示“国难至此,人人应各尽所能,挽救国运。凡为壮丁皆有从军之义务。儿为壮年,从事文化工作,虽未能持枪卫国,但是,执笔亦等于执枪也。”次日,乔周冕即以“河南民国日报特派记者”身份,赶赴徐州会战前线采访。他以“冠生”为笔名,发出多篇战场报道、人物专访、特写等。
1939年初,乔周冕到延安,更名乔秋远。先在“鲁艺”,后参加“华北战地服务团”,以国际新闻社特派记者、华北站主任,华北新华日报编辑身份,在华北抗日前线采访,报道八路军抗战及中共的抗战根据地建设。
1942年5月,日军袭击八路军总部,乔秋远在突围时不幸牺牲,时年33岁。1951年,河南偃师县人民政府批准乔秋远为烈士。1982年,民政部颁发了乔秋远革命烈士证明书。
1938年春,符克赴延安途中留影。作者供图
符克:“国家亡了,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了”
“九一八”事变后,山河破碎,人民遭难,海外华人华侨感同身受,纷纷谴责日寇的侵略行径,或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或直接回国参加抗战,或在海外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符克,原名符家客,1915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少年时期曾任昌洒乡童子团团长。1933年侨居越南任小学教员,1935年考入暨南大学。“七七事变”后,符克积极参加上海、南京、绥远、山东等地的抗日救国运动。1938年初,他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党中央为了动员和组织华侨参加抗日救国,选拔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组成了海外工作团,到东南亚各国开展华侨工作。符克加入该团,任越南琼崖华侨救国会常委,受党的派遣到越南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日。1939年2月,日军入侵海南岛,符克率领40余名旅越琼侨进步青年回琼参加抗战。年底在香港,经宋庆龄任名誉会长的琼侨联合总会批准,符克被任命为联合总会救济部驻琼办事处主任兼回乡服务团总团长。
1940年初,在离开香港,返回广州、海南的途中,符克给父母、大哥等亲人写下三封家书。他知道前方的道路是危险的,但为了抗日救国大业,必须坚定地向前走:“我之自动参加救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与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而已。我相信你们是了解的:国家亡了,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了,抗战救国争取胜利,不是少数(人)所能负得起的。”返回海南岛后,符克率领“琼侨回乡服务团”,活跃在琼岛各地,成为一支抗日宣传、战地救护、输送抗日物资的重要力量。
不幸的是,1940年8月,符克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年仅25岁。1951年,原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总队长冯白驹将军为符克烈士题词:“生为民死为民,生伟大死光荣。”
身着八路军服装的徐光耀,1945年秋摄于河北辛集部队驻地。作者供图
徐光耀:“为国抗敌是何等光荣”
1944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也是黎明前的黑暗。因战争形势严峻,八路军战士徐光耀已有6年没跟家里通信了。这年10月24日,他同时收到姐姐和父亲的来信,反复阅读,激动万分。姐姐为当八路军的弟弟深感自豪,告诉弟弟自己也参加了革命工作。两天后,徐光耀分别给父亲和姐姐回了一封信。给父亲的信既有浓郁的想念,也有对抗战胜利的憧憬:“爹!您耐心的等着吧!胜利的日子就快来了。今年就可以打败德国,明年就要反攻日本,那时候才是咱们团圆的时候!您不信,我姐姐会告诉您现在形势是多么有利。”给姐姐的回信很长,有1200多字,主要表达了对姐姐走上革命道路的欣喜之情,希望姐弟俩共同引导妹妹也参加革命。
1944年10月26日徐光耀致父亲家书。作者供图
徐光耀的父亲徐殿奎,是村里有名的木匠。他从一开始不舍得儿子参军,到亲近八路军、支持抗日,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变。12月23日,徐光耀又给父亲写了一封1600多字的长信,详细汇报了八路军的生活,免得父亲挂念,同时解释了自己从军抗日的原因:“现在日寇也来侵犯中国,亡国大祸临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学岳飞……为国抗敌是何等光荣,为人夸耀。即使牺牲了,也是流芳千古。”徐光耀说,自己参加八路军,既是尽忠,也是尽孝。“是尽的大忠大孝。不仅孝敬了你,也孝敬了中华民族,孝敬了中国。这比小孝,比对个人的孝是有价值得多了、光荣得多了。”在书信往来中,在子女的影响下,徐殿奎的觉悟很快地提高了。
1938年,只有13岁的徐光耀参加了八路军120师359旅特务营,随部队转战南北,参加了许多重大战斗,表现优秀,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徐光耀从特务营进入警备旅,在锄奸科当文书,后到宁晋县大队当特派员,在那里战斗了三年,“清剿”与反“清剿”,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和死神一次次擦肩而过,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抗战胜利前夕,徐光耀离开了锄奸部门,到冀中十一分区(原六分区)司令部任军事报道参谋。抗战期间的火热生活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成为他创作的丰富源泉。后来,他创作了《小兵张嘎》小说和剧本,并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映,聪明机智的抗日小英雄“张嘎子”形象被塑造得生动传神,成为抗战文艺经久不衰的经典。
附记
抗战已经过去了八十年,战争的许多细节变得越来越模糊,也给后代认识那段历史留下了诸多难题。抗战历史既有悲壮的难民流徙,亦有激昂的国民呐喊;既有壮烈的火线厮杀,亦有温馨的后方情话。军旅豪情,柴米油盐,这一切,都真实地记录在家书中。捧读家书,如同从一条条小径来到抗战历史的大舞台,还原全民族抗战的壮丽图景。
按照社会记忆理论,若干个体的记忆汇聚成一个集体的记忆,若干集体记忆形成社会记忆。在重建抗战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过程中,家书起到了十分独特的媒介作用。抗战家书代表的是抗战时期个体的情感记忆,一封封家书汇聚成抗战时期各阶层的集体记忆,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对那场战争的社会记忆。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31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与大伯家10年不说话,一天晚上,他家中传来怪叫声,妈妈踢开了门
与大伯家十年不说话的那个深冬夜里,楼道像一口凉井,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声。
怪叫声是从对门缝底下漏出来的,细细的,像有人在纸上划了一刀又不肯撕开。
楼道灯迟钝地亮了,玻璃罩里封着几只去年夏天的飞虫影子。
母亲把围裙系住,手在门后摸那串老铁钥匙,摸到又放下,眉头皱了一下又松开。
她抬脚对着对门的木板轻轻一顶,门锁里头的插销松动出一声闷响。
我被她拽着往前迈了一步,心里一咯噔,嘴里脱口就是一句方言。
“这可咋整啊。”
母亲没有回头,她只是说了一句很稳当的话。
“先看人要紧。”
门开了一条缝,冷风像一盏没有形状的灯,照出屋里一片不肯亮的黑。
我探身进去,鞋底踩在地砖上发出干脆的响,像提醒自己别慌。
怪叫声忽然变成哧啦哧啦的抽噎,像磁带卡在齿轮里打滑。
我伸手一摸,摸到一台双卡录音机的直角,塑料外壳有细细的划痕,像岁月抽过的线。
窗台上蹿下一只花猫,炸着毛,尾巴像蒲公英,爪子在蚊帐上刮出一小片月光。
“整挺吓人。”我压低嗓子笑了一声,笑完自己心虚,觉得此时笑不合适。
客厅里的灯被母亲啪的一下按亮,琉璃灯罩投下来一圈温柔的黄。
大伯半躺在炕沿下,靠着茶几,脸色发白但眼神有光,像熄火的炉膛里还有炭星。
母亲进厨房找糖,炉台上那口铝锅里冒了一点潮气,小米粥的味道正好从水汽里出来。
她端了杯白糖水,搪瓷缸的蓝边掉了一钩小瓷,像缺了一口却不塌的月亮。
她先吹了吹,再递到大伯嘴边,大伯抿了一口,喉咙滚动,胸口起伏慢慢稳定。
我这才伸手把录音机关掉,从卡槽里小心拽出那盘磁带,磁带壳上贴着手写的纸条。
纸条上写“评剧选段”,字横平竖直,像大伯年轻时在单位黑板报上写的行楷。
屋子里安静下来,花猫从桌下绕了个弯,蹭了蹭我小腿,尾巴温温的。
我看见茶几底下有一串钥匙,挂片上磨得锃亮,像经年握在掌心里走过的路。
我捡起来一看,挂片背面刻着我们家的门牌号,刻痕浅,却认真。
那一瞬间,我像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后背,脑海里把十年前的那扇门又拉开了一条缝。
那年我刚上大学,家里收拾屋子,母亲收拾出外婆当年的陪嫁缝纫机,黑漆面上金字还在。
缝纫机旁的踏板有点松,螺丝有点滑牙,母亲说回头找人拧一拧。
大伯那时候刚学会修理家电,说他拿去楼下老王那儿顺手弄一下,顺便代管一下我们家的钥匙,方便进出。
父亲当时在家休,话没说明白,他心大,觉得一家人不用客气。
母亲等了一阵没看见缝纫机回来,面子上过不去,心里就存了个疙瘩。
过了年,逢年过节,两家门都开着,话却不往一个方向说了。
这疙瘩像绳子上的结,不开不大碍事,拉紧了就硌手。
我在大学宿舍楼里听同学放流行歌,回家却总看见我们家的黑白电视蒙着花布,角上压着一枚铜钱。
茶几上放着玻璃糖缸,糖纸五颜六色,母亲拿一颗剥开给我,笑说甜要慢慢含。
她嘴上不提缝纫机,晚饭后手心里却总握着一枚顶针,无事的时候拿出来转两圈。
那年里我第一次真正懂得“物件会记人”,一台缝纫机记了她一个年轻时候的背影。
我把钥匙握紧,钥匙在掌心里缓缓升了点温,好像有个解释已经来到门口。
母亲把搪瓷缸放回桌面,去给大伯披了一件外衣,把窗帘拉开一点。
窗外飘着细雪,路灯下的雪花像被时间放慢了的羽毛,往地上轻轻落。
我蹲下靠近大伯,他伸手指了指墙角,墙角斜靠着缝纫机的踏板,踏板边上贴着一张纸。
纸条上有两个字,写的是“代修”。
那两个字让我心里猛地热了一下,又缓了下去。
“哎呀妈呀,竟是这么回事。”我心里说了一句,又觉得这句太轻率,便只是看着那两个字多看了两眼。
夜里一场忙乱就这样慢慢归于平静,灶上的火被我调小,小米粥在锅里“咕嘟”一声接一声。
母亲把窗台收拾了,花猫见缝钻到缝纫机踏板下面缩成一团,呼吸匀得像一团线。
我忽然想起更早的那些年,日子像一页页撕下来的日历,背面都留着点胶。
七十年代的老照片里,母亲背着帆布口袋排队领米,手里夹着粮票和油票,票角磨得毛了边。
她回想起那段日子时常说一句老话,日子得守。
八十年代初,父亲领了厂里奖励的“上海牌”手表,他把我的小手放在他手表的表盘上,说你听,滴答滴答,就是一天走过去的声音。
那时家里有一辆二八自行车,车把上挂着手编的花布袋,母亲骑着它去早市买菜,回来时车铃一摇一响,院子里的孩子们就知道饭点将到。
八十年代末,家里添了台黑白电视,天线像两根小角,父亲爬上椅子拨一拨,画面就雪花少一点。
九十年代的风吹来,厂里的老同事有的转行,有的另寻营生,母亲把缝纫活儿收起,去了早市摆摊卖早点。
铝锅里豆腐脑晃晃,辣子油红亮,冬天的热气跟早晨的规矩一样,每天都在。
母亲常用东北话半开玩笑地鼓励我,整住,咱不怵。
我心里知道,这句看似轻巧的话,背后有她早起的清冷和摊前的热气。
2001年春,我进了小厂做外贸跟单,电脑桌上贴着一张流程表,表上有很多格子,格子里写满了细碎的事。
我们接到的第一单外贸小订单,是一批围裙,布料要耐磨,针脚要齐整,交期卡在农历年前。
那时我总觉得自己像缝纫机上的线,谁拉我就往哪儿走,一刻都不能松。
我在键盘边放了一串旧钥匙,空了就握握它,心里踏实一点。
楼道里邻里互相打招呼,声音从门缝里过来,像冬天的太阳,短暂却温暖。
对门的大伯与我们,门相对却话不通,时间久了,相见一笑也就成了礼。
直到那个晚上,怪叫声把这层薄薄的礼像窗上的霜一样擦开了一个口子。
大伯缓过来之后,指了指那串钥匙,又指了指踏板上的“代修”,眼神里有一点抱歉,也有一点执拗。
母亲没有追问,她把锅里的小米粥盛了一碗给他,又盛了一碗给我,一碗碗热气在人手里往上冒。
她说了一句很淡的话。
“先吃口热的。”
第二天早晨,母亲照旧去早市,棉帽压低,围裙两边口袋鼓鼓的。
她给我留了张便条,写在旧挂历背面,字迹清楚。
“对门看一眼,锅里炖肉,别糊。”
我拿起那串钥匙轻轻掂了掂,再挂回钉子上,钥匙碰墙面发出一声清脆的叮当。
我敲开对门,花猫先露了半个脑袋,眼睛亮亮的,尾巴像一根逗趣的草。
大伯坐在窗边,阳光把他的眉毛照出一点淡金,他正在擦拭缝纫机台面的漆皮。
缝纫机的金色花纹依旧,像一条不喧闹的小河,一直在流。
我站在门口说了一句实在话。
“我来看看。”
大伯点点头,手里的布没有停。
我走进屋,看到墙上挂着一个布兜,布兜里露出几只线团,红的、蓝的、白的,颜色像四季的次第。
那一天我们没有多说话,屋里却安静得像一首小曲。
下午母亲回来时,手上端着一碗热豆腐脑,上面点了她自制的虾皮油,香味稳稳地在屋里坐下。
她把碗递给大伯,大伯接过,脸上有一种年岁见过的感激。
我坐在一旁,看见窗台上摆着一只老照片夹,里面夹着几张泛黄的照片。
我抽出一张,是母亲年轻时坐在缝纫机前的样子,头发梳得顺,嘴角夹着一枚别针,眼神往下看,像一束细光。
照片背面写着“新屋第一件成衣”,年月日旁边还有一枚小小的笑脸。
我把照片放回去,心里有一种慢慢铺开的温热。
和好的日子来得不急不缓,就像一锅小米粥,得慢慢熬,才见黏糯和清香。
母亲照旧起早,豆腐脑、煎饼、油条,摊前的人从冬到春,总是有一条队。
她爱说一句轻松话,别瞎寻思,干就完了。
我有时笑她,心里也悄悄记住了这句。
大伯坐在楼下石墩上,给人缝裤脚,针尖在布上走出一排细小的光,走到头,他抬眼望人,笑容里没有多余的意思。
他收的“工钱”多半是邻里的一句诚恳话或者一盆新摘的韭菜,门口的小日子就是这样互相送来送去。
社区后来进行了小改造,单元门换了新的感应灯,夜里上楼不用摸黑,光在脚边走,心里也亮一些。
那年夏天,小区组织了露天放映,大家搬小马扎到院子里,屏幕上放的是八十年代的老电影,孩子们一会儿坐一会儿跑,风把树叶吹得像轻柔的掌声。
母亲在影片开始前递给我一个热黄瓤的熟玉米,说你先吃,我再去给邻居端一碗豆腐脑。
我心里忽然浮起一句东北话,觉得这句话新鲜得很。
“整得挺有味。”
大伯把缝纫机搬到了窗下,光照得针尖亮亮的,他给邻居孩子缝书包带,手腕的力道平静而稳妥。
他偶尔播一段评剧,磁带一圈圈转,戏台上的唱腔从这小屋里绕出去,绕进楼道,再绕到院里,像一条旧街上熟悉的风。
2008年夏天,街头的彩旗把日子点得很亮,大家在电视前看运动健儿奔跑,孩子们在楼下学样,笑声像一群自由飞的鸟。
我在那年里学会了一件小本事,把复杂的工序拆成一个个清晰的小步骤,贴在墙上,自己看得明白,别人也好接手。
母亲见了笑我,说你这可算有谱儿了。
我回她一句,别嘚瑟我了。
她瞪我一眼,笑意还是藏不住。
到了2010年以后,小厂订单慢慢多起来,忙的时候我晚上十点才到家,楼道里灯一亮一灭,脚步声在光里走走停停。
对门的评剧声音依旧,音量不大,像有人在等晚归的人路过时给一声问候。
母亲有时候会在门口放一张小纸条,写上“热粥左边,钥匙右边”,末尾画一个小锅,画得很认真。
我经常在那个时刻心里软一下,觉得生活有一套不急不躁的规矩,像针脚,一针连一针。
那串老钥匙被母亲装进一个简单的相框,摆在客厅的墙上,旁边是我们家的合影,老照片和新照片挨得很近。
相框的玻璃会反日光,上午反得亮,下午反得温,钥匙在里面安稳地躺着,像一个不再需要频繁使用却随时可以拿出来的解释。
有时候来客人,看到那串钥匙会问一句,这钥匙挺有年头了吧。
母亲说,有年头,但更有心头。
她言语不多,这样一句就把过往轻轻地说清了。
我成家那一年,妻子随我回老屋,第一次见到这条楼道,她对着天窗发出一声短叹,说这楼道有生活味。
母亲拿出一块细花布,请大伯把它裁成两只枕套,布上的花是小小的,像从墙角偷偷开出来。
缝纫机踏板在脚下起落,声音熟悉,我想起小时候在炕上趴着听这节奏,困意像被摇出来一样甜。
婚礼那天,邻居们帮着摆桌,母亲把相框里的钥匙拿下来擦了擦,挂回去的时候轻轻一碰玻璃,发出一声清脆。
那清脆被笑声盖住,又在笑声里加了一层亮意。
大伯把缝好的枕套递给我们,针脚密,线头收得齐,手里递出来的不像物件,倒像一句安静的祝福。
他只说了一句。
“用着舒坦。”
我点头,心里回他一句东北话,心里话总得带点熟人的味儿。
“妥妥的。”
春夏交替的时候,我常在下班后去楼下转一圈,树影把地面切成一格一格,孩子们踩在格里跳,一二三,脚步轻。
大伯坐在长椅上看他们跳,偶尔提醒一句,别跑太快,鞋带松了。
母亲从早市回来,会在树下歇一会儿,掏出毛巾擦擦汗,和王婶唠两句价钱和时令。
她偶尔抹一下围裙,眼睛看向对门的窗,窗里有不紧不慢的光。
有一年冬天雪特别厚,小区门口的积雪被堆成小山,孩子们在上头滑,笑声一浪接一浪。
我拿铁锹去帮忙清一条路,雪在铲下发出"吱呀"的声,像旧门开一条缝。
大伯拿着扫帚在后面清扫,他不急,扫帚一来一回,地面就露出一个干净的条。
我说了一句像开玩笑的话。
“这活儿不白整。”
他笑,说一句朴实的话。
“走路的人心里踏实。”
我那时突然想到,十年前我们绕开的那条路,绕着绕着,也走回了一条简单的直线。
2012年以后,母亲学会用手机,学会在微信上发“早安”,每次都配一碗豆腐脑的照片,角上有光点,像认真摆上的一颗糖。
我提醒她少发点别打扰人,她回我一句东北话。
“可拉倒吧,我发我乐呵。”
她笑的时候眼睛弯,弯里有水光,像烧开的水要溢出来又不溢。
年复一年,家里的旧物件越发像家里的老朋友。
缝纫机在窗下,台面擦得亮亮的,偶尔缝个窗帘,偶尔缝个围裙,踏板一动一静的节奏和春夏秋冬配合得很自然。
钥匙在相框里,玻璃上会落一层尘,母亲每周拿抹布擦一擦,像给家里的一件体面的衣裳拍灰。
花猫在踏板下睡觉,醒来伸个懒腰,在窗台上晒太阳,晒得毛皮亮亮的。
父亲喜欢在晚饭后把收音机打开,调到戏曲台,评剧响起来,磁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声音却还是那股味道。
我们坐在餐桌边听,母亲不时把碗边的米粒抹平,日子就这么被轻轻抚顺。
有一次社区举办志愿服务,组织大家给古树围栏刷油,我和大伯在一块儿刷,刷子在木头上走,油光一层层显出来。
我问他手酸不酸,他笑,说活儿分散着干,啥都顺。
傍晚落日从楼角侧过来,斜斜照在人的肩上,肩旁似乎也暖了。
再后来,我和妻子有了孩子,小小的人在屋里学走路,一步一晃,扶着桌沿往前迈。
母亲把缝纫机上的一块旧棉布裁成软垫,铺在孩子常跌的地方,说这样不疼,孩子心里也不怕。
孩子摸着相框里的钥匙,隔着玻璃拍一拍,发出轻轻的声,笑得眼睛眯起来。
我蹲下告诉他,这是钥匙。
这句简单的话说完,我心里有一层细细的震动。
那不是一把开门的钥匙那么简单,它像一段家里人与人之间的解释,解释温和,不急不慢。
有时我会想起十年前那个门口的冷风,想起那一脚轻轻的顶,想起那一阵哧啦哧啦的怪声和花猫从蚊帐里钻出来的影子。
那一晚之后,时间像被轻轻拧了一下,齿轮对上了齿,运转起来了。
我也更能听懂母亲那些看似随口的叮嘱,比如换季要晾被子,比如下雨前要把窗户关一扇缝,比如晚一点回来记得带一束葱。
每一条叮嘱都像针线,针线来回,缝出家庭的密度。
父亲老邻居的电饭锅又坏了,他拿起螺丝刀去看,回来时手上沾着一点黑,眼睛里有亮光,像做成一件小事心里满足。
他把手洗净,坐下吃一块母亲蒸的红薯,红薯热热的,甜味是慢慢出来的。
我在这一刻不由得又说了一句东北话。
“寻思寻思,这不就是好日子。”
我说完自己笑了,笑自己总爱加一口方言,像给话加一勺辣椒油,有味也不冲。
秋天到来的那一年,楼下梧桐叶片一叠一叠落下,像一封封无信的信。
大伯拿了竹耙,把叶子拉成一条线,又用簸箕一点点端走。
他做事不着急,像写一笔字,一笔就只写一笔,不贪多。
我学他这份稳,把工作里的流程图再精细一点,遇到临时插进来的事,不慌不忙地在边角空白添上一个小注释。
事情被一条条理清,像衣服剪裁好了,就不再起皱。
有一天晚上,楼道里停电了,感应灯也没了,黑像一块布盖下来。
我摸黑上楼,口袋里翻出手机亮起一个小手电,光柱像一根细棍儿,划开前面的黑。
刚走到我们家门口,对门就开了一条缝,有一束烛光从里面出来,烛光里是大伯的笑脸。
他递给我一支蜡烛,说一句很顺口的话。
“拿着,省得瞎摸。”
我接过烛,心里忽然起了一句地道的话。
“有你在这儿,心里有底。”
他摆摆手,烛光把墙上的影子拉长,影子像一条长长的解释,解释到尽头,正是屋里人的模样。
我把烛火点进屋,母亲在厨房里把米洗到最干净,锅被擦得光亮,光能照见人的脸。
她抬头看我,眼里没有问,只有“回来就好”的那种简单。
我把那串老钥匙拿下来又擦一擦,再挂回去,钥匙碰到相框玻璃,发出一声轻清的响。
这声音不大,够把一段日子里的缝补声叫醒。
冬去春来,院里那棵槐树又开花了,花香一阵阵,像日子里的小福气,不高调,不稀罕,实在。
我抱着孩子在树下站一会儿,花瓣落在孩子的头发上,他用手抹掉,又抹到自己的鼻尖,笑得很安静。
母亲在一旁看着,笑得也安静。
大伯从楼上往下走,手里拎着缝好的裤脚,针线头一点不见,他对我点头,眼睛里的亮还在。
我忽然觉得,那一串老钥匙和窗下的缝纫机,就是两座灯。
一座点着门里门外的进出,一座点着衣角袖口的合身。
灯不大,却够照亮一家人的脸。
从那以后,我偶尔会把那串钥匙借出来一会儿,攥在掌心里,像握住一个不必大声说出来的道理。
这道理朴素,像母亲的一句常说的老话,日子,往好里守。
我给孩子做作业时也会讲这个道理,讲的时候不引用大道理,只把家里的故事说一遍,把钥匙的轻响学一声,他就懂了几分。
有一次楼下的小伙子来找大伯,说裤脚缝歪了能不能帮着拆了重缝。
大伯把眼镜往上推推,笑着说一句人情话。
“能整,慢点整,整利索。”
这句话像针,轻轻地把一段年轻人的焦虑缝住。
他做完,把线头收好,顺手把桌上的录音机擦了一遍,唇边有简单的满足。
傍晚的时候,母亲把一碗热汤端来,汤热气直直往上走,走得像一条看得见的路。
我端着碗,看着窗外那条被路灯照亮的小路,心里慢慢有了这样的明白。
家与家之间,有时需要一脚把门从缄默里踢开,有时只是需要一碗热汤,一串钥匙,一台缝纫机。
前者是勇气,后者是耐心。
我在心里又冒出了一句东北话,觉得这句说了不俗。
“有谱儿。”
夜色深了一点,楼道里的脚步声稀疏了,评剧声也低了,花猫在踏板下发出轻轻的呼噜。
我把灯调小一档,桌上的影子稳稳地铺开,像一张刚缝好的被面,不起皱。
我伸手扶了扶相框,钥匙轻轻碰到玻璃,清脆一声响。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