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格策美文教你学写《审判1962观后感》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02 2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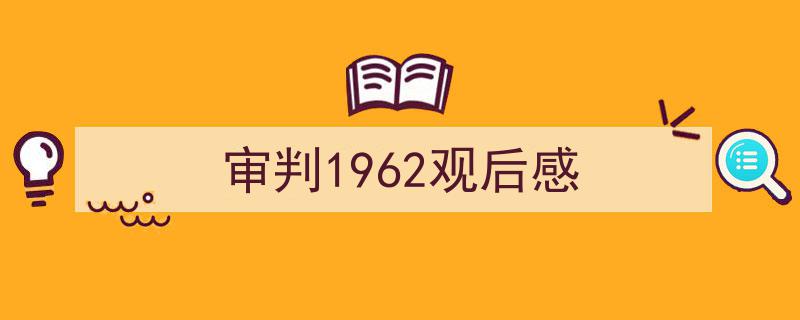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审判1962》的观后感作文,可以注意以下几个事项,以确保文章内容充实、结构清晰、情感真挚:
"一、 观影前准备:"
"了解影片背景:" 在观影前,最好对影片的历史背景、人物关系、主要剧情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例如,《审判1962》是以1962年印度最高法院审判辛格案为背景,关注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以及司法体系在政治压力下的运作。了解这些背景信息,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影片内容,写出有深度的观后感。 "明确观影目的:" 你想从这部电影中获得什么?是想要了解历史,还是想要思考人性的复杂,亦或是想要探讨司法的公正性?明确观影目的,有助于你在观影过程中保持专注,并引导你写作的方向。
"二、 观影过程中:"
"认真观察细节:" 注意影片中的细节,包括人物的表情、动作、场景的布置、象征性的道具等等。这些细节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更深入地理解人物和剧情。例如,辛格的眼神、法官们的表情、法庭的气氛等等,都可以成为你写作的素材。 "记录关键场景:" 在观影过程中,可以记录下一些关键场景,例如高潮戏、转折点、令你印象深刻的片段等等。这些场景可以作为你写作的
景凯旋读卡夫卡《审判》:阻碍人们认识真理的,是我们内心的牢笼
有天早晨,银行高管约瑟夫·K还躺在床上,两个陌生人突然闯进房间,宣布他遭到逮捕,然后就坐在桌子边大吃大喝他的早点。根据勃罗德的传记,在卡夫卡给朋友们朗读《审判》的第一章时,大家都笑起来,而他本人笑得“特别厉害”。看过卡夫卡忧郁神情照片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卡夫卡开怀大笑的样子,不过,对于他朋友们的反应,人们却不会感到太过惊讶。
因为他们也跟卡夫卡一样,跟K一样,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按照另一个犹太作家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战前的奥匈帝国正处在太平的黄金时代,整个社会相信进步的观念,国家赋予每个公民权利,法律公正,秩序稳定,人人按照法律行事,对自己的未来都有良好的预期。而卡夫卡的《审判》则是一个荒诞的故事,这样的事只能在噩梦中才会发生,对于现实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人们的反应往往是笑声。
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出生于布拉格,在保险公司任职,利用业余时间写作。1924年因病去世。1925年《审判》出版,1926年《城堡》出版,引发世界文坛震动。现如今,卡夫卡的影响已遍及文学艺术各领域。
“一只笼子去寻找鸟儿”
K一开始也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他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处境,认为没有人有权任意支配他,他拿出身份证,要求对方出示逮捕证,但来人却说,他们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不知道逮捕他的原因,并警告他要清楚自己的处境,因为上面是不会错的。这时候K想:“如果他去打开隔壁房间的门,或者打开通向客厅的门,也许那两个人不会有胆量来制止他,也许这是解决整个事件,使其告终的最简单的办法。”
假如K真的这样做,下面的故事就不会发生了,可是K随即又想到:“他们也可能会抓住他;他只要一被抓住,就会失去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拥有的优势。”于是他放弃了这个办法,回到自己的房间。什么是K仍然拥有的优势?是镇定自如。这是对司法机构的信任,法庭终究会给他一个满意的解释,抑或是对司法机构的不信任,如果他此时抗拒反而证明自己心中有鬼。
他的房东和邻居似乎也抱着同样看法,对于K的无端被捕,他们全都漠然视之。在等待审讯的日子里,K被允许照常上班,好像世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卡夫卡的作品总给人一个印象,周围所有人都活在真实的现实中,唯有主人公活在梦中,这是无比真实的细节与荒诞不经的情节相融合的结果。在这部小说中,卡夫卡采用的第三人称叙事不是全知全能视角,而是主人公的视角,只有主人公知道可怕的事正在发生,而且只发生在自己身上。
《审判》外文版封面。
K的初审就已具有这种独自面对一个敌意世界的典型特征。他接到电话通知,在一栋住户大楼里挨门逐户打听,转悠了很久才找到审判厅,大厅里挤满了人,多数人穿着青上衣,外面披着旧式长外套。预审法官翻着笔记本说:“你是油漆装饰匠?”“不对,”K说:“我是一家大银行的襄理。”这个使在场的人开心得大笑,K也不由得笑起来,指出法官的问题显示了这次审判的特点,他们也许是抓错了人。
显然,K觉得自己遭遇到一个错案,他必须洗清罪名,但他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到底是什么,甚至不知道是谁发出了逮捕他的命令,这使他不得不一再为自己申辩,表现出对司法机构的抗拒。接下来,K再没有接到审讯通知,他找到原来的审判厅,那里如今空空荡荡。K的叔叔从外地赶来,带他去找律师,照顾律师的护士莱妮告诉他:“记住我的忠告就行啦,以后别再那么倔强;你斗不过法院,你应该认罪。一有机会就认罪吧。你不认罪,就不可能逃出他们的魔爪,谁都无能为力。”
对于莱妮和K周围的人来说,这是普通人的常识,既然法庭要惩罚一个人,这个人就一定是有罪的。K开始思考现代法律制度,在他看来,“法律不鼓励辩护,只是允许辩护。”律师向他解释说,法院根本不把律师放在眼里,甚至还希望取消辩护律师,预审法官都是听命于上司,因此,最重要的是律师与法官的个人关系,许多律师往往采取行贿的方式,向委托人吹嘘自己与法官的私人交情。
为了替自己辩护,K认识了一个画家,这个画家常给法官们画像,知道许多法庭内情。画家告诉他,有三种无罪开释的形式,即彻底宣判无罪、诡称宣判无罪和无限期延缓审判。第一种例子从来没有发生过。第二种是设法使低级法官签署无罪判决书,但这不是终审判决,案子会在各级法院呈转,甚至相隔很长时间,只要上面一有命令就会重新安上罪名。第三种延缓审理是最好的方式,诉讼停留在开始阶段,不再继续往下进行,但被告必须不时去会见主管法官,提供一些新的证据,好处是不用时时担心、焦虑和紧张。
这使得K更加相信,法院是个毫无意义的机构,一个刽子手就能胜任。他始终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没有人能告诉他,这个答案只存在于从不露面的最高法院那里。他解聘了律师,因为在他看来,律师本质上不是为被告服务,而是为法庭服务,就连律师和画家的房子也属于法院。说到底,法院这个官僚机构正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代表了世俗权力的神圣化。就此而言,卡夫卡已经天才地预知了后来全能国家的出现:一个像机器一样运转的现代权力体制。
电影《审判》(1962)剧照。
按照纳粹制度的研究者、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观点,现代官僚机构具有一种理性的客观化功能,即造成执行者与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使得暴力的执行者可以保持冷然的道德中立,将施暴的对象非人化。组织纪律取代道德责任,成为行为的规范与美德,执行者只知道忠实地执行命令,根本不想去了解行动的目的,因为他遵从的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职责,而不是个人的道德判断。这就是现代权力机制对于个体的压倒性力量所在。在从前,当一个人无辜遭到别人指控时,他会感到愤怒,奋起抗争,但到了现代,当一个人无辜遭到一个权力机构指控时,他却会首先产生自我怀疑,而且越到后来就越感到自己有罪,因为现代权力机构的神圣化源于它的匿名性、非个人性和不可抗拒性。它的重要功能就像卡夫卡的一则格言所说:“一只笼子去寻找鸟儿。”面对这样一个非人化的现代机制,一个人的内心只会产生深深的无力感,最终不得不屈服。
“他死了,但这种耻辱将留存人间”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两个男人来到K的住所,一言不发地把他带走,“一出大门,他们就以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样子抓住他。他们的肩膀紧紧顶着K的后肩,但并不弯起胳膊肘,而是伸直手臂,压住K的胳膊,以一种训练有素、灵巧熟练、使人无法反抗的方式将K的双手压得不能动弹。K挺直腰板,在他们中间走着;这三个人联成一个整体,只要有一个人被击倒,大家就会一齐倒下。只有无生命的东西才能组成这样一个整体。”
这段话太有卡夫卡的描写特征,K突然明白,反抗是毫无用处的,即使他反抗,也称不上是英雄。他们来到郊区的采石场,两个刽子手互相谦让着,K在旁边安静地等待,这时他看见采石场旁边的一座房子开了灯,一个人突然探出窗口,双手伸出窗外。“这个人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仅仅是他一个人吗?还是整个人类?马上就会有人来帮忙吗?是不是以前被忽略的有利于他的论点又有人提出来了?当然,这样的论点应该有。逻辑无疑是不可动摇的,但他阻挡不了一个想活下去的人。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何处?他从来没有能够进入的最高法院又在哪里?”
勃罗德称这是又一个古老的约伯问题,即世上到底存不存在正义?勃罗德想将它引向犹太和神性的解释,上帝的尺度不是人类的尺度,这是导致卡夫卡不安的根源。但是,从卡夫卡的生平看,他其实并不笃信宗教,而是始终站在人的立场。在《审判》第九章,教士在大教堂向K讲述了《在法的门前》的故事,这个故事寓意复杂,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因而常常被世人单独拿出来讨论。
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要求见法。守门人告诉他,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如果他硬要进去便会遇到里面许多更有权力的看守。乡下人于是决定,最好还是得到许可后才进去,他就这样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变得越来越衰老病弱,模糊的老眼看见“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临终前,守门人走到他身边,俯在他耳边说,这道门就是专为他开的,现在乡下人快要死了,守门人要去把门关上了。
听完这个故事,K的第一反应是,守门人歁骗了那个乡下人,在最后时刻才把真实的消息告诉他,教士反驳说,守门人只是忠实遵守了职责,尽管他对法的内部也一无所知。实际上,他比K更惧怕里面那些职位更高的守门人,因此他也是受骗的,甚至他比乡下人更不自由,由于守门人背对着门,他甚至还看不见大门里射出的那束光线。乡下人可以随时离去,他却不能擅离职守,既不能提前关上大门,也不能擅自走进大门。
教士承认,守门人的确头脑简单,但又认为守门人代表了法的尊严,必须将他的话当作必然的东西来接受。K于是得出结论:“这会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但是,这还不是最后的论断,因为这个故事可以引出各种结论,教士只是选择了一个最容易的问题,一个奥威尔和鲍曼就可以很好解答的社会学问题:现代权力社会的实质。
这就是卡夫卡的深刻之处,他发现了事物的多义性,把最复杂的形而上问题留给了这个世界。“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正是这束光吸引了乡下人,让他徒劳地等待了一生,这束光看上去源于某个绝对之物,它是权力、正义、至善、理念或启示?是法、道、爱甚或是虚无?这是一个未解之谜,是一个柏拉图洞穴的故事,只有走出洞穴才能看清那个唯一的光源。对于卡夫卡来说,这道光源是人内心的“不可摧毁之物”。
可是,评论家们却似乎很少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乡下人为什么不径直走进法的大门?卡夫卡仿佛只是无意中提到一句,教士说门里面还有许多更有权力的看守,乡下人于是就不敢进去了,就像K最初被捕时决定不走出房间,尽管他明知自己无罪,但他潜意识里却惧怕高深莫测的权力。
那么,在此之前,有没有人曾经走进过法的大门?
我们应该还记得,这道门只是为乡下人而开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悖论,法的大门只是为那些不敢进去的人而开的。这让我想起两年前一个真实的见闻,一个人想要走出封闭的小区门,他小心翼翼地问门卫,自己可以出去吗?门卫随口道:“这个门本来就是开着的。”正是这件事让我突然间明白了《在法的门前》的寓意:阻碍人们认识真理的,其实是我们内心的牢笼。
意识到世界的绝对性,却无法抵达绝对之物,显示出人类最深刻的无能,这无能来自人的属性,来自人的内心。这就是卡夫卡带给我们的启示,他比任何作家都更深刻地表现出现代人的困境。我甚至觉得,代表二十世纪人类精神的人是卡夫卡。在中世纪,人们在宗教权威下不知道人之为人的道理,而在现代社会,人虽然成为了目的,同时又成为了世俗权威的奴仆,受害者与迫害者自愿地“联成一个整体”。然而,也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是人,K即使无力抵抗外在世界,但他在内心也从未接受这个世界。
像K一样,卡夫卡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一直都在抵抗,每个主人公面对困境时都表现出阿伦特所强调的“行动”,尽管结局总是归于失败。最后时刻,当刽子手在采石场把刀插入K的心脏,在皎洁的月光下,他感到自己像一条狗似的:“他死了,但这种耻辱将留存人间。”
他之所以感到耻辱,是因为他依旧保持着人的意识,在临终前仍能瞥见采石场旁边一个房间的灯亮了,露出一个伸出双手的身影,像是在呼唤。
K认识到自己在探索真理上是失败了,他对自己的内心进行了审判,得出永久耻辱的结论(这一耻辱留存到奥斯维辛)。在给勃罗德的一封信中,卡夫卡曾写道:“我们正是带着自身的一些弱点,去想方设法认识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审判》这部小说构成了卡夫卡式的终极悖论,人的耻辱感源自人内心的脆弱,同时也源自人内心的不可摧毁性。
撰文/景凯旋
编辑/张进
校对/刘军
《审判》中的法律之门
奥匈帝国下出生在布拉格,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小说《审判》,开启了“笼子找鸟”——因审判而有罪的“卡夫卡式审判”模式。小说波谲云诡、晦涩难懂,法律之门更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溢出众多法律隐喻,以至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所有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同样可以说,所有西方法律都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
小说《审判》中文版之一
黑格尔曾说,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可以看见整个白天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追寻其他鸟儿在白天自由翱翔的足迹。为此,我们在喧嚣中起飞,在法律门前盘旋,望见法律之门透出的光亮,抉幽发微,从故事本身试破迷雾围城,试解法律命题,试探人生之门。
1.
《审判》的主角叫约瑟夫·K。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学家阿甘本认为,K是古拉丁词诽谤诬告Kalumnia的首个字母,小说首句便是“准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无缘无故地被捕了”。因此,卡夫卡将其确定为K,既表示他是一个受陷害者,亦表示其人格消弭。
1962年改编的电影《审判》海报
一早醒来,坐在床头,按下床铃,K先生等来的不是房东太太送来的早餐,而是一身黑制服的男人对他口头宣布“你被逮捕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隶属哪个部门?他犯了什么罪?他的拘捕令呢?不可思议的疑问让K认为这可能是个闹剧,于是他决定演下去。他打开珍藏的好酒,为了果腹干了第一杯,为了壮胆干了第二杯,为了应付不测干了第三杯。
他们承认他们只是低阶雇员,不要跟他们讨论证件、拘捕令,他们的部门会把拘捕理由和被捕人的底细弄清楚,想见长官必须等长官的命令。这番说辞被房东太太理解为某种神秘:“你这种被捕,我觉得是某种深奥的原因,某种难以理解的原因,我不是很理解,也不需要理解。”K给他们命名了一个“审讯委员会”的杜撰部门,被邻居小姐解释得模棱两可:“如果是审讯委员会,这个罪名可不轻,但您还是自由身,那么应该不会是犯了什么大案。”
K应约来到杂乱无章的院子,曲里拐弯也找不到初审他的法庭。他随意编了一个名字,谎称寻找木匠“兰茨”,在六楼的一扇门,不无荒唐地被告知“兰茨”就在这,并且认真地对他说“您进去之后我就锁门了,不能再进人了”。面对乱哄哄的初审法庭,K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辩词,指责随意拘捕的非法性,初审法官翻看着K以为是案卷的色情书刊,不以为然。
再去初审法庭却空空荡荡,在廉租房的阁楼上,有一行孩子般幼稚青涩的字迹写着“通往法院办事处”。法院洗衣妇试图帮助他,她丈夫是法院差役,他从差役的嘴里知道了“审判结果从来都是早已决定好的”。K的叔叔帮他引荐了律师,见到了一位秘书长,他因故错失了这位重要人物的帮忙。不过在律师这里,K知道了法院“并非滴水不漏,玩忽职守和收受贿赂大有人在”,法院的流程对底层官员是保密的。
K不想坐以待毙,意欲通过邻居小姐、差役老婆、律师女护工、画家帮忙,他们要么虚与委蛇,要么无能为力。因为他们认为“法院不会轻率发起指控,如果发起指控,就认定了被告是有罪的,并且无法轻易改变法院的这种观念”。画家不无玄妙地说,“撤销指控这种巨大权力不属于我认识的这些法官,但他们有权暂停指控”。但暂停指控,表面无罪释放,案件仍然没有终结,还要继续进行,再次逮捕,然后是“第二次无罪释放之后的第三次拘捕,第三次无罪释放之后的第四次拘捕,如此往复,这一切都包含在表面无罪释放这一概念里了”。
决定K命运的法官似有却无,真正的法官见首不见尾。没人过问他的案件,没人倾听他的申诉,不讲述任何确定的东西,没有人包括K自己清楚所犯何罪,有的只是无限接近实质的可能性。他陷入一张无形法律之网,意欲冲破牢笼,却无从下手;举起重重的拳头,屡屡砸在了棉花上,而他身上的绳索越勒越紧。
杀人于无形,恐惧于无声。荒郊野外,两个训练有素的男人未宣判一个字就手刃了他。
K的生命就这样被法律终结了。因为它的无因果性,我们一开始便感知荒唐,但还是一步步看它从荒唐走向灭亡。
2.
K生前遇到了一个教士,K向其辩称:“这可能是个误会,一个人怎么可能无缘无故被判有罪。”教士反驳“有罪人都这么说”,并声称“你是自己骗自己”。接着教士便给他讲了一个法律之门的寓言故事: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守门人说现在还不能允许他进,以后倒有可能,里面“每道门都有守门人,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大”。“乡下人”给守门人送礼物,在黑暗中发现了法律之门照射出来一丝亮光,但他老死也未能迈进大门,临终问道:“大家不是都想了解法律是什么吗?为什么多年以来除了我再无别人要求进入法律之门?”守门人说:“因为此门只为你一人所开。现在我要关门了。”
一幅静谧凄凉的水墨画,隐喻四伏。
因为这个寓言故事起于无罪,源自欺骗,所以故事讲完后,教士和K便开始了关于欺骗的对话:K认为是守门人欺骗了“乡下人”。守门人在“乡下人”行将就木时才告诉他这扇门只为你开,不就是欺骗吗?教士认为“乡下人”之前并没有问守门人此门为谁开,而且守门人一丝不苟忠实履行了自己守门的职责。所以,教士认为真正受骗的是守门人,守门人不了解法的内部,只知道通往法的道路,他关于法的内部的想法是幼稚的,因此,他也处于一种受骗状态。教士还扩展了从属问题,认为守门人被职责禁锢在大门岗位,他应当从属于来去自由的“乡下人”,而不是把“乡下人”当成自己的下属。
K表示倾向同意教士的观点,但仍不放弃“乡下人”受骗的观点。认为这两个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守门人受骗了,那他的受骗必然影响到“乡下人”也受骗。守门人受骗于自己固然无害,却为“乡下人”带来无尽危害。
教士借用他人所言说:许多人断言,故事本身不能使任何人评判守门人,他终究是法的仆人,就是说他属于法,他完全超出人们评论范围,怀疑他的尊严等于怀疑法本身。
K反驳道,既然此门为“乡下人”开,就应该放这个“乡下人”进去。教士对此不置可否,却认为K篡改了故事,并指出故事里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但不必把他的故事每句话都作为真理来接受,只需当成必然的东西来接受。
“当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时,往往使人怀疑它的正确性”。两人关于欺骗的对话并没有全然包括这个寓言的隐喻,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审判》本身就是一个寓言,加之法律之门的寓言更显得扑朔迷离,二者呈现的要旨和案例的关系,富含更多暗喻。
“玫瑰就存在于玫瑰的字母之内,而尼罗河就在这个词语里滚滚流淌”。全面理解法律之门的隐喻,就在小说《审判》里的法律本身。当法律借理性之名反复定义和自我扩张,渗透到社会各方面时,字面上的法律将退却到非显要位置,理所当然进入隐喻之界、跻身形而上,呈现多义性、多维度、无边界样态,这是试解法律之门的语境钥匙。
由此出发,可以从作者设置的法律、门、守门人、“乡下人”四维度来尝试解读。
3.
法律是什么?“乡下人”为什么想进去?便是第一隐喻设置。寓言故事并没有明确这个法律是什么,倒是小说有几处是这样提到法律的:他们拘捕K时说“哪里有罪恶哪里就有他们,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找你。这就是法律”;当K说不知道有这种法律时,看守不无嘲讽地说“他承认自己不了解法律,但又声称自己没有违法”;邻居小姐表示对法律很感兴趣,说“法庭有一种强大的魅力”。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法律意指范围较大,既指实体法、程序法等有形法,亦包括司法过程,这里主要指法律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组织等上层建筑无形法,体现了法的广泛性、权威性。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形成了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说“乡下人”想进去,毋宁说K想进去,K不相信他遇到的“法律”就是这样的如同儿戏、惨不忍睹,强烈希望走进法律“城堡”,追寻法律正义。
但“乡下人”和K本人至死没有走进法律之门。因为无形的法律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组织,本不存在法律之门,所以“乡下人”和K走不进虚幻大门。而作为对此的心理阻断和期待可能,法律面前确实有道门,横亘在想进去的人面前。因此,作者设置门,具有象征意义,虚妄而真实,象征K遭遇艳若桃花、实则只余躯壳的法律的无奈;象征对法律公平正义、至高权威的向往;象征走进司法体制、跻身上层建筑的无限接近和不可能。即使K进入那乱糟糟的初审法庭现场,爬上那歪歪扭扭的法院办事处,接触那些一本正经的黑衣人,听到那么多法院传说,只是开始触摸法律跳动的脉搏,在法律的边缘踟蹰徘徊,始终没有走进法律之门。
法律之门层层叠叠,无限接近而不得进。如同卡夫卡的《城堡》,近在咫尺、可望而不可即,《变形记》门里门外两重天……不是卡夫卡对门情有独钟,而是有世界便有门。天门、地户、人门、鬼关……门的设立本身就是一种悖论,为方便出入而建门,也为防止出入而建门,既是一个范围限定的否定,也是这个限定缺口的肯定。“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有门便有守门人,守门人的设立出于门的形式需要,由于其人格性与法的上层建筑属性的不同,守门人并不是法律,拘捕K的执法人也不能代表法律,而且“乡下人”比守门人还多看见了从法的大门射出的光。因为守门人守护的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守门人才被误认为他们就是法律。
当“乡下人”奄奄一息时,这道门便随之关上了,守门人却说“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这是这个寓言最为诞妄的一句话,其实这和设立法律之门的道理是一样的,你追寻法律,法律之门便存在;你抛弃法律,法律之门随之而关。故你在门便在,你走门便关。正如K虚构“兰茨”木匠名字却被迎入真实法庭一样,这个法庭就是专门为你而设。“乡下人”终生没有、也不可能迈入虚幻的法律之门,不是欺骗问题,而是体现了追求法的过程中主客体的异化。
4.
法律之门是卡夫卡凝结绝望应对未知不可控的一个点,这个点离不开卡夫卡受父权控制、被女友“审判”、法学博士身份、工伤保险公司任职的经历之线,这个线离不开卡夫卡生活的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制度的面,这个面形成了卡夫卡对神圣法律的痛彻深悟和对精神沦丧的荒谬反思。卡夫卡关上了一扇门,却打开了一扇窗。K在受审路上,看见临街一扇扇诗意盎然、生机勃勃的窗,如同一束束法律之光,带给了卡夫卡“坚持下去”的生命希望。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卡夫卡说,“我写的和我说的不同,我想的与应该想的不同”,如此这般,陷入最深的黑暗之中。《周易·系辞上》载,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法律之门的意象纷繁复杂,浸淫了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的人性思想,与老庄、聊斋托物寄意相贯通,产生种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陷入无尽想象的空间,而人类阿喀琉斯之踵的语言之痛,使得语言解释是可能的,但绝对解释又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都是“乡下人”,试图走进法律之门,但终其一生也难以走进。
“尽日寻春不见春”,“春在枝头已十分”。西西弗滚石上山不止,吴刚月中伐桂不息,貌似奇诡徒劳,实为超越自我的胜利。困住我们的还是自身枷锁,限制我们的还是凡身肉体。我们只有破除自身限定,废除人为壁垒,坚持走在法律路上,追寻潋滟光芒,才能走向自由、正义和永恒。这才是我们的不二法门。
作者:孙全喜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