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推荐《冬作文300》相关写作范文范例(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03 06: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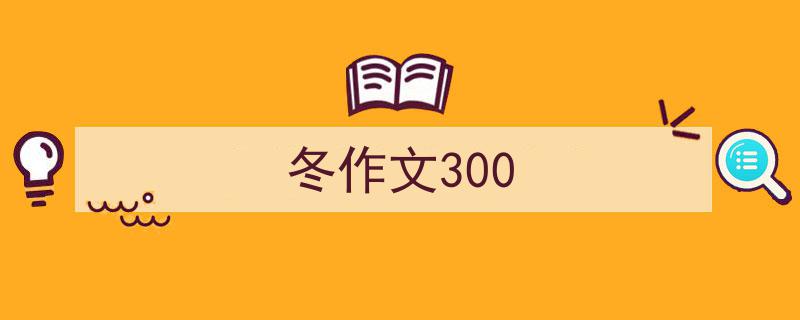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冬天的300字作文,并附带了写作注意事项:
"冬天的韵味"
冬天,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魔法师,它悄无声息地降临人间,用一场大雪装点世界。当第一片雪花悠悠扬扬地飘落,地面便铺上了一层洁白的地毯,树枝也变成了玉树琼枝,整个世界仿佛都变得宁静而纯洁。
冬天的早晨,窗户上常常会凝结一层薄薄的雾气,需要仔细擦去才能看清外面的景象。阳光虽然偶尔出现,但感觉总是带着一丝寒意,无法驱散凛冽的寒风。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曳,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更显得冬日早晨的寂静。
虽然冬天天气寒冷,但它也有独特的魅力。孩子们喜欢在雪地里嬉戏,堆雪人,打雪仗,银色的世界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屋内则温暖如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着热茶,吃着点心,享受着这份难得的温馨。
冬天,虽然短暂,却给大地带来了宁静和美丽,也让人更加珍惜家中的温暖。我喜欢冬天,喜欢它的纯洁,喜欢它的宁静,更喜欢它带给我们的那份温暖的感觉。
---
"写关于冬天的作文注意事项 (300字作文):"
1. "明确中心思想:" 首先要确定你想表达冬天是什么样的?是寒冷、美丽、宁静
一诺甲子 赤诚如初——记“中国好人”、退伍老兵秦兴海的“雷锋人生”
姑苏古城,小桥流水,粉墙黛瓦间流淌着千年的雅韵。在双塔街道觅渡社区的寻常巷陌里,一位85岁的老人,步履或许已不如当年矫健,但眼神依旧清澈明亮,胸中奔涌着一股永不褪色的热忱。他叫秦兴海,一位与雷锋同龄、同年入伍的退伍老兵。65载光阴荏苒,从风华正茂到鬓染霜雪,他始终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着1963年那个春天在“雷锋班”授旗仪式上立下的铮铮誓言:做雷锋那样的人!他用65余本厚厚的《学习雷锋日记》和数十年如一日的行动,在平凡的岁月里书写着不凡的“雷锋人生”,将雷锋精神深深刻进古城温润的肌理,汇聚成一道温暖人心的时代风景。
军旅铸魂:一面旗帜定下一生航向
1963年2月17日的沈阳军区礼堂,军号声穿透寒冬。来自86520部队指挥连的秦兴海与连队的10名战友站在队列里,看着“雷锋班”的红旗在军乐中升起。秦兴海聆听着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事迹,年轻的心脏像被春雷震响。他与雷锋同岁、同一年入伍、同在沈阳军区服役,那份“同频”的震撼,让他在当晚的煤油灯下,用冻得通红却异常坚定的手,在日记本扉页上重重写下:“雷锋同志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我一定要克服缺点,像雷锋一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行字,从此成为他一生的烙印。
北国的冬天,零下20摄氏度的寒风能冻裂铁皮。秦兴海却主动承包了全连厕所的清扫任务。冰碴子划破手掌,血珠滴在冻土上瞬间凝结,他裹紧棉袄继续擦拭,日记里写道:“冻手不冻心,为人民服务的热乎气儿能焐化冰雪。”食堂拉煤,上百斤的煤块压弯了战友的腰,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搭把手,汗珠浸透军装,在寒风里结出白霜,他却笑着说:“雷锋能冒雨送大娘回家,咱扛几袋煤算啥?”
战友张国平至今记得,1965年夏天他老家遭了洪水,秦兴海把攒下的50元探亲费全寄到了他家。“钱没了能再积攒,战友受伤的心碎了补不回,这不是一时热血冲动,我要坚持帮助困难的战友。”秦兴海的军旅日记里,记满了这样的“小事”:1967年3月5日,帮驻地小学修补围墙;1970年7月12日,深夜送迷路老人回家;1975年10月26日,替生病战友站岗…… 每一页都浸着汗水,也映着初心。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在探亲火车上的善举。1963年5月19日,他在回苏州探亲的火车上看到对座有一名瘦弱的老者,从上车起就没有吃过饭,时不时用祈求的眼神望着他。“当时我在想他是不是饿了,就把自己的四个热包子都给他吃了。”那一上午,虽然秦兴海的肚子饿得慌,心里却挺开心,“当时就感觉帮助别人是件很快乐的事。”
乡关扎根:一串号码连起百家冷暖
1982年深秋,秦兴海告别军营,转业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苏州,分配到东吴丝织厂新吴分厂工作。他脱下军装后,却把“为人民服务”的习惯带进了车间。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把织机擦得能照见人影;新工人小李家贫,他经常悄悄往其饭盒里塞两个白面馒头;老职工张师傅生病,他蹬着自行车跑遍全城抓药,药包上总缠着一张写着“按时服药”的纸条。
1998年除夕,阖家团圆之际,厂区电路突发故障。年夜饭刚上桌,秦兴海闻讯抓起工具包就冲向车间。在机器的轰鸣声中,他忙碌穿梭,汗水浸透衣衫。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他疲惫地蜷缩在值班室的长椅上,手里还攥着半块冷掉的梅花糕。窗外烟花绚烂,车间机器重新欢唱,这就是他心中最踏实的“年味”——一个当代工人对“岗位螺丝钉”精神的无声诠释。
2000年1月退休那天,秦兴海在社区多个楼道墙上贴了张红纸:“有困难找老秦,电话:62749021。”在手机没有普及的年代,这个七位数成了社区的“生命线”。里河新村的朱阿姨至今记得那个暴雨天,她腿摔了没法换社保卡,秦兴海带着银行工作人员深一脚浅一脚赶来,雨衣下的旧军装湿透了,却把社保卡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他说:“答应了群众的事,就是下刀子也得来。”那天他的关节炎犯了,下楼时扶着墙直咧嘴。
家住里河新村的重残低保人员徐阿妹近期因为楼上卫生间渗水的问题向秦兴海求助,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作为社区优秀调解员,秦兴海沟通有技巧、办事很公正,总能给双方很多实质性的建议和帮助,深受大家信任。独居老人李奶奶记性差,他每天早上敲窗喊“吃药喽”,一喊就是十年。女儿秦继红说:“小时候家里电话总响,半夜也有人找,我埋怨过,爸却说人家找我,是信任我。”那串号码,后来被居民们刻在了社区的“暖心墙”上,居民王先生说:“老秦的电话,有时比110还灵。”
群蜂酿蜜:一面队旗聚起满城春风
2010年春天,觅渡社区组建“小蜜蜂”志愿服务社,“小蜜蜂”寓意着勤劳、奉献、酿造甜蜜。70岁的秦兴海接过“兵蜂服务岗”队旗时,手微微发颤。“5个人也是队伍,要学雷锋那样实打实干事。”他给队员们定了“三必到”:突发事件必到、矛盾纠纷必到、特殊群体必到。
每天清晨,当古城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巷口,人们总能看见秦兴海带领着他的“兵蜂”队员们,臂戴红袖章,精神抖擞地穿梭在街巷里弄。他们细心巡逻,守护一方安宁;他们弯腰捡拾,维护环境整洁;他们耐心倾听,调解邻里纷争。风雨无阻,寒暑不辍。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工作量巨大。秦兴海主动请缨,负责2幢楼的普查工作。6层高的楼房,8个单元,近百户居民,他白天挨家挨户摸底登记,晚上整理资料。恰逢女儿生病住院,他硬是挤出志愿服务间隙的时间去医院照料,疲惫写在脸上,却从未落下一项工作。家属见他在病床边整理普查表,嗔怪他“不顾家”,他却指着表格说:“这上面300多户,都是我的家人。”
15年过去,5人的小分队成为190人的大家庭。他们巡逻的脚步印在行程2.8万公里的街巷上,调解的385次纠纷里,藏着张家漏水、李家占地的琐碎,也藏着“让邻里像家人”的温暖。截至目前,秦兴海和队员们共义务巡逻27950余人次,各类服务总时长超65300小时。如果把这些时长换算成日夜,就是2700多个晨昏的坚守。社区书记杨春燕说:“秦老就像块磁石,把零散的光聚成了火炬。”
薪火相传:一本日记续写雷锋精神
2023年,秦兴海的名字相继荣登二季度“江苏好人榜”、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当街道和社区领导一起把“中国好人” 的证书送到家时,秦兴海正在给孤寡老人缝制棉鞋。他摩挲着证书,却把更宝贝的65本日记搬到社区展览。泛黄的纸页上,1963年的字迹还带着少年意气,2024年的记录里,多了“教小志愿者帮助居民用手机挂号”的新鲜事。
秦兴海说:“这么多年来,我写了60多本《学习雷锋日记》,还都保存着,没舍得丢。”在青少年讲堂上,他举着雷锋补丁袜子的照片笑:“这才是最潮的破洞货。”孩子们围着他,听他讲“雷锋班”的故事,也听他说“做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的感悟。受他资助的大学生小王,毕业后成了社区社工:“秦老说雷锋精神不是历史,是现在进行时,我想接着写他的日记。”
如今,秦兴海的晨巡多了个小尾巴——12岁的孙子秦振坤,暑假里背着迷你版工具包跟着他到社区捡拾垃圾、打扫卫生。“爷爷说,雷锋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想做颗小铆钉。”
今年初,85岁的秦兴海应社区之邀,在“强国复兴有我 —— 百姓故事汇”活动中,给小蜜蜂志愿服务社的志愿者们,讲述自己的志愿服务故事和多年来的服务心得。他说:“我虽然退休了,但共产党员的党性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退。我要永远像雷锋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地为人民服务中去。”
夕阳爬上瑞光塔时,秦兴海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条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路。65年风雨,他从“秦同志”变成“秦老”,从满头青丝到银发如雪,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热望,从未降温。就像他在最近日记里写的:“雷锋没走远,他在每双伸出的手里,在每个温暖的笑容里。我的日记会写完,但他的故事,永远写不完。”
在苏州古城温婉缠绵的烟雨中,在觅渡社区寻常巷陌的烟火气里,退役老兵秦兴海的故事,如同一曲悠长的评弹,吟唱着坚守与奉献的旋律。60余本日记,是时光的刻度,更是初心的见证;60余载岁月,青丝成雪,诺言如金。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却用无数微小的善行,垒砌起一座精神的丰碑——那是一个战士对誓言的终生守望,一个党员对宗旨的生动践行,一个普通人用一生书写的、关于“人”字的最温暖注解。秦兴海,这位矢志不渝的“活雷锋”,正以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伟大,恰恰蕴藏于平凡的坚守;而信仰的光芒,足以穿透漫长的岁月,照亮人心,温暖一座城。(朱熙君、陆春芳、祝佳凡)
来源: 光明网
【考试】
(一)序章:一张卷子的诞生
五月末的南方,空气里漂浮着潮湿的铁锈味。印刷厂的排风扇昼夜轰鸣,像一只老迈的肺叶在喘息。老周戴着深蓝色袖套,在校对灯下一行行核对即将付印的“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语文试卷。他今年五十七岁,再过三年退休,却仍旧固执地坚持人工检字,理由是“机器永远闻不到油墨里藏着的那股杀气”。
这一夜,老周在校对到作文题时忽然停住。那是一行仿宋体三号字:“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考试的意义,到底在于分数,还是在于成长?’”老周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酸胀的眼睛。四十年前的那个清晨,他也在一张印着“恢复高考”四个粗黑体大字的油印卷子上写下第一篇作文,题目叫《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那一年,他十七岁,手心全是汗,钢笔在卷面洇出一朵小小的蓝花。此刻,老周用拇指摩挲着纸张,像抚摸自己少年时代留下的疤痕。他忽然想:这张卷子被装进牛皮纸袋、贴上封条、押运进保密室,再被层层看守,最后被无数支颤抖的笔填满,最终变成一个个数字,那些数字又变成命运的分岔口——这一切,真的只是“考试”两个字可以概括的吗?
老周把校对稿轻轻放下,走到车间外的走廊。天快亮了,远处教学楼的灯一盏盏熄灭,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掐灭的星火。他想起自己女儿,今年也高三,成绩忽上忽下,像一条在浪尖上挣扎的小鱼。女儿常说,爸,你不懂,现在的考试和你们那时候不一样了。老周点了一支烟,烟雾在昏黄的灯下盘旋。他想,也许真的不一样了,可那股杀气还在,只是换了一种更精致、更隐蔽的面孔。
(二)第一考场:七点三十分
林骁踏进市一中实验楼的时候,鞋底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嗒嗒”声。那声音像一把小锤,每一下都敲在他太阳穴上。他昨晚两点才睡,此刻眼底布满血丝,却异常清醒。母亲凌晨四点起床给他煮了桂圆红枣鸡蛋,他吃不下,只喝了两口汤。母亲站在厨房门口,围裙上沾着水渍,欲言又止。林骁知道她想说什么——“别紧张,就当平时练习。”可这句话在过去一年被重复了无数次,早已失去了安慰的效力,只剩下回声般的空洞。
考场门口,金属探测仪发出滴滴声。监考老师甲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教师,短发,银边眼镜,眼神像一把精准的游标卡尺,在每个人脸上量过去。她接过林骁的准考证,用指甲在照片边缘轻轻一刮,确认无误后,才在座位表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勾。林骁的座位靠窗,第二排。窗外是一棵香樟,阳光透过叶子,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像一摊摊融化的铜钱。
七点四十五分,广播里响起《致爱丽丝》的钢琴曲,提醒考生即将启封试卷。监考老师乙撕开牛皮纸袋,发出“刺啦”一声,那声音像撕开一层皮肤。林骁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想起上周的晚自习,班主任老赵把他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张排名表。他的名字在第17位,比上次月考跌了9名。老赵没说话,只把红笔横在“17”这个数字上,轻轻一点。那一红点像一粒朱砂痣,烙在林骁的视网膜上,三天未褪。
试卷发下来,第一页是选择题,密密麻麻的选项像蚂蚁行军。林骁深呼吸,把笔帽咬在嘴里,舌尖尝到一股塑料味。他告诉自己:先做古诗鉴赏,那是他的强项。可当他看到第一道题“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脑子忽然一片空白。那首诗他背过无数遍,此刻却像被封存在琥珀里,隔着一层透明的窒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窗外的香樟叶子忽然剧烈晃动,起风了。林骁抬头,看见一只麻雀撞在玻璃上,发出“咚”的一声,又仓皇飞走。他低头,发现手心全是汗,答题卡边缘被洇出一圈模糊的指纹。
(三)第二考场:同一时刻
与林骁的焦灼不同,同一栋楼的第三考场里,周茉正用食指轻轻摩挲着橡皮擦。她成绩稳定在年级前十,但这次模拟考对她意义特殊——如果总分超过680,她就能获得北大暑期学堂的入场券。父亲上周特地从北京回来,带她去吃了海鲜自助。父亲很少回家,在饭桌上却一反常态地给她夹菜,说:“茉茉,爸爸当年没考好,只能去当兵,后来转业进了企业,一辈子在酒桌上谈合同。你不一样,你是我们周家的希望。”父亲的手背上有淡淡的烟斑,那是常年被客户敬烟留下的印记。周茉低头扒饭,喉咙发紧。她想起母亲离婚后独自开美甲店,手指常年浸泡在丙酮里,皴裂得像干涸的河床。
此刻,周茉的笔尖在草稿纸上写下一个“稳”字,又画了一个圈。她做题的速度不快,却极有条理,像一位老练的棋手,每落一子都要计算后续五步。可当她翻到作文题,眉头还是微微蹙起。那道题目让她想起小学三年级第一次考砸数学,父亲把卷子摔在地上,说:“你怎么这么笨?”那天夜里,她躲在卫生间,把卷子撕成碎片,冲进马桶。水流打着旋儿,把纸屑吞没,也把她的一部分自尊卷走。
周茉深吸一口气,在作文纸上写下标题:《分数之外》。她的字迹工整,像一排排被修剪过的冬青。她写道:“考试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恐惧,也照见我们的渴望。可镜子本身没有温度,温度在于我们如何在镜子前站立……”写到这里,她忽然停住,笔尖在纸上留下一个黑点。她想起母亲昨晚发来的微信:“茉茉,考不好也没关系,妈妈给你存了留学的钱。”那一刻,她鼻子发酸,却不敢哭,怕眼泪把答题卡弄脏。
(四)走廊上的监考老师
十点整,考试进行到一半。楼道里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的嗡嗡声。监考老师甲——那个短发女教师——站在走廊尽头,透过窗户望向下面的操场。那里,高一的学生正在上体育课,传来断断续续的笑声。她想起自己1993年参加高考,考场设在一所乡镇中学,课桌坑坑洼洼,她用垫板垫平,才勉强写完作文。那年作文题是“尝试”,她写的是第一次学骑自行车,摔得膝盖流血,却倔强地爬起来继续。后来,她真的考上了师范,成了老师,也真的在一次次“尝试”中,把最初的热血熬成了此刻的疲惫。
她低头看表,还有四十分钟。她想起上周教研会上,校长说:“我们要提高一本率,这是学校的生命线。”她没反驳,只是想起自己班那个叫李想的男孩,父亲去世,母亲摆地摊,成绩中等偏下,却写得一手好字。那天放学后,李想塞给她一张纸条:“老师,如果我考不上,能去当兵吗?”她把纸条夹进教案,回家路上,眼泪被风吹得满脸都是。
此刻,她轻轻推开考场的门,目光扫过每一张低垂的脸。她看见林骁的笔停在半空,像一支被冻住的箭;看见周茉的背挺得笔直,像一株倔强的竹;看见角落里一个女生在抖腿,鞋跟敲击地面,发出细碎的“哒哒”声。她忽然觉得,这些被考试定义的孩子们,其实也在定义着考试本身——他们的呼吸、颤抖、迟疑、决绝,都在给那张冰冷的卷子注入滚烫的血肉。
(五)父亲的来电
十一点,距离考试结束还有三十分钟。林骁终于把作文写完,最后一个句号画得像一颗小炸弹。他甩了甩酸痛的手腕,抬头看窗外。香樟树影里,阳光已经移到西侧,像一块倾斜的金箔。他想起父亲昨晚的来电。父亲在工地做钢筋工,每天爬几十层楼,皮肤晒得黝黑。电话里,父亲的声音沙哑:“骁骁,别有压力,考不好就回来,爸教你绑钢筋,一天也能挣三百。”林骁当时鼻子一酸,却故作轻松:“爸,你放心,我肯定能考上。”挂掉电话,他躲进厕所,把水龙头开到最大,让水声掩盖抽泣。
此刻,林骁的目光落在作文纸上。他写的是父亲去年冬天在脚手架上摔下来,右腿骨折,却瞒着他,直到他放寒假回家,看见父亲拄着拐杖在院子里劈柴。他写:“那一刻,我明白了,考试的意义不是逃离,而是带着那些爱我的人的伤口,一起走向更远的地方……”写到这里,他的视线模糊了,赶紧抬手擦眼睛,怕泪水滴在卷子上。
(六)周茉的抉择
十一点十五分,周茉检查完最后一道选择题,忽然发现答题卡上有一道2分的填空题漏写了。她的心跳骤然加速,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那道题考的是《红楼梦》里贾宝玉的别号,她明明记得是“怡红公子”,却在填涂时跳过了。她抬头看监考老师,老师正在讲台前整理试卷,目光平静。周茉的指尖开始发抖,2分,意味着她可能从680跌到678,意味着北大暑期学堂的资格可能泡汤。她想起父亲昨晚发来的微信:“茉茉,爸爸在北京等你。”
她深吸一口气,把橡皮擦攥得发烫。她知道自己可以悄悄补上,没有人会注意。可当她低头,看见作文纸上自己写下的那句话——“考试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恐惧,也照见我们的渴望”——忽然像被烫了一下。她想起母亲说的“考不好也没关系”,想起父亲酒桌上被灌醉的背影,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每一次考试都像在走钢丝,下面是万丈深渊。她忽然明白了,那2分不是分数,是一面镜子,照见她是否愿意为了“完美”而背叛自己。
周茉松开橡皮擦,把笔帽盖好。她决定不补那2分。这个决定让她浑身发抖,却也让她第一次感到某种轻盈。她想起小学三年级那个夜晚,撕碎的卷子被马桶冲走,而此刻,她选择让那2分留在空白里,像一道未愈合的伤口,提醒她:成长不是填满所有空白,而是学会与空白共处。
(七)终章:收卷之后
十一点三十,铃声响起。监考老师甲大声说:“全体起立,停止答题!”教室里一阵窸窣,像风吹过麦浪。林骁最后一个站起来,他的腿麻了,差点摔倒。他看见前排的女生把卷子按在胸口,肩膀微微耸动;看见周茉把笔轻轻放在桌面,像放下一件沉重的行李;看见监考老师乙用密封条封住试卷袋,动作熟练得像在缝合一道伤口。
走出考场,阳光刺眼。林骁眯起眼睛,看见父亲站在校门口,手里拎着一袋苹果。父亲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裤脚沾着泥点。林骁跑过去,父亲把苹果递给他,说:“你妈让我给你带的,说补维生素。”林骁咬了一口,苹果很甜,汁水顺着嘴角流下。父亲拍拍他的肩:“走,回家吃饭。”
周茉走出校门,母亲站在马路对面,手里拿着一杯冰美式。母亲今天没穿围裙,头发新染了栗色,在阳光下泛着柔光。周茉跑过去,母亲把咖啡递给她:“没考好也没关系,妈妈带你去吃日料。”周茉摇头,笑着说:“妈,我考得挺好的。”她没说那2分的空白,她觉得母亲能懂。
老周在印刷厂门口抽完最后一支烟,把烟头摁灭在垃圾桶上。他抬头看天,云很淡,像被橡皮擦过的铅笔痕。他想起早晨校对的那张作文题,想起自己十七岁写下的《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他忽然笑了,皱纹像涟漪一样荡开。他想,也许考试的意义,从来就不在于分数,也不在于成长,而在于那些被我们忽略的、转瞬即逝的、像麻雀撞玻璃般的小小瞬间——它们如此脆弱,却又如此真实,如此滚烫,足以照亮漫长的一生。
(八)尾声:许多年以后
很多年后,林骁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参与设计了一座图书馆,馆名就叫“考试”。图书馆的外墙是透明的玻璃,阳光穿过,在地面投下香樟树影般的斑驳。开幕那天,他站在大厅里,看见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坐在角落里看书,膝盖上放着一张草稿纸,上面写着一个“稳”字,被画了一个圈。他走过去,轻声问:“小姑娘,你在准备考试吗?”女孩抬头,眼睛亮晶晶的:“不,我在看小说,考试只是顺便的事。”林骁笑了,想起多年前那个在考场里颤抖的自己。
周茉后来去了北大,毕业后成了一名纪录片导演。她拍的第一部作品叫《空白》,讲述一群高考生如何面对一道无法得分的题。首映礼上,她站在台上,说:“那2分让我明白,人生不是所有空白都要填满,有些空白,是光进来的地方。”台下掌声雷动,她看见母亲坐在第一排,眼角有泪,却笑得像一朵迟开的向日葵。
老周退休那年,学校把历年试卷做成了一座档案室。他走进去,在1993年的那摞卷子里,找到自己当年的作文复印件。纸已经泛黄,字迹却依然清晰。他读到最后一段:“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我以为我在逃离土地,后来我才明白,我不过是把土地背在了肩上,走向更远的地方。”老周合上档案,窗外香樟树影摇晃,像无数只小手在向他告别。
而那张印着“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的语文试卷,被密封在牛皮纸袋里,贴上封条,运进保密室,再被碎纸机打成雪花般的碎片。那些碎片被倒进回收桶,最终变成再生纸,印成新的试卷,新的作文题,新的选择题,新的空白与分数。它们循环往复,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恐惧、渴望、眼泪与微笑,流向未知的远方。
在这条河的尽头,也许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金光闪闪的录取通知书,只有那些被时间冲淡却依旧滚烫的瞬间——它们像老周指间的烟灰,像林骁手心的汗,像周茉漏掉的那2分空白,像麻雀撞在玻璃上的那声“咚”,像父亲工装上的泥点,像母亲指尖的丙酮味,像监考老师甲眼角的细纹——它们如此微不足道,却又如此不可或缺,因为它们提醒我们:
考试,从来不只是一张卷子。
考试,是我们如何与这个世界,以及与自己,面对面站立。
(全文完)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