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格策美文教你学写《童年 读书笔记400》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04 2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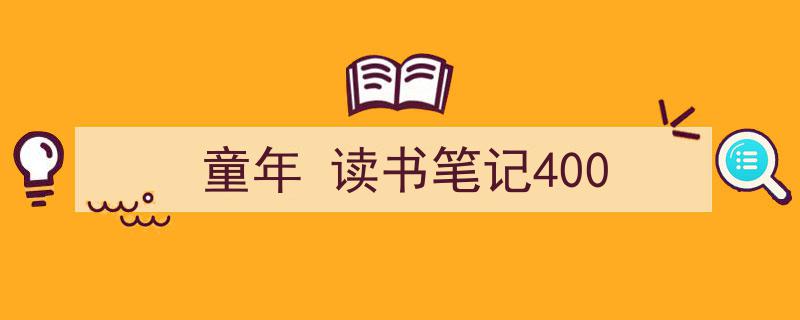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童年读书笔记的400字作文范文,并附带了写作注意事项:
"范文:童年的印记——我的读书笔记"
童年的记忆如同散落在时光沙滩上的贝壳,五彩斑斓,其中,读书笔记是我珍藏最久、也最闪耀的一枚。它不仅记录了我阅读的足迹,更是我童年时光里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和成长的见证。
记得小时候,我总爱缠着妈妈给我讲故事。从简单的绘本到稍复杂的儿童小说,每一次阅读都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我会在书页边写下简单的想法,比如画个小星星代表喜欢,画个问号表示疑惑。渐渐地,我开始尝试自己写读书笔记。起初只是抄写喜欢的词句,后来学着写下故事的主要情节和自己的感受。虽然字迹稚嫩,内容简单,但每完成一篇笔记,都让我有满满的成就感。
这些童年的读书笔记,记录了我对白雪公主的同情,对匹诺曹的担忧,对孙悟空的惊叹。它们像一个个小小的坐标,标记着我认知世界、形成价值观的过程。当我再次翻阅这些泛黄的纸页,那些生动的字句和稚嫩的想法依然清晰可见,让我仿佛穿越回那个充满好奇与幻想的童年。它们不仅锻炼了我的写作能力,更培养了我热爱阅读、勤于思考的习惯,这些宝贵的品质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童年的读书笔记,是我与书籍最美好的初遇,是我
小时候,我常常挨父亲的打,分到的饭菜也是最差的
在延安的窑洞中,昏黄的灯光摇曳,毛泽东正接受着采访。他的神情平静如水,说出的话语却如石子投入心湖,泛起层层涟漪:“小时候,我常常挨父亲的打,分到的饭菜也是最差的。”这话一出口,仿若时间都为之凝滞。人们本以为,面对这样的过往,毛泽东或许会苦笑,以一种略带无奈的姿态提及;又或许会愤怒,控诉曾经所遭受的不公。然而,他只是平静地诉说着这些细节,语气中没有丝毫的怨怼,仿佛在讲述一段与己无关的故事。这些童年的经历,是他成长路上的荆棘,刺痛过他,却也磨砺了他。但在这之后,似乎再也没有人提起过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它们被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偶尔被有心人打捞起,却也只是惊起一小朵浪花,很快又归于平静。饭桌上的“教育”与拳头
韶山冲的晨雾还没漫过田埂,毛家屋后的水渠已泛起浑黄的波光。少年毛泽东常蹲在渠边,就着流水抹把脸,把书册垫在膝盖上背书,有时端着粗瓷碗,就在青石上扒完一顿饭。这渠水见过他朗朗的书声,也映过他挨揍后泛红的眼眶。父亲毛贻昌的算盘珠子总比田埂上的露水醒得早。这个土生土长的湘人不识几个字,指节却比稻穗还熟悉田垄的纹路。他靠种田卖米攒下的银元,把家从佃农的草屋撑成了地主的院落,性子却随谷仓一起收紧——更谨慎,更吝啬,也更像晒裂的土地般暴躁。"会念书有啥用?读不出钱来。" 他啐着唾沫,不信那些穿长衫的酸气。作为长子的毛泽东,在私塾里写的字比先生还周正,墨迹落在纸上像生了根。可父亲眼里从没有赞许,只有算盘珠子般噼啪作响的挑剔。那天饭桌上,毛泽东正背《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 的余音还没散,父亲的巴掌已经拍在书上。"你要念这个,还是要种田吃饭?" 黑着脸的质问,比桌上的咸菜还涩。多年后,毛泽东记得最清的不是私塾里的字句,而是饭桌上的分食。父亲总给自己盛满满一碗白米饭,弟弟也能分到小半碗,轮到他,只有锅底带着糊味的残羹。"你不是要当读书人么?吃差点的,看你还能记住多少字。" 话落,勺子 "哐当" 扔回盆里,汤水溅在桌布上,像一朵朵委屈的泪渍。他从不顶嘴,只是盯着桌面发呆,默默把饭扒进嘴里。放下碗就往田埂跑,有时干脆翻过山岭,去别人家借书看——哪怕是缺了页的破书,也看得比白米饭还香。"父亲打我最多的几次,不是我偷钱、不是我偷吃,而是我看书。" 后来他轻描淡写地说,可那时的疼,早刻进了骨头里。《毛泽东自述》里记着件事:14 岁那年,他躲在屋后菜地看《三国演义》,看得入了迷,连回家的时间都忘了。父亲抓着藤条追打,从堂屋到厨房,母亲拦在中间哭,他在地上滚来滚去,满腿血痕却咬着牙不吭一声。那晚,他偷偷跑到溪边,把《三国演义》埋进泥里。不是不爱了,是怕了——怕那藤条再落在身上,更怕心爱的书被父亲撕成碎片。在父亲心里,"儿子读书是花钱",不是往地里撒种子,是往水里扔银元。每次毛泽东怯生生提 "上学",他总瞪着眼问:"你读完能种多少田?"母亲文七妹却是另个模样。她识字不多,心却比韶山冲的清泉还软。悄悄拿出私房钱给儿子买书,被发现后,家里吵了好几天。父亲骂母亲 "软蛋",顺手给了毛泽东两个耳光。他没哭,也没解释,转身回房,把《资治通鉴》紧紧按在胸口,一字一句往下读。"我父亲很强硬,但我不比他差。" 多年后他这样说,可那时的他,还只是个常被支去背粪、只能吃锅巴饭的少年。父亲不是不管他,是管得太密,像田埂上的篱笆,把他圈得死死的。从清晨起床到深夜关门,饭桌、地头、灶房,处处都是父亲的声音:"别读了"" 去挑水 ""不许去祠堂听戏"。可毛泽东偏不。他把每一次责骂都刻在骨头上,把每一份不甘都藏进心里。那些被压抑的渴望,那些饭桌上的委屈,那些藤条下的倔强,后来都成了他脚下的路——一步步,走向比韶山冲更远的地方。逃离米行
十五岁的韶山冲少年,终究没能逃过父亲的算盘。毛贻昌对儿子那股 "读书疯" 忍到了头,托人把毛泽东送进湘潭的米行当学徒。说是 "去见大市面",算盘珠子里藏的心思却再明白不过——学做生意,断了书本的念想。米行是座方正的牢笼,米袋堆得比天花板还高,空气里飘着陈米的气息。毛泽东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每日里抬米、打算盘、称斤两,粗粝的米粒磨着掌心,也磨着心口的劲。每到黄昏,他总站在最高的米袋上往街口望,远处的炊烟缠在树梢,像根无形的绳,勒得他心口发闷。"我不想卖米,我想读书。" 他跟米铺老板说这话时,声音里带着没褪尽的少年气。老板眯着眼笑,手里的算盘打得噼啪响:"你父亲早跟我交代了,你要是跑了,他可不认账。" 毛泽东咬着牙应下,活计一天不落,只是到了夜里,就点起豆大的煤油灯,借着微光偷看捡来的旧报纸,字里行间的世界,比米袋堆成的山更高远。秘密终究藏不住。一次被师兄撞见告了密,迎来的又是一顿打——这次,父亲竟亲自从韶山冲赶来了米行,指着他的鼻子骂 "白眼狼",唾沫星子溅在他的长衫上。他没争辩,垂着的眼睑遮住了眼里的光。只是第三天凌晨,天还没亮透,他趁着米行的人都在酣睡,从吱呀作响的后门溜了出来。青布鞋踩过带露的石板路,一路往前,直到东山书院的朱漆大门撞进眼里。那年,他十六岁。书院哪肯收一个逃出来的学徒?他就蹲在后门的老槐树下等,等先生们下课,拦着人说:"我能背《论语》,能写千字文,不要束脩,只要让我坐在最后一排听。" 固执的眼神像韶山冲的石头,磨得先生动了容。于是,穿着旧长衫的少年,在最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饭还是最差的——冷馒头、咸菜、温不透的粥,但这次,是他自己选的,没人再把带糊味的饭往他碗里扒。毛贻昌听说儿子逃去了书院,气冲冲找过来,站在书院门口就骂开了,被书院长劝了半天才走。毛泽东在教室里没动,指尖攥着笔杆,心里只有一句话:"我要的是书,不是你的账本。"这个选择几乎斩断了父子情分。毛家不再给他送米送衣,乡邻们都在传,毛贻昌要 "断绝父子名分"。可他没退,搬去朋友家借住,靠抄书、打杂换口饭吃。"我知道他恨我,但我不后悔。" 冷战持续了好几年,直到 1910 年,毛泽东考进湖南一师,拿了第一名的消息传回韶山冲。毛贻昌托人捎来一封信,没有半句问候,也没有丝毫软话,只在末尾写着:"念完书,也要懂种田。"父子间的裂痕终究没能弥合。毛泽东再没回家过过年,就连父亲病重时,也没能赶回去。1919 年,毛贻昌去世的消息传来,他只写了封信给弟弟,托他们料理后事。信里说:"他给了我身体,也给了我苦难,我不恨他。"纸页上的字迹平静,像多年前在延安窑洞里,他说起童年时那样,不带怨怼,只余一段被时光磨洗过的过往。思想成形后,父亲的影子仍在
离开韶山冲多年,毛泽东的脚步早已踏过父亲眼界里的田垄与账本。他没成父亲期望的庄稼汉,也没成算盘珠子精的商人,反倒成了学生、思想者、组织者——从东山书院的角落,到湖南一师的讲堂,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案前,日子过得拮据,心志却像田埂上的野草,铆着劲往上长。父亲那道刻着“暴躁”二字的门槛,他早就一步跨过去了。在湖南一师时,他组织新民学会,在油灯下和同伴们讨论家国命运,案头常摊着《天演论》与《新青年》。在这些振聋发聩的文字里,他为少年时的“反叛”找到了清晰的逻辑支点。“社会不该像我父亲那样压住儿子,更不该像地主那样压住穷人。”他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时,笔尖仿佛带着当年饭桌上的热气与藤条的痛感。1919 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涌到长沙,他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笔下的文章像投枪,直刺官僚与买办的痛处。那些文字里没直接出现“父亲”两个字,却处处长着少年时被打压的记忆——他写农民的苦,写“孩子不能选自己的命,被父权捆得死死的”,与其说是政治檄文,不如说更像带着体温的回忆。朋友曾问他:“你父亲是不是特别反对你出来做事?”他望着窗外的雨,没正面,只淡淡一句:“他不是反对我做事,是反对我读书。”他心里透亮,毛贻昌从不懂什么主义,更不在乎什么革命,只认一亩三分地的收成和账本上的盈亏。像他这样“从家里跑出去”的儿子,在父亲眼里终究是个异类。可恰恰是这种“异类”的自觉,让他彻底挣开了旧家庭的桎梏,大步走进了更辽阔的天地。在他眼里,父亲不是天生的恶人,只是旧时代压迫者的一个缩影——不是出于恶意,而是那个体系运转的必然。他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得像说别人的故事,却透着一种斩断过往的冷。那不是恨,是切割。1939 年,延安保安的窑洞里,昏暗的灯光摇曳不定。埃德加・斯诺坐在简陋的木桌旁,目光专注地看着对面的毛泽东,轻声问道:“你的家庭对你有怎样的影响?”毛泽东靠在椅背上,眼神平静,思索片刻后缓缓说道:“我父亲是个暴躁的人,经常打我,给我吃最次的饭。” 他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仿佛那些过往的苦难早已化作轻烟。这句话,被斯诺如实记载在《西行漫记》中,成为了后人研究毛泽东童年心理的重要线索。很多人惊讶于他的坦诚,没有丝毫的拔高与修饰,既非歌颂亲情的温暖,也非控诉苦难的沉重,只是一句云淡风轻的描述,却如同一记重锤,敲响在人们的心间。“最差的饭”,那不仅仅是一碗粗茶淡饭。它是身份的标签,贴在少年毛泽东的身上,宣告着他在家庭中的低微地位;它是思想的约束,如同沉重的枷锁,锁住了他对知识与未来的渴望;它更是命运的原型,暗示着他似乎注定要在这片土地上,重复着祖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少年毛泽东被强制分配着低等食物,正如他被认定“读书无用”,只能回去务农一样,他咽下的每一口冷饭,都是一个农民家庭对“书生”梦想的不信任,是对他灵魂的一次次碾压。毛泽东并非是那种用“怀念”来粉饰过去的人,他从不刻意美化自己的出身。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能走出韶山冲,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是一场长达数年的艰苦博弈。他逃过父亲的藤条,那藤条落下的呼啸声仿佛还在耳边;他也逃过了米行的束缚,那堆积如山的米袋和昏暗的灯光,见证了他曾经的挣扎与不甘。每一步,都是他用坚定的意志和对知识的渴望,为自己铺就的道路。然而,他从不否定毛贻昌的存在价值。在一些私下的谈话中,他曾说:“我父亲很会过日子,早上五点起,晚饭后还数账,一分一毫都精细。” 那语气中,有着对父亲持家能力的敬佩,但更多的是不认同。他理解毛贻昌为何要打他,为何不给好饭吃,那不是仇恨,而是两个灵魂在认知层面的激烈碰撞。毛贻昌坚信着秩序、等级与节俭,如同坚守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而毛泽东,却一心想要冲破这些束缚,去拥抱一个全新的世界,两人之间的鸿沟,深如马里亚纳海沟,根本无法达成和解。哪怕在毛泽东功成名就之后,他也从未刻意去“美化”这段家庭经历。不像有些人,总是把自己的“家风”说得如何严谨,把父亲说得如何英明神武。他只是淡淡地说“他常打我”“分我最次的饭”,简单的几个字,却道尽了那段岁月的残酷与真实。因为那段成长,没有丝毫的温柔可言,全是挣扎。每一个夜晚,在米行的煤油灯下偷看旧报纸时的提心吊胆;每一次被师兄告密后,遭受父亲打骂时的委屈与愤怒;每一回站在米袋上,望着街口时心中的迷茫与不甘,都成为了他生命中无法磨灭的印记。更重要的是,这段父子冲突,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后来对社会结构的理解。他早年提出“打破旧家庭”,反对“家长制”,这些思想的根源,都能在他与父亲的矛盾中找到。他不是仅仅读了几本书、听了几场演讲就走上了革命道路,而是在饭桌边的饥饿与屈辱中,在米铺里的繁重劳作中,在藤条下的疼痛与泪水里,一点点地孕育出了不一样的信念。斯诺没有追问“你后来原谅你父亲了吗”,毛泽东也没有主动提及。但从他一生对家庭关系的沉默中可以看出,这段关系没有修复,也不需要修复。那是他成为“毛泽东”的必经之路,是他灵魂的淬炼之火。而那碗“最差的饭”,如同一个永恒的符号,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记忆深处,他从未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
开学前的“作业大战”:从我的童年到娃的假期
开学前的“作业大战”:从我的童年到娃的假期
作者:流水流远
快开学了,或多或少的家长在为孩子的假期作业焦虑吧,我倒想起些有意思的事。
其实孩子自觉的话,家长根本不用操心——我小时候就是这样。一拿到假期作业,当天就铆着劲写,通常前几天就能把会做的都完成得差不多。剩下不会的题,就每天翻出来看看,说不定哪天灵光一现就会了。所以整个读书期间,我爸妈几乎没为我的作业费过心。
不过关于作业,也有段好笑的回忆。我潜意识里总觉得妈妈语文好、爸爸数学厉害,有次遇到不会的拼音,自然第一想到的是找妈妈。可妈妈说:“去问你爸。”我捧着书去找爸爸,他又摆摆手:“问你妈去。”就这么来来回回推了三次,我委屈得直哭,以为他们明明会,就是故意欺负我不告诉我。后来才知道,他俩其实都不会,又都不好意思说,现在想来也是好玩!
如今我也成了家长,自家两个孩子对待假期作业的态度,可半点没随我。整个假期,他俩心思全在玩上:要么凑在一起“打牌”“打麻将”;要么去院子里玩沙子,踢鞋子;要么去水坑里捉螃蟹,网鱼;要么在家看电视、出去闲逛……就不怎么想写作业。
家乡的天空
奔腾特意开视频说想让爸爸15号去接他们,说作业还剩一大堆,怕回来晚了补不完。可那阵实在走不开:一是他婆婆不想那么早回来,二是俩孩子一见面就吵,怕吵到楼下准备高考的哥哥,三是我那周要开线上家长会。
从那之后,奔奔几乎天天开视频问“什么时候来接我”,总念叨“还要等好久啊”“作业真的要补不完了”。我只好在线上帮他一点点梳理:剩下多少作业,哪些在家能做,哪些得等回来后完成。
总算接回来后,他倒还算听话。两天时间补完了二十多天的数学算数题,还赶完了一张手抄报,就是作文怎么都不想写,嘴里还一直抱怨:“为什么语文作业这么多!”
数学手抄报
我跟他说:“不是语文作业多,是你之前几乎没动笔呀。而且语文这学科,本就需要日复一日的积累!”
今天他写作业累了歇口气时,我翻出2022年6月24日记的一段他小时候的笑话讲给他听——
那时候他仰着小脸说:“我都没有哥哥,好可怜哦。”
我笑着接话:“妈妈也没有哥哥呀。”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认真地说:“妈妈,你必须再生一个。”
我问他为什么,他理直气壮地答:“给我生个哥哥。”
他听完自己也笑了。我逗他:“现在还让我给你生个哥哥不?”
他连忙摇头:“不生了。”
我追问为什么,他叹口气,一本正经地说:“不可能了呀!”
看着他那小模样,倒觉得这被作业“催着”的开学前时光,也多了些暖乎乎的趣味。
奔腾
世纪语文乐园:有喜欢写作的初中孩子们的作品,有愿意与学生坚持一周一稿的老师的作品,有实践后好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