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3招搞定《数学日记10篇20字》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06 1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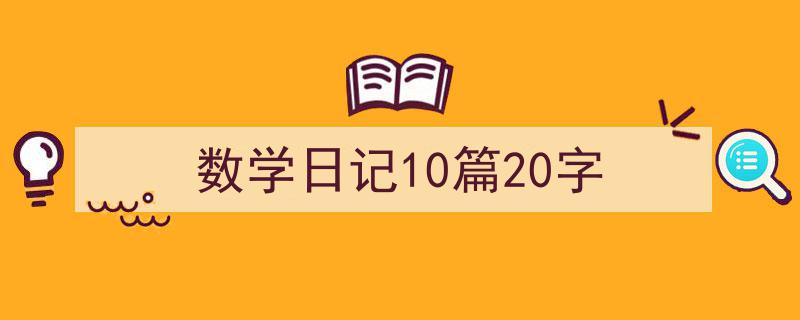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数学日记10篇20字作文,应该注意以下事项:
1. 简洁明了:每篇日记控制在20字内,表达清晰,避免冗长。 2. 主题明确:每篇日记围绕数学学习或生活展开,主题鲜明。 3. 逻辑连贯:日记之间要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如时间顺序、问题解决过程等。 4. 反思总结:每篇日记可以包含对数学知识点的反思、总结或感悟。 5. 积极向上: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展现对数学的兴趣和热爱。 6. 诚实客观:真实记录自己的数学学习情况,不夸大、不虚构。 7. 语言规范:使用规范的数学术语和表达方式,避免口语化。 8. 图文并茂:如有需要,可以适当使用图表、图形等辅助说明。
以下是一篇示例:
今天学习了三角函数,感觉很有趣。通过实践,我更好地理解了其应用。
趣味数学探索数字奥秘,中秋文化传承家国情怀
本网讯(通讯员 陈广春)7月17日,团山村村委会的活动室里既有数字游戏的欢乐,也有中秋故事的温情——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大风车”团队的郑兰帅老师,带领40名孩子开展“基础学科教育之数学+中国传统节日之中秋节”主题课程。从数字的奇妙规律到月饼里的文化密码,孩子们在知识与传统的浸润中,收获了思维的成长与情感的共鸣。趣味数学课:让数字变成“会游戏的朋友”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数字会变魔术哦。”上午8点,郑兰帅举起一个魔方,“比如这个魔方,每个面都有9个小格子,无论横加、竖加还是斜加,结果都是15,这就是数字的魔法。”孩子们好奇地围上前,想一探究竟。为了让数学学习更有趣,郑兰帅设计了“数字游乐园”系列游戏。“数字接龙”中,孩子们从1数到100,遇到3的倍数就拍手,小宇因漏拍被“惩罚”表演一个小节目,他背了一首数学儿歌,引得大家鼓掌;“图形拼拼乐”里,孩子们用七巧板拼出动物、人物,小欣拼的“小兔子”栩栩如生,郑兰帅称赞道:“你的图形感太棒了,将来可能成为设计师哦。”“生活中的数学”环节让孩子们发现数学的实用价值。郑兰帅拿出月饼盒、饮料瓶等物品,让孩子们测量长度、计算数量:“这个月饼盒能装8块月饼,我们25个人,需要几个盒子才够分?”孩子们立刻开始计算,有人用加法“8+8+8=24,还少1个,所以要3个”,有人用乘法“3×8=24,不够,要4个”。郑兰帅笑着说:“两种方法都对,数学就是帮我们解决生活问题的工具。”课程中段,孩子们制作“我的数学日记”,记录当天发现的数学现象:“我家有3口人”“今天喝了2杯水”“操场的边长大约有20步”。郑兰帅逐本翻阅,在小哲的日记上画了个笑脸:“你观察得真仔细,数学就藏在这些小事里。”中秋文化课堂:从月饼香甜到家国团圆
午后的活动室飘着桂花香(郑兰帅提前准备了桂花香囊),桌上摆着月饼模具、灯笼骨架和彩色纸。“你们知道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吗?”郑兰帅的问题引发了热烈讨论,小宇说:“因为月饼圆圆的,像月亮。”小雨说:“是为了纪念嫦娥。”郑兰帅用“故事串”的方式讲述中秋起源:从嫦娥奔月的神话,到朱元璋用月饼传递起义信号的传说,再到现代中秋团圆的习俗。他特意展示了不同地区的月饼图片:“广式月饼甜糯,苏式月饼酥脆,京式月饼咸香,就像我们国家的民族一样,各有特色,却都团圆在一个月亮下。”“中秋工坊”环节让孩子们动手体验传统习俗。他们分成两组,一组用黏土和模具制作“迷你月饼”,郑兰帅教他们压模时要用力均匀:“这样花纹才会清晰,就像奶奶做的月饼一样好看。”另一组制作灯笼,用彩纸糊在骨架上,再贴上“中秋快乐”的字样。小远在灯笼里放了一个LED灯,点亮后,灯笼瞬间变得五彩缤纷。“月光诗会”为课程画上圆满句号。郑兰帅带领孩子们朗诵《静夜思》《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虽然有些字认不全,但孩子们的声音充满感情。小欣还分享了自家的中秋习俗:“每年中秋节,爸爸都会带我们去奶奶家,大家一起吃月饼、看月亮,爸爸说这叫‘团圆’。”郑兰帅点点头:“团圆就是中秋节最珍贵的礼物。”理性与温情的双重滋养
离班时,孩子们的手里拿着自制的“月饼”和灯笼,书包里装着数学日记。郑兰帅看着他们互相约定“中秋节要一起看月亮”,在教案上写道:“数学培养逻辑思维,中秋传承家国情怀。当理性的光芒与温情的月光交织,孩子们的成长会更立体、更丰满。”夕阳下,活动室的窗户上映着灯笼的影子,仿佛提前点亮了中秋的月光。1930年,考生数学交白卷作文写28字,院长看后十分激动:破格录取
**数学0分,成了“文坛大人物”?有些人哪,生来就不走寻常路**
有些人一生都“苟且”地照本宣科,也有不甘心的,总喜欢打破常规。要说上学考试,谁进大学不是靠刷分呀?可1930年这一年,青岛大学招生榜上,有人居然数学挂了——零分,不及格,大红鸭蛋一个。本来没戏,他却偏偏被文学院院长闻一多一锤定音收下了。这要搁现在,怕是要被家长投诉、媒体围观吵上一阵。可那一年,大学就是这样“任性”:只看了他三句话的作文,二十八字,就此决定命运。
臧克家,其实就是那个考零分的小伙子。想象一下,他考完数学,估计也没啥底气——老老实实,怕都没敢和同班的同学拼聊这科。可人生这个东西,有时候就像开盲盒。你准备的地方失手了,“不抱期待”的角落却出点意外的光亮。
臧克家生在山东诸城,1905年的事,那时还没有什么高考状元、教育公平,甚至家里穷点富点差距极大。臧克家家底不薄,是本地小有名气的地主家庭。说起来,他家祖上当过清朝大官,隔三差五还写点诗,弄点字。这种家庭,娃还小就得识文断字,读读诗,《论语》《古文》之类更是耳边常被念叨。家里的老人都讲究文化,也希望能给子孙“铺个台阶”下,臧克家少年时的日子还算是“安稳书房”。
也别觉得地主出身就是早晚要进军阀队伍。臧克家那一代,赶上了变天年头。别看他小时候家里条件好,后来也是兵荒马乱、家道中落。可他自小书香“泡”得深,外头风雨再大,心里那点古旧诗意总是藏着的。临近五四运动时,他在县里最好的小学读书,忽然看到满街青年大喊“救国”,心里的火一下子被点着了。那会儿的孩子,有的是为了冲动,也有的是为了跟风,臧克家不太一样。他是真着了迷,开始琢磨新学问,停不下来的爱上了新诗——这种爱有点像青春期偷偷喜欢一个人,每天想一遍写一段。
说真的,臧克家一开始只对文学眼馋。但偏偏念到师范,碰见了理科。咱们现在看文科生被数学支配的恐惧,他那时可是“最早一批受害人”,什么几何、代数,怎么做都绕不过那个坎。再拼命也不行,他自己都觉得,国学还能得个“优”,理科,糊弄不了。
可人到了这种“自卑地带”,往往容易掉头往擅长的方向跑。他就靠着他的笔努力跟时代合个拍,在报刊杂志投诗,还真和大作家周作人通信。这时的臧克家,像个头发微乱的中学男孩,忧郁且倔强,用文墨和外面的世界交流。
命运的齿轮,又一次拧紧了。1926年,山东军阀张宗昌的稗官野史早已满城尽知。臧克家实在看不惯,干脆丢下学业,去了当时革命大本营——武汉。你说他是脑袋一热也行,反正那年头“投戎革命”风起云涌。他就考进了中央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也就是当年的黄埔“五期”。看似是去了军校,但他骨子里的文人气没忘,枪林弹雨里,也偷偷书写自己的所见所感。
没过多久,局势又乱了。讨伐夏斗寅、战火纷飞,大革命失败——这一波惨烈,臧克家卷着家里人一路逃往东北。你说他这个地主娃能不能吃苦?真的能。他在那里边咳嗽边奔波,边写诗边流亡。别人家小孩儿吹空调,他背井离乡。咱们看历史人物,文字里是风雨飘摇,实际人生,也是心酸泪下。
1929年,身体垮了,他回了山东养病,却没躺平。听说青岛大学招生,他琢磨着再试试,说不定能有条出路。那一年他已经一把年纪(相较于其他考生),一边补习、看书,还得担心家中老小。别说,他那会儿最怕的就是数学——这辈子都没搞懂的数学。
结果到了考试那天,盯着眼前的数学题,他脑子一片空白。做数学题时,可能想起家里的账本、逃荒的日子、过去读的诗,却就是做不出,最后只能交了空卷。按常理,这关他铁定完了。“但凡有一点别的特长也不至于如此”,大多数人碰到这种事,就是一个“认命”。可语文还有一场,作文题目倒是他拿手的那类——做人、生活的“杂感”。
他写了什么?全篇只二十八个字,三句话。简短得好像随手一写,偏偏又点到了人心里最哲学的焦灼:“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换个人,这怕是要被老师骂敷衍,但闻一多拼命为他撑腰。闻先生批卷向来不客气,能给十几分算高了,臧克家这个“零分哥”倒拿了九十八分,简直离谱。
闻一多说不上哪里被打动,是不是想起自己当年靠文采闯关清华门,也有那点“天才相惜”的气味?总之,这一锤定音,臧克家成了青岛大学别样的“幸运儿”。
其实进了大学,臧克家也没走多顺。他本来报了外文系,想着学点稀奇技能,可背英语单词死活记不住。看见外文课表头大,和一群同学一样,大家一窝蜂冲去中文系主任闻一多那“走后门”。别人都被闻先生一口拒掉,他本来都要灰溜溜撤了,闻一多居然点名“你留下”。谁说命运不眷顾有灵气的人?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那点缘分,是说不得的。
从此以后,他常常泡在闻一多的办公室,和先生聊诗说事,师生之间倒像朋友。大学的青岛,美则美矣,却也让他“喘不上气”——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大街上满是外国军舰、殖民势力耀武扬威,工厂的劳苦大众哀声不绝。他多年后提这段经历,总说像少女被污辱,美而哀伤。
也就在这个心情憋闷的季节,他自己花六十块(朋友和老师都支持,凑起来才出的),把诗集《烙印》印出来了。书名取的沉重,里面都是劳苦大众的故事:农民、老马、拉车的、工人、婢女……这些形象,你看着不像文学,倒像街上真实遇到的人。书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名声一下子打开。老舍、矛盾、韩侍桁……那时的文坛大人物,都说他是农民诗人——有血有肉,和风雨里的中国融在一起。
其实想想,臧克家的感情,有种烈火烹油的苦情。他从乡村长出来,心里一直惦记“泥土的味道”。他和穷孩子一起疯、一起玩,没什么富贵距离。他写诗,不是摆造型,是发自内心——控诉剥削,渴望新生。他多次写到:“啥时候我才能别再为这些人悲伤,而是真真正正唱首快乐的歌?”
风暴又来。1937年,卢沟桥事件一响,民族危亡。臧克家这个文弱书生,把“文艺青年”的身份甩到一边,直接投奔抗日事业,一边写作一边上前线。他写诗声嘶力竭:“抗战!抗战!诗人也得张开嗓子!不给人家打气你还写什么?”
他真的上了阵地采访,冒着枪林弹雨写出《津浦北线血战记》。这才是文人的另一种担当:不是在书斋里“发牢骚”,而是和士兵们一起站在血与火的最前沿。他说自己是“农民诗人”,又在烽火中成了“人民诗人”。
战争的五年,他在部队里扑腾着,满脑子是民族生死,有时脸是黑的、手是脏的,但诗句里是热的。抗战胜利那年,每个人对未来都怀了点好心思。可形势很快又变了——国民党闹“反共”那一套,臧克家一年四季嗓子都像被掐住。他渴望新中国,新生活,因而激愤地写诗,甚至一度被迫远走香港。
云黑风高也好,风平浪静也罢,终归天亮。1949年春,他重新闯回北平,在《新华日报》上一首诗热烈抒发对新生活的向往。艾青、郭沫若、臧克家……新时代的文人们,终于有地方可以痛快歌唱。
后来,他以主编、名作家的身份,和毛主席讨论诗词,谈雪、谈“骏马”,甚至帮主席修改《咏雪》里的字。这一幕,想来也有趣——革命家和诗人坐在一起“挑字眼”,将大风大浪归于平常嬉笑。
到了老年,臧克家依旧没停笔。出版社要他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他爽快答应,说“其他事可以不做,这件事我愿意干。”直到98岁悄然归西,这个零分考生,用一生证明了,有些人的生命轨迹,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你说是宿命,是天分,是倔强的心气?
可我们常说,“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也许正因为那点幻光,他不肯认输,一直用诗歌和世界对话。到头来,谁又能说这种人生,不值呢?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