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写作《有趣的一天日记300字》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06 20: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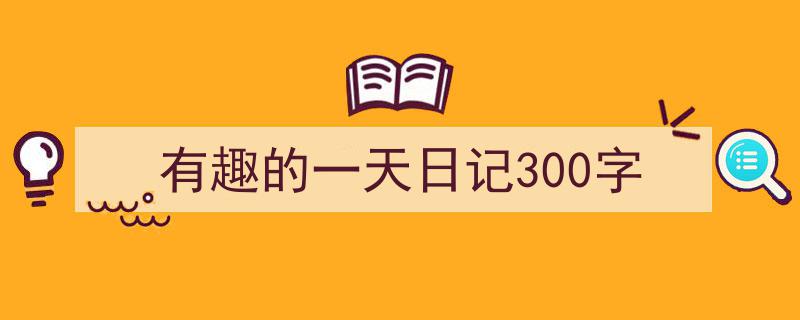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以下是一篇关于有趣的一天日记,大约300字,并附带写作注意事项:
"2023年10月26日 星期四 晴"
今天真是令人难忘的一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然而,在上学路上,我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小猫。它看起来非常虚弱,孤零零地坐在路边。我立刻心生怜悯,决定把它带回家。我小心翼翼地抱起小猫,匆匆赶往学校。
到了学校,我把小猫放在教室的角落里,然后开始上课。上课期间,小猫时不时地发出几声微弱的叫声,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下课后,同学们都围过来想看看这只可爱的小猫。老师也知道了这件事,她决定帮我把小猫送到动物救助站。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不仅帮助了一只小动物,还让同学们感受到了关爱和温暖。
放学后,我去了动物救助站。工作人员告诉我,小猫已经得到了妥善的照顾,并且很快就会找到一个新家。我松了一口气,心里充满了喜悦。今天真是充满意义的一天,我学到了关爱动物的重要性,也感受到了帮助他人的快乐。
"写作注意事项:"
"日期和天气:" 在日记的开头写上日期和天气,可以营造氛围,也为读者提供背景信息。 "具体事件:" 描述今天发生的有趣的事情,要具体、生动,可以使用一些细节描写,例如人物的
农民工安三山:《我的母亲》和一场突如其来的“看见”
在安三山的世界里,1000元很具体:在逼近40℃的日头天站三天,搬2万块砖,铲好几吨重的沙子和水泥。
所以,当听到坐在空调房里,写一篇作文就可以拿到这个数时,他没有丝毫犹豫,“一辈子都没碰到过这种好事。”
这是一个博主发起的街头挑战,安三山不懂这些,只觉得划算。不到一个半小时,他就写好了那篇800多字的作文《我的母亲》,握着千元现金满意离开。那时,他完全没想过故事的后续——作文被传到网上,“看哭了”无数网友,一夜之间抖音、快手上全是他,还上了大大小小的新闻媒体。
那句“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断不了”被反复品读,有人建议把作文纳入中小学课本。网上冒出不少素未谋面的“儿女”,逐字拆解他的写作技巧。也有人一本正经地分析,试图证明作文不是他写的。
安三山不玩网络,对这些反应迟钝。后来作文登上了报纸,村里不识字的老农都听孩子念过。一拨又一拨的人登门拜访,有大老板,也有出版社的编辑。他不知如何应对,只能不断重复:“我就是个农民。”
与网络上的热闹相比,太原火车站对面的马路沿上要安静得多。之前和安三山一起趴活的工友们,仍然会天不亮就聚集在此。提到安三山,他们才意识到,有几天没见到那个“不爱说话的小老头”。在这里,最近火遍全网的事实,就像发生在另一个时空,工友们大多没有听说过。
“啥?他还能写作文?”一位工友先瞪大眼睛,又撇了撇嘴说。
他们也没空琢磨。挑人的工头要来了,这是决定一天生计着落的关键时刻。没人在意,安三山正在以一种大家从未想过的方式,被外界“看见”。
土墙
从太原一路向西,经杜儿坪进入西山,车子转过几个陡峭的发卡弯,再向上不断爬升到山顶附近,安三山家就到了。
原本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安三山每次都要用将近一天。带上干粮从太原火车站出发,倒两趟公交车后,再在半道拦上山的顺路车,这样全程只花两块钱。
安三山家在村子东南角。在成排的砖墙和铁门里,只有安家的院墙由泥巴和石块垒成,木棍绑在一起就是门。透过木棍间能塞进西瓜的缝隙,院内一览无余:三分地里种着西红柿、豆角和茄子。半米高的台阶上,是一新一旧两栋平房。
平日,除了鸡鸣鹅叫,村里人最常听到的,是三轮车偶尔驶过路面的摩擦声。但一个月前,这条柏油路两边停满了车,一度堵得“迈不开腿”,全是来看“作文大爷”的。村里院墙下拉呱的老汉见到外人,不等对方张口,就朝着安三山家指去。
安三山住在太原西山靠近山顶的一个村子,旅游公路穿村而过。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
那几天,安三山小院里外挤满了人,家里杯子不够,罐头瓶都临时派上了用场。围观者举着手机,拉近焦距,试图在他身上找到一些独特之处,但大多失望而归——安三山太普通了,甚至有些不起眼。
他不高,身材精瘦,长一截的大号T恤让他显得更加瘦小;他也不像视频里那样白,皮肤黑黄,脸上皱纹就像西北的山,沟壑分明;那双写出《我的母亲》的手也和别的农民工没什么两样,指节粗大,因为被砸伤太多次,一根小指朝外翻着。他掌心的茧子厚,能拿得住装满开水的罐头瓶。
如果非要在他身上找出不同,迷彩裤下那双黑得锃亮、样式过时的皮鞋算是一个。安三山每天都闲不住,但这双鞋显然不适合劳动。
坐在镜头前,安三山咧嘴一笑,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齿,然后用方言一板一眼地自我介绍。他不是个健谈的人,提问在沉默和简单的中交替进行。关于作文是怎么构思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欣然作答。也有令他不快的“题外话”,母亲怎么去世的,埋在哪,家里人都是做什么的,他沉默以对。
来访者很快发现,安三山不是那种在镜头前事事配合的老汉。他谨慎地表达,带着很强的边界感。外人“在村里到处问”的做法让他生厌,“我家的事就问我不行吗?”
事实上,几乎每个到访者都曾被他拒绝过,他不断强调农民的本分,把自己与外界隔绝,“不想风风火火。”但不请自来者出现在他家门口时,也会受到客气对待。就像家里那扇门,他的世界也留有缝隙。作文火了之后,他总让儿子帮忙点开抖音的评论区,戴着老花镜一条条翻阅。
安三山声称专看“不好的”,但质疑、猜测的留言又会让他窝火。他不喜欢评论里夸他“像作家”的说法,那些评价《我的母亲》文字干净、情感真挚倒是能让他微微点头。
他抓起个儿子不要的本本,打算专门抄评论,并在扉页上记下了第一条:“知识分子的知识,应该用于理解和帮助,而非揣测和计算。”右下角,是评论者的昵称。
也有来访者说,他戴上老花镜时,像个知识分子。安三山对此反应激烈,仿佛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羞耻。
那个最常听到的问题也令他恼火:有没有想过,通过读书和写作改善生活?
“那是瞎想、幻想、白日梦。”他眉间的川字纹拧在一起,“不吃苦,不受罪,还能改善生活了?”
沉默
在太原火车站对面马路边的日结工里,安三山几乎是最能吃苦的一个。
对他来说,生活从来都是一道必须精打细算的算术题。三百块,是他给自己定下的日薪目标,意味着要抢最苦最累的活儿。
他做小工,给砌墙的大工递砖和灰(水泥)。干这活儿要快,保证脚手架上不能断料。脚手架比他高一头,每次发力脚尖要紧绷撑地。这活儿给年轻后生干,都要吃不消。砌墙的砖要提前洒水,一块三斤重,干一会儿汗就啪啪往下滴。一天下来,人累得躺在床上翻不了身。
他清楚,只有这个活儿,才能让他在支付完10块的床铺费、8块的饭钱后,有更多结余。这些收入是通往另一个目标的唯一路径:三个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
这笔堪称庞大的支出,像一道缰绳,把他拴在这片尘土飞扬的劳务市场。它解释了安三山所有的选择:为什么只点土豆丝盖饭,为什么把没开封的矿泉水攒起来卖回给小店。为什么干完300块的活儿,如果第二天能爬起来,他还想再干一天三百的。在他的人生算式里,任何无法快速折现的事物,都是多余的。
每天四五点钟,太原火车站对面的劳务市场挤满务工者,交谈着当天哪里有活儿可干。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
就像在10块钱一晚的地下室里,潮湿阴冷,空气里混着体味、烟味和霉味。老板偶尔查房,曾撞见过他不一样的时刻——“他开门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本一指厚的书看。”但那画面短暂得像幻觉。
作文火了后,很多人说他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安三山也在下雨天没法出工时,到新华书店看过这部小说,但只是翻翻,“没看几页,因为没时间。”
他不是没有过别的可能。1978年,他是郑家庄村少数能念到高中的年轻人。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毕业时他和同学抱头痛哭,一起唱歌、在山坡上合影,徒步到县城的公园游玩。后来,他离大学差了二十分。校长和老师不止一次挽留他任教,他都因为家里缺劳动力,还有薪水微薄拒绝。
录取通知书没等来,却等来了征兵的消息。他顺利通过体检,分到了青海天峻县的铁道兵部队。在连队,他仍然是“高材生”。1981年,义务兵役将满,他又一次被挽留。但他再次选择了离开——听说“复员回地方好找工作”。
次年,他终于得偿所愿,到古交的一个机械化砖厂当工人。他干的是唯一要上手的活儿——出砖,把滚烫的红砖从轨道车上卸下,每天干9个小时。
原本他一直干下去,如今早已是退休工人的身份,但没过几年他就生了场大病,卧床两年,命运再次转向。身体康复了,他也被彻底钉回了农民原本的身份。那条想象中的、通往“公家人”的狭窄通道,在他眼前彻底关闭了。
“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后悔也不顶用。”他后来说起这些,脸上没什么表情。希望破灭之后,成了他嘴里的“瞎想”。
他没能成为孙少平,半辈子的经历早让他学会了认命,对待世界,他回以深深的沉默。
那些被压瘪的表达欲,也挣扎过,只是都悄无声息地败下阵来。病倒的两年,身体被困在炕上,他翻来覆去地看那几本仅有的书,在一个笔记本上,抄下能触动他的字句。偶尔精神好时,写写日记。“我认为语言的能力超越一切,它胜过了金钱、力气、权力,这一切一切都需要语言穿过。”“星星向往月亮,我在寻觅知音。”笔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
但生存的力气回来时,这点精神上的喘息就显得多余。那本日记,连同那段试图与自己对话的脆弱时光,迅速显得“不切实际”。
上个月,或者更早,他记不清了,在又一次整理少得可怜的家当时,他把日记本和一堆旧报纸、废纸壳一起卖了废品。“不是要紧的事情。”他这样定义它。过秤,算钱,几元而已。当年看过的书,如今“糊了窗户和柜子”,那是它仅剩的价值。
没有仪式,甚至没有一丝波澜,就像随手掸掉身上的一粒灰尘。他卖掉的,是一部分无用的、过于沉重的自己。他不再是那个病中抄诗的年轻人,只是太原火车站路边,一个等着一天300块活计的老汉。
作文火了后,一位北京的出版社编辑前来拜访。几杯热茶下肚,对方向他提出一个概念:“在农村,能识文断字,有一些文化和见识往往会被称为知识分子。但如果自己没有挣大钱的能力,还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那他们就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甚至在农村,在家族里都没什么地位。他们内心总是不被理解的,向内求,与自己达成和解,理解并原谅这个世界,是他们生存的一个重要选择。”
“这段话形容你,合适吗?”对方试探性地问。
安三山点头回应。
母亲
大部分时候,安三山的表达,只存在于他那用土墙筑成的堡垒里。
他喜欢给家里的各种物件题字。房前架电线和自来水管的木棍上,贴着毛笔字写的“生活之源”。原本那是“生命之源”,他斟酌后,觉得“生活的内涵比生命更大”,于是换掉。
水井的挡盖上曾写过“井水长流”“井泉长流”,但都不如现在的“细水长流”,“细水长流不仅形容水,也形容生活嘛。”
有时他坐在台阶上,飞机从头顶划过,家在山顶他能看清飞机的颜色。他琢磨着,坐在飞机里的都是什么人呢,它是从哪飞来,又要飞去哪里啊。
他喜欢留意细节,有时大清早会突然指着院子里的一株草,让孩子用手机搜搜,然后记下名字。
“用心记在脑子里。”被问到是不是有随手记的习惯,他摆摆手,“哪还能经常拿个本?那就不是劳动人民了。还用拿笔?那成了啥了。”
安三山家的老屋,墙上贴着他写的毛笔字。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
直到6月29日这天,因为无法拒绝的1000元,他才在家之外的地方拿起了本和笔,那些埋在心底的柔软细节,终于找到了出口。
那是一场巧遇。前一天,他干了回300块的活儿,晚上睡得很差,“那天活太重,把人干翻了。”
次日他一睁眼,已经五点四十。平常这时候,他早就吃完早餐,坐上去工地的车了,根本见不着那两个女孩。
她们正在做一个街头挑战:路人可以选择直接拿走100元,或者尝试写一篇作文赢取1000元。前面四五个工友都选了100元现金,安三山没作声,他另有打算。
“我念过高中,有高中毕业证书。”他凑上前告诉女孩,决定“挑战一下”。
纸盒子递到眼前,他伸手在一堆折叠的纸条里摸索,捻出一张,展开——“我的母亲”。
视频里,拿到这个题目时,这个66岁老人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波动,但他在作文开头写下:“重温母亲的回忆,我思绪万千。”
写作在附近的一家空无一人的餐馆里进行,女孩为他准备了一杯冷饮,奉上纸笔。安三山从随身带的红布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没有搭框架,也没有打草稿,文字像是从笔尖流淌出来一样。
某种程度上,母亲从未真正离开。
他写“天不亮就起,摸着黑才歇”的母亲,写她洗得发白、补丁叠着补丁的衣裳。太原火车站对面的劳务市场上,他也是每天去得最早的那个,工友记得这个“一年四季都在穿劳保迷彩服”的老头,袖口已经磨破开线,但领子总是干净整洁的。
他写家里“那口烧柴火的大铁锅,死沉死沉”,但母亲瘦小的身子总能稳稳端起来。有那么一两次,他在工地上累得抬不起砖时,母亲抬大铁锅的身影真的就出现在眼前,他咬紧牙,又挤出些力气——母亲教会了他“骨子里的硬气和对家的担当”,“我得把您撑起来的这个家,接着撑下去,撑稳当。”
他写母亲“心善,能容人,跟邻里没红过脸。”在工地,安三山因为个子矮,被工友叫“武大郎”,但他总是笑笑。给大工铲水泥时,他总会留意不要溅到别人身上。
母亲曾是他最大的依靠。8个孩子里,只有他和二哥上学,一个铅笔掰成两半用。家里供不起后,母亲做主让二哥回家,他回到了学校。
六一时,母亲借钱买来白布,踩一整夜缝纫机为他赶制白衬衫。晚上,他点着煤油灯看书,两个鼻孔熏成黑色,睡醒后,母亲已经为他擦去。米少得只能熬汤时,母亲总会悄悄给他留一碗稠的。
生病的那两年,母亲整天围在床前照顾他,给他包最香的饺子,搀着他在院子里散心。自己病好了,母亲却累倒。母亲50岁出头就走了,留给了他这辈子最难以释怀的遗憾。
“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断不了。”他写下这句最为人传诵的文字。
文章最后,“母亲”换成了“妈妈”,这个压在心底30多年的称呼,终于冲破了沉默。
作文完成,安三山收起现金,抓起他的红布袋,简单答谢后离开餐厅。他快步走向街头,汇入人群,又成了一个只擅长体力活儿的农民工。
最后的缝隙
作文写好后两周,博主把视频传到网上,瞬间炸开。到8月30日,已经有超过900万次点赞、30多万评论。
安三山得到的,除了那实实在在的1000块,从附近市场买了十几斤猪肉带回家,还有受媒体的生平第一次去了北京,似乎再没有别的。
有人建议他开直播,继续写文章。他说:“我就是个受苦人。”他用大衣哥举例子:“被人家在村里又围又堵又弄,那叫生活了?我宁愿不要那个钱财。”妻子也有顾虑,见到有人拍照就阻拦:“不要拍。要是发出去,我儿子以后怎么娶媳妇。”
网络上的热闹渐渐平息后,他脱下那件大号T恤和皮鞋,又换上迷彩服,还有儿子穿剩下来的球鞋。早晨五点,他站在院子里打量老屋的墙面,开始和水泥。
他从那栋旧房子进进出出,和儿子往外搬杂物。出汗了,他就敞开怀,肋骨在皮肤下清晰显现。干瘪的肚皮下面,一条红绳穿过裤子,权当腰带。
修整老房子的想法早就有了。他想给墙抹层灰,装个吊顶,地面铺上水泥。这样等亲戚来时,家里也有住的地方。“房子是人的头脸”,他受了大半辈子苦,也想证明自己“算是活出来了”。
如今,两个女儿找了工作,小儿子课余时兼职,能自己还助学贷。经济压力稍减,他立刻行动起来。
在儿子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催家人“快点”,赶着工期,追着生活的节奏。此刻的安三山却细致地打磨着墙面,这次儿子当小工,他当大工。墙抹得不顺利,灰浆一直往下掉。一天下来,只完成了几平方米。
安三山坐在角落抽烟,“不服气。”他看别人干过无数次,真自己上手,却“干得自己都看不过去”。
他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墙要修得平整,说话要恰当,形象要干净。更重要的是农民要守本分,劳动是美德,沉默是金。
在这个院子里,子女也继承了他的沉默。面对来者的提问,他们总会瞥向父亲,客气地摆手婉拒。
大部分时间,院子里只有安三山劈砖发出的声响。老房年久失修,墙上出现十多个缺口,抹灰前,要先用砖补平。他举起斧子把砖敲打成想要的形状,塞进缝隙。
最后一块砖补完时,裂口消失在灰浆与砖石中,墙面完整如初,再难窥见内里。
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编辑 杨海
校对 刘军
幸福不在远方:那些被我们捧在手心的日常才是真福田
深夜加完班回家,看见母亲留的夜宵还冒着热气;孩子把99分的试卷藏在背后,眼睛笑得弯成月牙;伴侣边抱怨你乱扔袜子边帮你把拖鞋摆正——这些瞬间你留意到了吗?我们总在追寻所谓的"更大幸福",却不知真正的福气往往藏在最平凡的日常里。
寻常日子里的不寻常馈赠
有位智者曾说:"父母不躺在医院,孩子身心健康,夫妻携手到老,钱包虽不鼓却够用,这已是天大的福分。"细想确是如此,我们习以为常的平静生活,其实是命运的珍贵礼物。当别人在为父母的医药费四处筹款时,你的母亲还能在电话里叮嘱"记得吃早饭";当同龄人在儿童医院彻夜难眠时,你的孩子正在操场欢快地奔跑。
钱不必多到令人艳羡,够用就好。能够不为明天的面包发愁,不为下月的房租焦虑,这样的从容已是难得的幸运。菜市场里新鲜的蔬菜,阳台上晒得蓬松的棉被,晚饭后全家人围坐的闲聊,这些看似普通的画面,构成了生活最扎实的幸福底片。有位作家说得好:"我们总是仰望别人的幸福,却不知道自己也被别人仰望着。"
向内探寻的精神桃花源
物质满足只是幸福的冰山一角,真正的丰盈来自内心的修炼。清晨五点晨读时与古人的神交,静坐冥想时感知到的身体韵律,背诵经典时体会到的语言魅力——这些精神体验带来的愉悦远胜于物质的堆砌。当我们与《道德经》对话,在游泳时感受水流的拥抱,或是写作时理清思绪的脉络,心灵便悄然生长出坚韧的根系。
有位每天写作的实践者发现,三百字的小作文不仅训练了逻辑思维,更培养了对生活的敏锐感知。这种通过持续精进获得的成长喜悦,是任何奢侈品都无法比拟的幸福。正如禅宗所言:"饥来吃饭,困来眠",回归本真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修行。
幸福的三重境界
幸福首先是当下的感知力。能为一杯热茶感动,能为路边野花驻足,这样的敏锐让普通日子熠熠生辉。有位每天记录"小确幸"的女士说,坚持三年后,她发现不是幸福变多了,而是自己变得更会发现了。
其次是持续的生活状态。幸福不是偶尔的惊喜,而是稳定的心境。就像那位每周游泳两次的坚持者所说,在水中漂浮时的自在感,让身心获得深层的放松与平衡。这种通过规律习惯培养的内在稳定感,才是抵挡生活风雨的基石。
最高境界或许是自我实现的满足。当我们在陪伴82岁母亲时体会到的亲情温暖,在背诵经典时感受到的文化传承,这些连接着更大意义的体验,让生命有了深度和重量。一位哲学家说得好:"幸福不是目的,而是高质量生活的自然产物。"
下次当你抱怨生活平淡时,请想想:此刻有多少人正羡慕着你拥有的"平淡"。父母的唠叨,孩子的嬉闹,伴侣的叮咛,这些看似简单的画面,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奢侈。真正的幸福从来不在远方的山顶,而在我们捧了一路却未曾留意的怀中烛光。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