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风波读书笔记300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08 0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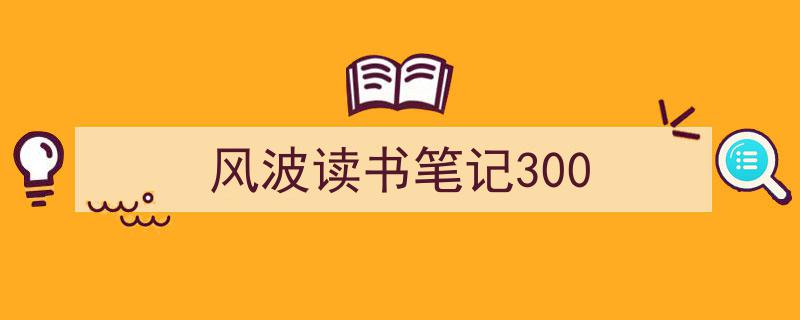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以下是一篇关于风波读书笔记 300 字作文应该注意哪些事项的文章:
"风波读书笔记 300 字作文注意事项"
《风波》是鲁迅先生的一篇短篇小说,通过描写一场因辫子而引发的风波,深刻揭露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愚昧和落后。写一篇 300 字的读书笔记,需要抓住文章的重点,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简要概述故事情节。" 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小说的主要内容,包括人物、事件、起因、经过和结果。例如,可以写:小说围绕胡传贵儿子的辫子被剪展开,描写了未庄人们对此的不同反应,以及最终风波平息的过程。
"2. 分析人物形象。" 选择一到两个主要人物进行分析,例如赵太爷、假洋鬼子等。可以从他们的语言、动作、神态等方面入手,分析他们的性格特点,以及他们在风波中所起的作用。例如,赵太爷代表着封建势力的残余,假洋鬼子则代表着投机分子。
"3. 阐述主题思想。" 《风波》的主题思想是揭露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中国农村的愚昧和落后。在笔记中,要结合具体事例,谈谈你对这个主题的理解。例如,可以写:辫子风波反映了人们对辛亥革命的意义认识不清,也说明封建思想根深蒂固。
"4. 注意语言简洁。" 300 字
【俄】契诃夫: 风波
玛申卡·帕夫列茨卡娅是个非常年轻的姑娘,刚刚在贵族女子中学毕业,这一天她在外面散步后,回到库什金家,她是在那儿做家庭教师的。不料她正碰上一场非同小可的风波。给她开门的看门人米哈伊洛神情激动,脸红得跟大虾一样。
楼上传来一片嘈杂声。
“多半是女主人发病了……”玛申卡暗想,“要不然就是她跟丈夫吵架……”
她在前厅和过道里都遇见了使女。有个使女在哭。随后玛申卡瞧见从她自己的房间里跑出一个人来,正是男主人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他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年纪还不算老,脸上却已经皮肉松弛,头顶秃了一大块。他脸色通红,浑身发抖……他没看见这个女家庭教师,径自从她身旁走过去,举起双手,叫道:
“啊,糟透了!多么鲁莽!多么愚蠢,野蛮!太可恶了!”
玛申卡走进她的房间,在这儿,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极其尖锐地体验到凡是寄人篱下、听人摆布、靠富贵人家的面包过活的人所熟悉的那种心情。原来她的房间正遭到搜查。女主人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在她桌子旁边站着,把她的毛线球、布块、纸片……放回她的针线袋里。那女人是个体态丰满、肩膀很宽的太太,没戴头巾,生着两道乌黑的浓眉,颧骨突出,嘴唇上生着隐约可见的唇髭。她那两只通红的手、她那张脸和她那姿态,都像是一个普通的村妇和厨娘……女家庭教师的出现分明出乎她的意外,因为她回头一看,见到女家庭教师苍白而惊讶的脸容,就有点慌了手脚,支支吾吾地说:
“Pardon。我……无意中弄撒了这些东西……是我的袖子碰翻的……”
库什金娜太太又说了几句别的话,就把她的长衣裙弄得沙沙地响,走出去了。玛申卡用惊愕的眼睛扫一眼她的房间,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该怎样想才好,只是耸起肩膀,害怕得浑身发凉……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在她的袋子里找什么呢?如果确实像她说的那样,她是一不小心让衣袖碰翻了袋子,把东西弄撒的,那么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为什么从她房间里跑出去,脸那么红,神情那么激动呢?为什么书桌上的一个抽屉略微拉开了一点?女家庭教师有个贮钱盒,原是用来收藏十戈比银币和旧邮票的,现在却打开了。人家把它打开后,虽然想关上,而且把锁抓得满是指痕,却还是关不上。书架、桌面、床铺都带着新搜查过的痕迹。装内衣的筐子也是如此。本来那些内衣叠得整整齐齐,然而现在却不像玛申卡出门的时候那么井然有序了。可见这次搜查是认真的,极其认真的,然而这是什么意思,什么缘故呢?出了什么事呢?玛申卡回想看门人的激动,回想目前还在延续的纷乱,回想泪痕斑斑的使女,莫非这一切都同刚才在她房间里进行的搜查有关?莫非她牵连到一件可怕的事情里去了?玛申卡脸色煞白,周身发凉,身不由己地往那个装内衣的筐子上坐下。
有个使女走进房间来。
“丽莎,您知道他们为什么……搜查我的东西吗?”女家庭教师问她说。
“太太丢了一个值两千卢布的胸针……”丽莎说。
“哦,可是为什么搜查我呢?”
“他们,小姐,把所有的人都搜查遍了。我的东西也统统搜查过……他们把我们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搜我们……上帝作证,小姐,我……从来也没有到她的梳妆台跟前去过,更别说拿她的胸针了。就是到了警察局我也要这么说。”
“可是……为什么要搜我的东西呢?”女家庭教师仍然大惑不解。
“我跟您说过,有个胸针让人偷去了……太太亲手把所有的东西都翻遍。就连看门人米哈伊洛她都搜过。简直是丢脸!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光是瞧着,呱呱地叫一通,就跟母鸡似的。不过您,小姐,用不着这么发抖。在您这儿什么也没找着!要是您没拿那个胸针,就用不着害怕。”
“可是要知道,丽莎,这是卑鄙……欺负人,”玛申卡说,愤懑得上气不接下气,“要知道这是下流,卑鄙!她有什么权利怀疑我,翻我的东西?”
“您是住在别人家里,小姐,”丽莎叹道,“虽然您是位小姐,不过也还是……跟仆人差不多……这跟在爹娘家里住着可不一样……”
玛申卡扑在床上,伤心地放声痛哭。她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的迫害,也从来没有受过像现在这样深重的侮辱……她是个有良好教养而且敏感的姑娘,又是教师的女儿,可是现在人家居然怀疑她偷东西,搜查她,把她当做街头女人一样!比这再厉害的侮辱似乎都没法想象了。而且除了这种受屈的感觉以外,还有沉重的恐惧:今后还会怎样?!种种荒谬的想法钻进她的头脑里。既然人家能够怀疑她偷东西,那他们现在也可能拘禁她,把她的衣服脱光,把她里里外外搜查一番,然后派人押着她走过大街,把她关进又黑又冷而且满是耗子和甲虫的牢房里,就跟幽禁塔拉卡诺娃郡主的牢房一样。谁会来给她做主呢?她父母住在遥远的外省,他们没有钱乘火车到她这儿来。她在这个京城孤身一人,就跟住在荒野上似的,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人家要怎样处置她就能怎样处置她。
“我要跑到所有的法官和辩护人那儿去……”玛申卡想,不住地发抖,“我要向他们解释清楚,我要起誓……他们会相信我不可能是贼!”
玛申卡想起她衣筐里被单底下放着一些甜食,这是她按照在贵族女子中学里养成的老习惯,吃饭时候藏在衣袋里,带回自己房间里来的。她想到她这个小小的秘密已经被女主人识破,就不由得周身发热,害臊起来。由于这一切,由于恐惧和羞臊,由于受屈,她的心猛烈地跳起来,弄得她的两鬓、双手、肚子深处也猛烈地跳动不已。
“请您去吃饭!”仆人来请玛申卡。
“去不去呢?”她想。
玛申卡整理一下头发,用湿手巾擦一把脸,走进饭厅。那儿已经开始吃饭……饭桌的一头坐着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大模大样,脸容死板而严肃。饭桌的另一头坐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饭桌两旁坐着客人和孩子们。伺候吃饭的是两个听差,身穿礼服,手上戴着白手套。大家都知道这个家庭起了风波,都知道女主人闷闷不乐,就都沉默不语。只有嚼东西的声音和汤匙碰响盆子的声音。
谈话是由女主人自己开的头。
“我们的第三道菜是什么?”她用懒洋洋的痛苦声调问听差说。
“De l’esturgeon à la russe,”听差说。
“这道菜是我点的,费尼娅……”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赶紧说,“我想吃鱼。要是你,ma chère,不喜欢吃,那就叫他们不用端上来了。反正我也是随便点的……一时高兴罢了……”
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不喜欢吃不是由她本人点的菜,这时候眼睛里就含满了泪水。
“得了,您不要激动,”她的家庭医师马米科夫用甜蜜蜜的声调说,轻轻碰一下她的手,而且同样甜蜜蜜地微笑着,“就是没有这件事,我们也已经够烦恼的了。我们忘掉那个胸针吧!健康总比两千卢布贵重!”
“我倒不是心疼那两千卢布!”女主人说,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流下来,“惹我气愤的是这件事本身!我不能容忍我家里有贼。钱我倒不心疼,一点也不心疼,可是偷我的东西,未免太忘恩负义!我待人好心好意,人家却这么报答我……”
人人都瞧着自己的菜碟,然而玛申卡却觉得女主人说完那些话后,大家似乎都瞧着她。她忽然觉得喉头堵得慌,就哭起来,用手绢蒙上脸。
“Pardon,”她喃喃地说,“我受不住了。我头痛。我要走了。”
她从桌旁站起来,笨手笨脚地碰响自己的椅子,越发心慌意乱,赶紧走出去了。
“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忍不住说,皱起眉头,“何必去搜查她的房间!这件事,真的,……办得多么不得当。”
“我并没有说她拿了那个胸针,”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说,“不过你能替她担保吗?我,老实说,对这些念过书的穷人是不大相信的。”
“真的,费尼娅,这件事不得当……对不起,费尼娅,根据法律,你没有任何权利进行搜查。”
“我不懂你们那些法律。我只知道我的胸针丢了,就是这么的。而且我要把那个胸针找到!”她说着,把叉子的一响摔在她的菜碟上,气愤得两眼放光,“您吃您的饭,不要管我的事!”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顺从地低下眼睛,叹口气。这时候玛申卡已经回到她的房间里,扑在床上了。现在她已经不再感到恐惧,也不再觉得羞臊,只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折磨着她,就是恨不得走到那边去,给那个冷酷、傲慢、愚蠢、有福的女人一个清脆的耳光才好。
她躺在床上,鼻子对着枕头呼吸,幻想着如果现在她能出去买来一个最贵重的胸针,朝着那个任性胡为的女人脸上扔过去,那才痛快呢。只求上帝大显神通,叫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倾家荡产,沿街乞讨,领略一下贫困和不能自主的地位的种种惨痛,然后再让受了侮辱的玛申卡给她一点施舍才好。啊,但愿能得到一大笔遗产,买上一辆四轮马车,坐着它辘辘响地经过她的窗前,惹得她看着眼红才好!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幻想,在现实生活里她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赶快走掉,再也不在这儿多待一个钟头。不错,丢掉这个职位,又回到一贫如洗的父母身边去是可怕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玛申卡再也不愿意看见女主人,再也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小房间,她觉得这儿又气闷又可怕。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总爱谈她的病,总爱装出贵族的气派,简直着了魔,惹得玛申卡讨厌透了,似乎人间万物都因为有这个女人活着而变得粗俗可恶了。玛申卡跳下床来,动手收拾行李。
“可以进来吗?”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在门外问道。他悄悄地走到房门跟前,用轻柔的声调说,“可以吗?”
“请进。”
他走进来,在房门近旁站住。他的眼睛黯淡无光,小红鼻子发亮。饭后他喝了啤酒,这可以从他的步态和软弱无力的双手看出来。
“这是怎么了?”他指一指衣筐问道。
“我在收拾行李。对不起,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我不能再在您家里住下去了。这种搜查深深地侮辱了我!”
“我明白……只是您不该这样……何必呢?您遭到了搜查,可是您……那个……这于您有什么妨碍呢?您又不会因此吃什么亏。”
玛申卡没有说话,继续收拾行李。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捻着唇髭,仿佛在盘算还应该说些什么,然后用讨好的口气继续说:
“我,当然,是明白的,不过您应当体谅她才对。您知道,我的妻子脾气躁,任性,对她不能太认真……”
玛申卡一言不发。
“既是您感到这么委屈,”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继续说,“那好吧,我来向您道歉。请您原谅。”
玛申卡什么话也没,光是把腰弯得更低,凑近皮箱。这个形容憔悴、优柔寡断的人在这个家庭里丝毫也不起作用。他无异于一个可怜的食客和多余的人,甚至在仆人们眼里也是如此。他的道歉也是毫无意义的。
“嗯……您不说话?您觉得这还不够?既是这样,我就替我的妻子道歉。用我妻子的名义……我以贵族的身分承认,她办事鲁莽……”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走来走去,叹口气,继续说:
“这样看来,您还要我这儿,喏,我的心底里痛苦……您是要我的良心折磨我……”
“我知道,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这不能怪您,”玛申卡说,用沾着泪痕的大眼睛直直地瞧着他的脸,“您何必自寻烦恼呢?”
“当然……不过您还是……那个……不要走吧……我求求您。”
玛申卡否定地摇一下头。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在窗旁站住,用手指头轻叩着窗上的玻璃。
“对我来说,这类误会简直就是苦刑,”他费力地说,“怎么样,您要我在您面前跪下还是怎么的?您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于是您就哭着,准备走了,可是要知道,我也有自尊心啊,这您就不顾了。或者您是要我对您说出我在举行忏悔礼的时候也不愿说出口的话?您是要这样吗?您听着,您是要我说穿连我在临终忏悔的时候对神甫也不肯说穿的事吗?”
玛申卡没有答话。
“我妻子的胸针是我拿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很快地说,“现在您称心了吧?您满意了吧?对,就是我……拿的……不过,当然,我希望您保守秘密……看在上帝份上,您对外人一句话也别说,半点口风也不要漏出去!”
玛申卡又惊又怕,继续收拾行李。她抓住她的衣物,揉成一团,胡乱塞进皮箱和衣筐里。现在,经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坦率地说穿以后,她在这儿就连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甚至不明白以前她怎能在这个人家住下来。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这件事很平常!我缺钱用,她呢……不给。要知道,这所房子和这一切都是我父亲挣下的,玛丽亚·安德烈耶夫娜!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就连那个胸针也是我母亲的……全是我的!可是她都拿去了,霸占了一切东西……您会承认,我没法跟她打官司啊……我恳切地请求您,请您原谅,而且……而且留下来吧。Tout comprendre,tout pardonner。您肯留下来吗?”
“不!”玛申卡坚决地说,开始发抖,“请您躲开我,我求求您。”
“哎,求上帝跟您同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叹道,在皮箱旁边一个凳子上坐下,“我,老实说,喜欢那些还能有受侮辱、蔑视人等等感情的人。我情愿一辈子坐在这儿瞧着您愤慨的脸……这样说来,您不肯留下了?我明白……事情也不能不是这样……是啊,当然……您这样一走,倒挺自在,却苦了我,唉唉!……这个地牢我连一步也迈不出去。我原想到我们一个庄园上去,可是那儿也到处都是我妻子的爪牙……什么总管啦,农艺师啦,叫他们见鬼去吧。他们把田产抵押了又抵押……于是你就钓不得鱼,踩不得草,砍不得树。”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从大厅里传来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的说话声,“阿格尼娅,去把老爷叫来!”
“那么您不肯留下来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很快地问道,站起来,往门口走去,“其实您应该留下来,真的。每到傍晚我也好到您这儿来……谈一谈心。啊?您留下来吧!您一走,整个这所房子里就连一张人脸也看不到了。这岂不可怕!”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苍白而憔悴的脸上露出恳求的神情,可是玛申卡否定地摇一下头。他就挥一挥手,走出去了。
过了半个钟头,她已经上路了。
1886年
* * *
法语:对不起。
塔拉卡诺娃郡主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在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自称是故女皇伊丽莎白的女儿,后被捕,死在牢房里。俄国画家弗拉维茨基在一八六四年完成的画《塔拉卡诺娃公主》描绘了她被关在牢房里的情景。——俄文本编者注
法语:俄式鲫鱼。
费多西娅的爱称。
法语:我亲爱的。
女家庭教师的本名,玛申卡是爱称。
法语:了解一切就原谅一切。
陶洛诵:我知道的遇罗锦离婚风波
原题
遇罗锦给我的信
(上)
作者:陶洛诵
遇罗锦
在我心里,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可以和三十年代媲美的黄金时期。尽管当时在各个领域里逐鹿中原的勇士豪杰天生学养不足,但他们利用手中有限的资源,利用昙花一现的大好时机,向激进势力宣战,在中国社会被文革摧残到濒临绝境时打出一片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
作为一名亲临那段历史的过来人,愿意为有兴趣者提供仅知的史料,权作一斑窥豹。今天,我把遇罗锦给我的信再次发表。1986年这些信曾在香港《百姓》杂志发表。
编辑手记里这样写到:
遇罗锦在西德请求政治庇护,成为世界重要新闻,中共的反应相当理性,不如当年胡娜那么紧张了。以遇罗锦的家庭特别是他哥哥遇罗克的遭遇,她之要求政治庇护并非无理。我们特请在波恩的朋友,实地訪问了她,谈她在大陆创作的感受。同期,我们及时得到了一篇重要稿件,由遇罗锦的最好朋友陶洛诵执笔,记她与遇罗锦的结识与遇的为人,写得非常有感情。
因为原文较长,有些和我在微信公号“新三界”上发表的内容重复,在此不再赘述,挑选些大家没见过的打印出来,并加上一些解说,供有兴趣者参考。
遇罗克和妹妹遇罗锦
01
写作真的是每个生命的需要,我看到文章中的这段,百感交集,我对这场景没有丝毫记忆,但它肯定是真的:
数九寒冬,清晨,我被一阵敲门声叫起,开门一看,是两颊冻的通红的忠培。他伸出粗糙的手递给我一张电影票。
“罗锦请你今晚看电影。”
“请进来暖和暖和吧!”
“不啦,要不上班该迟到啦!”
我妈妈望着他的背影,说:“真不错,老婆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遇罗克全家照,1963年
02
我给幼年的儿子写下了十几万字的日记,这事多亏遇罗锦。这部沉甸甸的日记扉页上,是她情深意切的题词。以下是题词全文:
一九八零年二月三日,星期日,是你在托儿所放假的日子。我和你母亲正在谈着我那不知何年何月才发表的用生命写成的书。你玩累了,到你母亲怀里撒娇。你年轻的母亲心爱地抱起你、拍着、哼着,你甜甜地闭上了眼睛。
我们望着你那可爱的面庞,目光都不忍离去——那躺在柔软的棉被下,无力地抱着奶瓶子,吸着糖水的你呀。
“你给他记过日记吗?”我问道。
“还没有。”
“你应当给他记一本日记,一星期记一件事,一年还五十二件事呢!你记下他那有趣的言谈和行为,他长大了,看着自己小时候的忠实记录,多有意思!那时他才知道母亲的心血!如果社会能给他土壤,造就他成为人才,这将是一本珍贵的历史资料。你的孩子很有音乐天赋,从他那正直坦荡的可爱相貌中,从他父母的性格中,能看出他有浓厚的艺术气质。他会喜欢绘画,喜欢文学,但哪个也不如音乐更能成为他的天职。他的天赋是优厚的,他的思想感情会是丰富的,他胆大,虽然外表不明显,这就造成他敢于爱、敢于恨、敢于创造生活。加上父母要立志培养他,他一定会创作出比贝多芬更感人的乐章。他生活的时代,将不会是再因日记而定罪的时代。他生活的时代,将是中国大变革的时代。他的性格,会使他有生活的坎坷,所以他会更爱底层的穷苦人。他天生的充沛精力,会使他排除万难,所以他才会创作出气魄宏伟、悲壮的乐章。设想,如果我们现在发现了一本贝多芬儿时他母亲为他记的日记,全世界将会如何轰动震惊?那本日记将价值连城!可惜他母亲没有记。你记吧,记吧,他不会辜负这本日记的!
“罗锦......“你母亲激动地欠过身来,眼里迸射出感动和依赖的光芒,热诚地抓住我的手,从眼儿里说道:”谢谢你!“
下一个星期日前,她买了这个在全市所有日记本中价格最昂贵、最精致的本子,特意送到我家来,郑重地交给我,请我题词。
这就是我给你的题词,孩子。
遇罗锦
一九八零年二月八日
于北京
1987年6月,陶洛诵出国前和儿子告别
03
我儿子是个非常知恩图报的人,2016年,我和多年没联系的罗锦联系上了,他知道罗锦阿姨的日记题词在他生命中的积极作用,他让我罗锦来悉尼我家住一阵子,我转告了罗锦,罗锦没时间没来。
儿子是个理工男,IT工程师,为了给我和他妹妹一个好的生活,四十出头,至今未婚。我告诉他,萧蔚阿姨说他是钻石王老五,他说:“王老五是真的,钻石倒不是。”他勤奋好学幽默谦虚,孝顺之极。我说:“谁能嫁给你太福气了!”他说:“这倒是真的!”(是不是有征婚广告之嫌啊?)
这部日记的价值在于,我在记录儿子成长的同时,无意中记录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瞬间和参与创造这个伟大瞬间的我的出类拔萃的朋友。
1983年陶洛诵北京电视大学毕业证
04
一九八零年四月九日,我接到罗锦的一封信:
洛诵,我亲爱的朋友:
四月七日起,我彻底抛开了过去自欺欺人的生活的一切,有了我可爱的农民房,开始了新生活。
志国、忠培代表什么?代表爱情吗?幸福吗?真和美吗?不,虽然他们都是好人。忠培比志国更好,他俩只代表我那自欺欺人生活的一页......
过去,我没着谁惹谁,左帮们把我的户口、工作全剥夺了,又戴上反动的帽子。而今意外地又给了我独立生活的条件——让我尝尝一个人生活的清净滋味吧,我太想尝尝了!所以五日晚我极巧地找到一间十分理想又不贵的北房,七日晚我顶着濛濛春雨一路上唱着歌,便骑车飞奔到我的新居......
我是再也不会回去了,洛诵,虽然我和家里及忠培没有说的那样死,但我自知是再也不会回去了。我宁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也绝不想和并不爱的人一起凑合了。在可爱的肃静中,我感到生活可爱极了,再也没有杂音吵我了。
我请你见到我的信以后,晚上去看看忠培,开导开导他,不要让他想不开,我以为你的话他是肯听的。也希望你去我家里一次,(最近我不想回家)让我的父母不要给我捣乱,不要在忠培面前充好人,那样一点好处也没有。请把你父母的态度告诉我父母,让他们也得些启发。
你不要在他们面前露出是我叫你去的。好洛诵,再见!过些天有空我再看你。
望你常看看忠培。
实话大王 四.九
如果你认为这封信让我父母看看有好处,让他们看看也好,罗勉也可以看看。
房子离厂骑车只十分钟。只要左帮们不再搞政治运动,我就会一个人幸福地过到老。
遇罗锦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
05
我到德胜门外她工作的玩具六厂找到她。她拿出一本《新华文摘》,里面转载了她的处女作《一个冬天的童话》。她签了字送给我,有些抱歉地说:“《当代》杂志没有了,送你这个吧。”
“忠培找我来了,对你思念万分,说你会过日子,一毛钱的带鱼尾巴干爆沾盐香极了,谁让我没能耐,给媳妇吃不上好的,我愧得很。”我说。
“我们俩不是这个问题,当初嫁他是无奈。”
“你们家我也去了,你爸说你就会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
“哎……”她兴奋起来,“我又写了一本书,叫《春天的童话》,这回我给自己扣得更厉害了,不信,明儿你瞧瞧!”
外界对她已是沸沸扬扬,议论纷纷,她毫不在意,还把她该不该进行第二次离婚拿到《新观察》杂志上讨论。她会闯祸的。
我不由“腾”地站起身来,猛地看见她稀少的头发,想她在艰苦卓绝地孤军奋战,一激动差点儿没掉下眼泪。
离婚案在法院公开审理,被告席上的忠培举着一个绣花饭袋,声嘶力竭:“大家看看,这是罗锦给我绣的,若没有感情能给我绣吗?”
蔡忠培话还没落音,一个憨直的声音要求:“让我发两句言!”
罗锦坐在前排原告席上,一听这声想:“喲,怎么这么耳熟?”回眸一看,原来是阔别当年的前夫,也被法院请来列席,就是《一个冬天的童话》里的志国。他要把多年的积怨倾诉一番。
他还是那么膀大腰圆,头上戴着大皮帽子,脚不用看了,还是穿42号鞋。
“这两个不得意的丈夫!”罗锦想,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左起前排:陶洛诵、遇爸爸、遇罗锦;后排:遇罗勉一家三口,吴范军。殷凡摄。这组照片提供给报纸制版后,原照下落不明了
左起:陶洛诵、遇罗锦、遇罗文
陶洛诵与遇罗锦(右)
06
就在遇罗锦为自身的解放与幸福左右冲杀之际,《人民日报》内参登了一篇名为《一个堕落女人》的文章。指名道姓说遇罗锦不检点,追求老干部等等。
原来她在给哥哥平反的过程中,认识了《光明日报》的一个副总编辑,她爱上了这位副总编辑。她以前对此事守口如瓶,只是听她常说:“我想找个年纪大的,让他好好疼我两年,他老了我就用小车推着他,伺候他,用手绢给他擦哈拉子。”
她的感情纯真美好,可惜的是副总编辑是有妇之夫。这事不知道怎么被《人民日报》记者知道了,就写了这么篇足以把罗锦打趴的文章。
乔雪竹很是替罗锦抱不平,忿忿地说:“那么大报纸,跟一个女人过不去!”
罗锦也没被打趴下,反而越挫越勇,继续寻找她生命中的真命天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罗锦终于找到了吴范军,她向往期待一生的白马王子。
遇罗锦和吴范军
07
罗锦和忠培的离婚案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热烈讨论。我把罗锦在内地激起的波澜写信告诉移民香港的邢泓远,泓远一开始对她不感兴趣,问我:“她有什么主要缺点?”我告诉泓远:“她的主要优点就是带着浑身的缺点冲了出来,这句话是乔雪竹说的。”泓远在香港《争鸣》上开始报道罗锦,并让我寄罗锦的相片给她。很可惜的是,一张罗锦在北大荒的照片寄丢了。
几经波折,离婚被批准,罗锦恢复了自由的单身。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人蜂拥给她介绍对象,里面不乏名人商贾。但罗锦选中了北京钢铁学院的教师,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吴范军。
罗锦与范军来我家做客。范军个子很高,气宇轩昂,彬彬有礼。罗锦有了真爱,重获新生。她的眼睛变大了,重获神采,留着披肩发,她送我一张俩人的订婚照,她的头微微偏向着范军,一副可爱的小鸟依人状。
范军的爸爸在台湾,范军比罗锦大11岁。一九五七年,身为北京钢院青年教师的范军被划为“右派”,系里把他留下来做“反面教员”,范军告诉我说,每有运动一来,系里先让他发言,他就如实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家再发言批判。范军一直单身。
1980年代,遇罗锦和吴范军在北京留影
罗锦告诉我,范军对她心仪已久,每当有批判她的文章出现,范军都会兴致勃勃地复印,然后装订成册,保留起来。
罗锦和范军在一九八二年八月结婚,新家安置在北京钢铁学院范军的宿舍里,门口的上方挂着大画家范增先生为他们题的墨宝:童斋。
直到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罗锦乘国际列车去西德之前,这应该是她最幸福的一段生活。
这位爱我,理解我,无私地帮助我的女人走了,从此海角天涯,不知还能见面否?
我保留着她在国内给我的全部信件。先前征得了她的同意,我把一部分发表出来,诸位将看到的是一颗火热的心。
吴范军在台湾拜会作家柏杨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