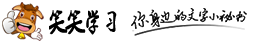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怎么写《思考建筑 读后感》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1-04 10: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思考建筑”的读后感,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事项,才能让文章既深刻又条理清晰:
"1. 明确核心观点与主题:"
"读懂原文:" 首先,你必须彻底理解所读建筑书籍或文章的核心观点、主要论点、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以及其写作背景。思考作者对建筑的核心理解是什么?他/她提出了哪些独特的见解或批判? "提炼主题:" 找出文章最想让你思考的那个“点”。是关于建筑的功能性?美学表达?社会文化意义?历史传承?技术革新?还是人与环境的互动?明确这个核心主题,你的读后感才能有的放矢。
"2. 深入分析与联系:"
"批判性思考:" 不要仅仅复述作者的观点。要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分析、评价。你同意作者的看法吗?为什么?有哪些地方让你深以为然,哪些地方让你持有不同意见?作者的证据是否充分?逻辑是否严密? "联系实际与个人:" 将书中的理论、观点或案例与实际生活中的建筑、城市环境或你个人的观察、体验联系起来。例如,你是否见过符合或违背作者观点的建筑?这种联系能让你的读后感更具说服力和深度。 "跨领域联想:" 尝试将建筑思考与其他学科(如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心理学
新与旧的哲思
这些日子身处意大利罗马,望着古老城墙的遗迹感慨万分,回到下榻处随手翻读几篇林徽因的散文。
罗马古老城墙的遗迹▲
这一读,仿佛感染了她所说的“情趣上的闲逸”。
就继续看完林徽因的生平;发现这位出色的才女建筑师,在生命弥留之际,还极力保留古建筑物。无奈就是有一群人欠缺少建筑美学修养,视古城的墙垣为封建的象征,决意将之拆掉。这一拆,也完全暴露了缺乏文物鉴赏能力的人的愚昧。
林徽因散文集▲
把城墙简化为封建的图腾的人,一定是没参考过布拉格,这个全世界唯一以整个城市,被划入文化遗产的地方吧?
布拉格的新城区不完全是钢筋水泥的科技城。但旧城区,尤其广场的旧皇宫、城堡、天文钟和教堂等,皆是中世纪罗马和歌德式的艺术品。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以及中世纪末的洛可可新艺术风格,也由鳞次栉比的古建筑和雕像,展现得一览无遗。
布拉格▲
古老,不一定就是封建。墙的基本功能当然是保护,它将一座城市或地方,分隔了内与外。
但如水,它能载舟亦能覆舟。墙在阻挡了外界的危险入侵的同时,也能断绝人们对墙外世界的探索欲望。人在墙内久了,就安逸,最终危机意识降至最低。当攻击再次出现,人又能否有效地应对?
拆除北京旧城墙老照片▲
据记载,当年与林徽因对峙,执意要拆掉北京古城的吴晗,认为古建筑是“美善鉴赏价值”的“老破砖瓦”,就直接否决了林徽因的新旧双规划的独特建议。
无价的人文景观被拆了,若再重建,充其量也只是仿古的现代作品。有谁能还原独一无二的700年的古董?如何重新装置一砖一瓦所蕴涵的历史价值和时代特征?
五十年代的林徽因▲
林徽因曾说过,如果这些古建筑拆除,总会有一天会后悔的,即便以后想复原,那都不是原来的了,只是赝品而已。
其实没错,许多年后,一些建筑家乡恢复这一些古建筑,虽然进行了一比一还原,但终究不是原来的建筑了。拆毁容易,再建却无门。拆除古城建筑物,是一并将建筑师的匠心,与民族的艺术特色一起拆毁了。连承载历史信息的标志性文物都消失了,又哪来的文化遗存?又有何昔日的风貌承传给下一代去鉴赏?当挖掘机在敲打几百年的建筑墙时,国土的记忆也随之被敲碎成粉末。
当年民工进入拆除城墙现场的旧照▲
借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筑•居•思》中的话,我们必须思考建筑和居住背面的哲学意义,去追溯每一件存在的东西所属的那个领域。
拆除古迹,不属行为艺术。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墙垣划分的边界,不是旧物停止处,而是新事开始的起点。新与旧可以相互共存,映照着悠久的变迁。墙,随时可拆。人的短视和迂腐,却不一定能除去。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
抛开拆除旧城墙话题,联想年轻时阅读一篇关于科举废除的论文时,有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
它来自张作霖的智囊人物——袁金铠的日记,写于1909年夏,彼时,39岁的他正投于盛京将军赵尔巽门下。他对于新与旧的感慨,正是20世纪初的普遍情绪。
张作霖的智囊人物——袁金铠▲
“新旧之见,近乃日甚,无定体也,无休止也。前之所为者本新也,自今视之皆旧也;人之所为者本新也,自我视之皆旧也。于是舍旧而谋其新,再越一时、再历一人,则见适间之、舍旧某新之种种,又皆旧已!于是又谋其所谓新者,纷更烦扰,将不知何时、何地为得新之止境也。”
科举时代画册▲
在描述晚清最后十年的历史时,人们常以清王朝之腐败、无能、列强之咄咄逼人、革命党之兴起为视角,却很少人将目光投射于士大夫的内心。
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变化接踵而至的世界,他们如何慌乱不堪。你可以想象,你在四书五经、八股文中,已经耗费了半生,突然要求你面对经济、政治、立宪、化学、物理这些新概念。你又认定,这些新概念不仅是知识上的兴趣,更与国家存亡相关。你渴望速成,越想速成,往往欲速不达,新与旧裹成混乱的一团。
民国时代的北京城▲
一种简单、粗暴的二分法也就此形成。
新与旧、西与中、今与古,都变成了紧张的对立关系。历史则一条线形,它有着明确的方向。于是,为了支持一方,就必须否定另一方。在慌乱中,做出判断与行动。而愈是慌乱,愈渴望一个明确口号与主义,愈需要创造一个明确的敌人。当一个明确的敌人被推翻后,慌乱并未稍减,反而更生焦躁。
走出旧家庭民国女性▲
成长在六十年代的我,也仍深受五四一代的影响。
那时的文化人物的言辞、思考方式,塑造了我对世界的最初思考。“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同样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这段陈独秀的话,那股打破旧世界的青春冲动,曾让我热情难耐。(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意思是民主和科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两面旗帜。其中民主就是德先生,而科学就是赛先生。)
陈独秀文集▲
在袁金铠与陈独秀之间,你看到一个日趋激进化的思想趋向。这趋向贯穿一个世纪,也作用于我身上,甚至内化成思想方式的一部分。
过去一年,人们对于AI的热情,常令我想起一个世纪前华夏读书人的感慨。一方面,你感到呼啸而来的兴奋,人们似在畅想一个升级的文明体的出现,技术爆炸将把我们拖入科幻小说的世界;另一方面, 我强烈地感觉到思想与价值的混乱,我们似乎还未搞清楚一个现代国度、一个现代人的模样,就准备要大踏步进入一个后人类的世界了。
《现代化陷阱》▲
一位晚清御史曾感慨,“新学盛行,固富理想,然予终觉旧学深切有味”。而我最近常有相似的感慨。
那些19世纪的小说、20世纪的散文,古老的城墙、一部老电影、旧唱片、竟更显迷人。
聆听旧唱片的音声▲
《新韵更迭·七律》——作者
古巷残墙忆旧章,苔痕石径韵悠长。
檐前宿燕寻前梦,陌上新芽唤曙光。
旧纸诗成尘影瘦,新弦曲奏彩云翔。
乾坤代谢寻常事,且赏今朝菊桂香。
建筑的学问,何处安身:四所学院如何铸就建筑师?
"道理应可传授建筑的学问,起初是没有学堂的。它不在书本上,而在师父的规尺和徒弟的目光之间,在石头的敲击声与木料的刨花香里。人们相信这门手艺里藏着的,是些不可言说的秘密,只能靠着年月,一点点地浸润,一点点地领悟。
后来有人觉得,美的背后应有法度,秩序之下当有规条。道理是可以写在纸上,放在课堂里教的。于是,建筑教育有了自己的命运。
我们故事要说的,就是这股潮流里的四次转向:巴黎画室里对古典的回望,德绍工厂中向未来的呐喊,德州荒原上那固执的沉思,以及伦敦雾里关于图纸自身的狂欢。
01秩序的黄金时代巴黎美术学院 (École des Beaux-Arts)
▲巴黎歌剧院,折衷主义代表作品在建筑的漫长谱系尚未被学院的理性所规训之前,它的生命力,是在一代代无名匠人的手中默默流淌的。中世纪那些指向天空的哥特教堂,建造的奥秘,并不记录于纸上,而是藏在行会的口传心授里,刻在泥瓦匠大师(Master Mason)勘量石材的指掌间。建筑,因此是一种与土地、材料、信仰紧密相连的深沉手艺,质朴而坚实。新的精神则从文艺复兴的薄雾中浮现。当一群学者从意大利的城邦走向旷野,在古罗马的断壁残垣间流连,建筑师的身份便开始了静默而深刻的转变。关乎比例、和谐与宇宙秩序的智识之学,被从单纯的“建造”中提炼出来,建筑师也因此从工地的劳作者,转变为书斋里的思想者。然而,将这份属于少数天才的灵光,锻造成一部人人皆可修习的、宏伟而严谨的法典,则是十七世纪法兰西王权的事业。在为君权与荣耀规制一切的雄心下,巴黎美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Arts)应运而生。它标志着建筑教育从经验的传承,走向了体系的建立,一个秩序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启。学院的核心信念单纯而坚定:建筑的至高之美,范本早已在古典时代臻于完美,后人的使命,就是以最虔诚的技艺去理解、继承这份不朽的遗产。▲罗马大奖获奖作品这套被后世称为“布扎”(Beaux-Arts)的体系,其严谨,其坚定,在当时无出其右。它为建筑师提供了一套丰富而典雅的古典语汇——柱式、拱券、山花,而设计的要义,便是在白纸上,进行一场名为“组合”的沉思。一切秩序皆由平面生发,轴线如命运般贯穿始终,统率着对称的格局与主次的尊卑。为将这套法则深植于学子心中,学院设立了二元并行的教学之路。理论与评判的权柄归于学院,而技艺的磨练则在各个独立的工作室(Atelier)中,由一位大师(Patron)亲手传授。学生的成长,依赖于一场场竞赛的严酷筛选。这条路的终点,是传奇的“罗马大奖”(Grand Prix de Rome)——一份无上的荣耀,优胜者将被送往罗马,去亲身感受那作为一切古典源头的阳光与空气。多数图纸的宿命并非立于大地,图纸本身,便成了作品的终点。于是,一种极致的图面艺术得以发展。墨线,精准而不容迟疑,勾勒出结构的骨骼;水彩,淡雅而层层浸染,赋予纸面以光影的呼吸。每一张图,都是一个静默而完美的世界,无声地诉说着那个时代对于秩序与永恒的全部信仰。▲巴黎美术学院庭院然而,历史的河床,总是在最平静的河段下,悄然改变着流向。那些体系中最优秀的学子,那些罗马大奖的桂冠得主,当他们真正站在帕埃斯图姆神庙粗粝的石柱前,感受到地中海的风拂过不同于罗马的肌理时,一种沉默的疑问,或已在心中萌生。书本里的普世法则,与眼前这片土地上真实的阳光与石头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可言说的距离。一场风暴,正从这片古典世界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
02机器时代的社会宣言国立包豪斯学校 (Staatliches Bauhaus)
▲乔治·穆奇和阿道夫·迈耶:“号角屋”平面设计,1923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欧洲大地满目疮痍,旧世界的秩序与美学,连同其所依附的君权与廊柱,一同坍塌在废墟之中。一群年轻人选择背过身去,不再凝望罗马的废墟,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机器的齿轮与轰鸣。他们相信,建筑的出路不在于复刻旧日的美,而在于为劫后重生的大众,创造一个全新的、诚实的、属于机器时代的生活。1919年的魏玛,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发表了一份薄薄的宣言。封面上,列奥尼·费宁格用激越的木刻线条,刻画了一座光芒四射的“社会主义大教堂”。宣言的开篇,格罗皮乌斯写道:“所有创造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建造’!”。他呼唤艺术家与手工艺人之间不再有那“使人自傲的障碍”,呼唤他们共同创造“未来的新结构”。这便是包豪斯(Staatliches Bauhaus)的诞生。它像一声惊雷,宣告了对巴黎美术学院所代表的古典体系的彻底决裂。▲包豪斯宣言和包豪斯计划,1919包豪斯的核心思想,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建筑必须斩断与一切历史样式的联系,拥抱工业化大生产。建筑不再是为少数权贵服务的纪念碑,而是为广大民众解决居住问题的社会工具。为了培养能够胜任这一使命的新型创造者,格罗皮乌斯构建了一套前所未有的教育体系。所有入学的新生,无论日后志向为何,都必须先进入为期半年的“基础课程”(Vorkurs)。在这里,没有古典柱式,没有石膏像,甚至没有“风格”这个词。导师们——从神秘主义者约翰·伊顿到构成主义先锋莫霍利·纳吉——要求学生们忘掉一切先入为主的美学观念,回归事物的本源。他们用双手去感受木头的纹理、金属的冰冷、织物的柔软;他们用眼睛去观察光如何穿过玻璃,色彩如何彼此呼应。这是一场感官的“洗礼”,旨在将学生的创造力从陈规旧习的重压下彻底解放出来。▲包豪斯的基础课程练习完成了这场精神上的“格式化”,学生们便进入各个“工作坊”(Workshops)。金属、纺织、木工、陶艺、舞台……每一个工坊都由一位“形式导师”(通常是艺术家,如康定斯基、克利)和一位“技术导师”(工匠)共同执掌。艺术的想象力与建造的现实性,在这里被强制性地捆绑在一起。学生们不再是画室里空谈的“艺术无产者”,他们设计的茶壶、台灯、椅子,都必须以能够被工厂批量生产为前提。▲卡尔·J.尤科尔和威廉·华根菲尔德:玻璃台灯,1923/1924这场革命的高潮,是1925年包豪斯迁往工业城市德绍。格罗皮乌斯亲自设计的德绍校舍,本身就是一部石与钢写成的宣言。巨大的玻璃幕墙消融了室内外的界限,不对称的体块自由伸展,平坦的屋顶如同机器的甲板。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在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诚实、透明、高效、没有一丝多余的装饰。它不再模仿任何历史,它本身就是历史。▲包豪斯主楼西南视角(上)与东南视角(下),1927然而,这场过于纯粹的革命,也为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当包豪斯的大师们流亡美国,深刻的社会理想与艺术实验,在新的商业土壤中被逐渐简化为一种易于复制、缺乏灵魂的“国际风格”。这场始于魏玛,旨在为大众建造一个美好新世界的乌托邦实验,最终变成了一种风行全球的建筑时尚。但无论如何,包豪斯那短暂而灿烂的十四年,已然在建筑教育史上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纪元。它所确立的“基础课程+工坊实践”的教学框架,至今仍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建筑与设计学院的骨架。它所倡导的“艺术与技术相统一”的理想,也如同一颗永恒的星辰,持续地拷问着后世的每一位建筑师:我们为谁而设计?我们又该如何诚实地面对我们身处的时代?
03荒原上的思想拨正德州骑警(The Texas Rangers)
▲彼得·艾森曼:六号住宅,1975包豪斯播下的种子,越过大西洋,在美国的土壤里长出了另一副模样。那份来自魏玛的社会理想与艺术实验,在战后富足而讲求实用的商业浪潮中,被渐渐磨平了棱角。现代主义,从一场曾激动人心的革命,变成了一套枯燥乏味的教条,一种可以快速复制的“国际风格”。建筑的深刻内涵,似乎正消散在一片思想的荒原上。就在这片荒原的中心,1950年代的德克萨斯,一群年轻的建筑师从欧洲而来,发起了一场沉默而坚决的反叛。他们之中,有日后声名显赫的理论家柯林·罗,也有诗人般的建筑师约翰·海杜克。人们后来给这群人起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名字——“德州骑警”(The Texas Rangers)。他们的武器,不是马背上的左轮枪,而是柯布西耶的别墅图解,和一张张被画了无数遍的九宫格。他们的反叛,并非要推翻现代主义,而是要为这个被“掏空”了的现代主义,重新寻找失落的灵魂。建筑的本质并非仅仅是功能,更在于形式的内在逻辑。一场深刻的教学变革,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悄然上演。▲弗斯卡利别墅(左)与加歇别墅(右)的比较图解柯林·罗向学生们展示了一张不可思议的图纸:他将十六世纪帕拉第奥的弗斯卡利别墅与柯布西耶的加歇别墅并置在一起,通过几何分析,揭示出两者在平面构成与比例韵律上惊人的相似性。他的论点如同一道启示:建筑中存在一种超越时代与风格的、纯粹的“形式语法”。现代主义的根,原来一直深植于古典的土壤之中。于是,建筑教育的核心,从学习如何“解决问题”,转变为学习如何“阅读文本”。柯布西耶等现代大师的作品,成了被反复精读的“圣经”。而“德州骑警”发明的核心教学工具,是一个看似简单,却蕴含无穷变化的练习——“九宫格问题”。▲约翰·海杜克的“九宫格”练习在一个由十六根柱子构成的九宫格框架内,学生被要求通过置入墙、板等最基本的建筑元素,去探索空间最本质的命题:中心与边缘、围合与穿透、静止与流动。功能、材料、文脉……所有外部世界的纷扰都被暂时悬置,建筑被前所未有地还原为关于空间的智力游戏。图纸的语言也随之改变,水彩渲染的温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静、客观的轴测图,它能最清晰地“图解”出空间的生成逻辑。约翰·海杜克的德州住宅系列,是这一时期教学实验最极致的成果。这些房子大多只存在于纸上,它们是纯粹的“卡纸建筑”,是形式逻辑推演的诗意结晶。▲约翰·海杜克:德克萨斯住宅1,轴侧图这场在美国南方荒原上仅持续了数年的教学实验,其影响却如涟漪般扩散开来。当“德州骑警”们日后将这套思想带到康奈尔、库伯联盟乃至欧洲的ETH时,它为整整一代建筑师,包括后来的“纽约五人组”,重新注入了被遗忘的理论深度。他们证明了,即便是在一片看似贫瘠的土地上,思想,依然可以凭借其自身的严谨与力量,开垦出一片丰饶的绿洲。
04伦敦雾中的纸上风暴建筑联盟学院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贝德福德广场那场在美国德克萨斯荒原上燃起的思想火焰,越过大西洋,以一种更加猛烈的方式,回到了欧洲。如果说,柯林·罗和他的“骑警”们,还在现代主义的屋宇内,小心翼翼地拂去尘埃,试图修复梁柱间失落的古典秩序,那么1970年代的建筑联盟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简称AA),则索性一把火烧掉了整座房子。在一代传奇掌门人阿尔文·博雅斯基的治下,这所贝德福德广场上的百年老校,成了一座思想的“巴别塔”。在这里,建筑的根基不再是坚实的土地,而是漂浮的、变幻的观念。图纸,也不再是通往建造的桥梁,它本身,就是目的地。这阵风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一个叫“建筑电讯派”(Archigram)的团体。这群年轻人,大多出身于AA,骨子里带着一股桀骜不驯的野气。他们厌倦了战后伦敦的灰败与沉闷,便自己动手办了一本拼贴画似的小杂志。他们从科幻小说、太空竞赛和消费品广告里汲取灵感,画出了一个个石破天惊的构想:一座可以随时插拔、更新的“插件城市”,一座可以在大地上行走的巨型“行走城市”。建筑在他们笔下,第一次摆脱了自身的重量,变成了一种轻盈的、流动的、可以传播观念的媒介。▲建筑电讯派的插件城市,彼得·库克博雅斯基懂得这群年轻人的心思。执掌AA时,他便将这种游击式的精神,系统性地请进了学院的殿堂。他将“单元制”推向极致,全球最前卫、最大胆的建筑师开坛设讲。AA不再教授一种统一的“真理”,而是变成了一个允许无数种“真理”相互碰撞、争鸣的“思想联邦”。于是,一场长达近二十年的“纸上风暴”开始了。在博雅斯基眼里,建筑师最重要的产品,是凝结了思想的图纸。设计的评判标准,不再是功能是否合理,结构是否可行,而是观念是否足够颠覆,图面是否足够有力。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一代日后将彻底改变世界建筑图景的年轻人,留下了他们最初、也最纯粹的足迹。▲扎哈·哈迪德:马列维奇的构造,1977扎哈·哈迪德从俄国构成主义的画作中,释放出爆炸性的、反重力的空间碎片,她的毕业设计《马列维奇的构造》,仿佛一场纸上的宇宙大爆炸。雷姆·库哈斯,则带来了冷峻的社会叙事与反讽,他的毕业设计《逃亡,或建筑的自愿囚徒》,用一个关于柏林墙的都市寓言,宣告了建筑作为一种社会评论工具的到来。伯纳德·屈米,则将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的思辨,转译为一系列关于事件、运动和空间的图解。▲库哈斯:逃亡,或建筑的自愿囚徒,1972他们不再满足于“德州骑警”那般,在建筑学内部寻找形式的法则。他们贪婪地望向建筑之外的世界——哲学、电影、文学、艺术……一切都被熔炼为建筑思考的燃料。当他们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引入建筑时,并非在赶时髦,而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回归——将哲学长期以来所借用、却又同时压抑的“建筑性”——即关于不确定性、复杂性、内在矛盾性的思考,重新带回建筑学的中心。AA的纸上风暴极大拓展了建筑的思想边界,但也使建筑教育一度陷入图像崇拜与建造疏离的两难,直到九十年代数字化浪潮到来,这种观念建筑才重新找到生成的可能。这场伦敦雾中的风暴,至今仍深刻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宣告建筑可以不是房子,它可以是一段叙事,一种批判,一场辩论。而建筑师也不再只是匠人或工程师,他们首先是思想家。1.《The Architecture of the École des Beaux-Arts / Arthur Drexler (Ed.)》
2.《Designing Paris: The architecture of Duban, Labrouste, Duc, and Vaudoyer / David Van Zanten》3.《The New Architecture and the Bauhaus / Walter Gropius》4.《The Bauhaus: Weimar, Dessau, Berlin, Chicago / Hans M. Wingler》5.《The Texas Rangers: Notes from an Architectural Underground / Alexander Caragonne》6.《The Mathematics of the Ideal Villa and Other Essays / Colin Rowe》7.《Collage City / Colin Rowe & Fred Koetter》8.《Mask of Medusa: Works 1947-1983 / John Hejduk》9.《Archigram / Peter Cook (Ed.)》10.《The Architecture of Deconstruction: Derrida's Haunt / Mark Wigley》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