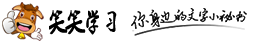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精心挑选《文学活动说说》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1-05 20:27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写好“文学活动说说”时应注意的事项的作文:
"点亮文字之火:撰写文学活动说说时应注意的几点"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无论是盛大的书展、作者签售,还是一场温馨的读书分享会,都吸引着无数热爱文学的人们通过“说说”等形式在线上分享感受、传递信息。一篇精炼、生动、有吸引力的文学活动说说,不仅能点亮活动本身,更能激发他人的阅读兴趣,扩大活动的影响力。那么,在撰写这类说说时,我们应注意哪些事项呢?
"一、 核心要素,清晰呈现"
文学活动的说说,首要任务是传递信息。因此,清晰、准确地呈现活动的基本信息至关重要。这包括:
1. "活动名称与主题:" 点明活动的全称和核心主题,让读者一眼就知道这是关于什么的。 2. "时间与地点:" 准确提供活动举办的具体时间(日期、时段)和地点(具体场馆、地址),方便感兴趣的人查询和参与。 3. "主办方与嘉宾(如有):" 提及活动的组织者以及邀请的作者、嘉宾等,增加活动的权威性和吸引力。 4. "活动亮点与内容:" 简要概括活动的特色环节或主要内容,比如是讲座、互动、新书发布还是颁奖典礼,激发读者的好奇心。
将这些要素简洁明了地放在说说的开头或显著位置,是吸引读者
难忘青春过往 再谈梦想初心——“说说心里话:我和我的文学”活动侧记
活动现场
马原
“似有神助,独具一格。”10月16日,在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入会三十年专场”之“说说心里话:我和我的文学”活动现场,作家马原缓缓展开自己加入中国作协时的入会申请表复印件,凝视许久,并指着上面这句话说:“铁生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这张40年前的入会申请表上显示,推荐马原入会的作家是史铁生和冯骥才。冯骥才用蓝色的笔在史铁生的文字下方写道:“马原同志几年来的创作,证明他是很有才华和潜力的青年作家。无论是作品的质量、分量还是影响,都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国作协的一名会员。”马原还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中国作协会员证,这本深蓝色的证件充满了岁月的痕迹——表皮有很多划痕,勒口被老鼠啃坏了一部分。打开会员证,马原说,“1985年10月21日,是我加入中国作协的日子。我看着40年以前的照片,那时还是长方形脸庞,大胡子,挺帅的。人生就这样一晃过了40年”。
“您的文学经历文学生涯,是中国作协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您的文学起点,已被时代郑重记录和珍藏。”参加此次作家活动周的作家们,都收到了这样一份特别的礼物——入会申请表复印件。这份礼物将作家们拉回到记忆深处,共同怀想起文学生涯启程之时的梦想初心和青春过往。据了解,这一策划的初衷是想给作家们一个文学的惊喜,帮助他们回忆并讲述自己的文学往事和入会故事,也希望作家们能从中获得无与伦比的归属感、荣誉感和成就感。
活动现场
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宏森,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邱华栋,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李一鸣、何向阳出席活动。活动由吴义勤主持。
“文学和我的生命融在了一起”
谈及与文学相伴的岁月,那些深藏在漫长时光里的热爱与坚守,随着作家们的真挚讲述,也渐渐清晰起来。
李钢
展开入会申请表复印件的一瞬间,诗人李钢说,这字迹可真熟悉,这是1987年青涩的自己写下的字。“打开这份申请表,也就是打开了20世纪80年代火热纯真的激情。”他绘声绘色讲起自己创作组诗《蓝水兵》和参加诗刊社第三届青春诗会的经历。“我当年坐火车去成都送稿子给《星星》诗刊,保安一给我打开门,我就看见诗人流沙河从后门拎着暖水瓶到办公室一坐,在看我的稿子。”后来,李钢的《蓝水兵》被分为两组,先后由《星星》和《诗刊》推出,在诗坛产生了不小的轰动。他回忆说,“80年代是激情的年代,也是理想主义闪闪发光的年代”。
姜琍敏
“文学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文学对我而言,有心灵救赎的意义。”作家姜琍敏说,从太湖煤矿的一名普通电工到调入《雨花》杂志成为文学编辑,文学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成为漫长岁月里的心灵支柱。“时至今日,我仍然还在写。对我而言,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它真的和我的生命融在了一起。”
张中海
作家张中海说,这次回家让自己充分感受到中国作协对作家的重视和关怀。“能够在创作上走这么远,我要感恩文学、感恩生活、感恩时代。”近年来,他把对乡土和田园的观察思考写进《农事诗》,把黄河的雄浑与壮阔写进了《黄河传》,以此展现作家的使命担当。“我的文字是生活和时代给予我的,也是由衷地从心里生发出来的,唯其如此,才能写出真诚的作品。”
阎欣宁
军旅作家阎欣宁在回忆自己的文学之路时说,写作这条路走得不算容易,但自己一直都很痴迷。“感谢中国作协的,在入会30年之际,我们应当回头看看风雨来时路,这很重要。”
刘一达
出生于北京的作家刘一达曾有过24年的记者生涯,这段经历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灵感和素材。他亲眼目睹北京城几十年来的巨大变迁,按捺不住心中的创作梦,决心开启自己的京味文学创作和研究之路。入会31年来,他坚持多栖发展,既写过京味小说,也写电视剧和话剧剧本,努力推动京味文化传统创新发展。
徐小斌
“感谢中国作协唤我回家。”作家徐小斌回忆起9岁时偷偷读父亲新买回家的新版绣像《红楼梦》,“当我读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一章,泪水哭湿了枕头”。20世纪80年代,她开始写作,先后在《北京文学》《十月》等杂志上发表了短篇作品。当她写下人生中第一个中篇小说后,鼓起勇气投给了《收获》,一周之内就收到了电报,电报里写,“见面以手持《收获》为号”。到了上海,迎接自己的是巴金先生之女李小林。李小林将她带回家改稿,并建议修改小说结尾。“我是无名之辈。《收获》编辑那么细致认真,我非常感动,后来这篇小说发在《收获》1983年第5期,对我此后的创作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杨雪
作家杨雪的少年时代是浸泡在说书人的故事世界里的。他回忆起年少时,外地读书人辗转来到家乡泸州,给乘凉的街坊们讲故事或说评书以换取食物。从他们口中,自己知道了《穆桂英挂帅》《薛仁贵征西》《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故事。“从中我懂得了正义、良知与罪恶、虚伪,也有了从事写作的念头。”他谈到,多年来自己始终致力于描写故乡川南的民俗风情和历史意蕴,以文学之笔记录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
“将文学事业一代又一代传下去”
在回忆与讲述中,作家们不仅回望了自己与文学的过往,更将目光投向未来。那份对文学的珍视与传承之心,也在分享交流的过程中愈发浓烈。
申弓
“我来自广西北部湾,经常仰望着中国作协这个‘家’。”作家申弓谈起此次受邀参加活动,感到非常暖心和激动,尤其是那块镌刻着入会天数的专属纪念牌,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创作初心。他说,自己坚持写小小说30多年了,小小说这一文体不仅可以记录身边丰富有趣的小事,更可以写时代的宏大题材,自己会一直坚持写下去。
谢柏梁
“细致、周到、精致,如此温暖人心,非常让人感佩。”作家谢柏梁说,在入会介绍人一栏里看到恩师徐中玉的名字,无限往事浮现眼前,令人感怀。他谈到,在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时很震撼,许多文学文物的价值是无形的,期待中国现代文学馆能够创新更多数字化的传播方式,让不能亲身参观的人也能看到这些珍贵的藏品和展览,最大程度传播和发挥中国文化的价值。
张旻
作家张旻认为,自己这代人走上文学的道路,并能最后留在这个行当里,更多是源自天性。“这次活动,除了回家的温暖,我还感受到了发自肺腑的尊重。”他回忆起自己与《人民文学》《花城》《作品》等文学杂志的情缘,感谢文学道路上的编辑和引路人们,“感谢他们成就了我的文学梦,成就了我平凡但很有意思的一生”。
杨远新
“我今年72岁,但因为文学,我感觉自己才27。”作家杨远新此话一出,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被中国作协推荐参加武汉大学作家班、1994年第一次申请入会失败的曲折……他用生动的湖南口音讲述与中国作协有关的许多往事,并表示,自己不仅要继续坚持用作家的眼光观察生活、以警察的情感丰富文学,更要让家人后辈接过手中的接力棒,将文学事业一代又一代传下去,“不负中国作协会员这一光荣而神圣的称号”。
金萍
“我曾是一个乡村的民办教师。日子索然无味的时候,为了宣泄内心的情感,我就写诗,写小说。”来自安徽蚌埠的作家金萍讲到,1983年,她生平第一次出远门,坐上绿皮火车去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参加笔会,当时作家丁玲也在。金萍说自己本姓“钞”,因为经常被人读错而深感苦恼,丁玲就支招说:“你应该是少数民族,不如把名字里的姓去掉吧,就叫金萍。”这个笔名一直沿用至今。谈及参加此次活动的感受,金萍说,写作多年,虽然一直默默无闻,但感谢中国作协能够自己“回娘家”。“虽然左手没有鸡,右手没有鸭,可我有一颗滚烫赤诚的心!”
阿拉提·阿斯木
新疆作家阿拉提·阿斯木回忆起自己如饥似渴学习小说创作的青春年代。他说,20世纪80年代,自己所有业余时间都在读小说,在不停地研究如何写小说。因为一系列的学习探索和不停写作的努力,自己在结构故事、语言运用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变。他还谈到,中国作协多年来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是非常有成效的:“我们以前多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现在都可以用汉语创作诗歌、散文、小说。感谢中国作协有组织的引导和培训,为少数民族作家打开了思想和视野。”
古耜
作家古耜表示,希望中国作协可以进一步关注那些虽然籍籍无名却始终在创作的年轻人,给予他们机会,扶持他们创作,扩大和团结基层作家队伍。
葛均义
来自黑龙江绥芬河的作家葛均义谈到自己的文学研究,认为文学的最大力量在于风骨和文采,风即情感,骨就是思想,文采就是艺术特色。
任芙康
“岁月又慢又快,就像众多短剧一样,既不虚妄也不真实,只是一种感觉,想得开的人当自在度日、从容前行。余生将努力当中国作协会员当得久一些,再久一些。”活动最后,作家任芙康忍不住读起自己在现场写下的感怀,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作家们数十年来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与无私奉献,当然远非简短的分享所能道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到大家与文学相伴的珍贵岁月,触摸到他们历久弥新的文学情怀。这份对文学的赤诚,在今天依旧令人动容,也让更多人深切感受到文学的温度与力量。
相关视频: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5年10月17日1-2版
摄影:冯海文
视频制作:唐山山 李菁
编辑:刘 雅
二审:张俊平
三审:王 杨
我握紧文学,正如紧握着一面盾
吴任几,1997年出生于上海,现就读于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院。2019年8月,由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孔子学院评选为“中国三十岁以下三十位诗人(30under30)”之一。曾获得闻一多杯全国原创诗词大赛二等奖、上海市民写作大赛写作高手、复旦大学光华诗歌奖等。诗歌作品刊登于《诗刊》《星星》《中国青年报》《上海文学》《作品》《诗歌月刊》《诗林》等,收入《中国诗歌2019年度精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国内外多本文学年鉴。
--------------
当我回想起遥远,但又显得过于漫长的童年,我总是会先想到我的父亲。他显然没有活在让自己最快乐的生活里。但我从未看过他拿起过烟或酒,一次也没有。
而我读过父亲写的文章,很长时间,我也把这些文章作为自己写作的范本。但事实上,在他充满跌宕与矛盾的一生,他从未真正有充足的时间来写作。他花了太多时间,让这个家庭从险恶的命运里跳出去。而他也未曾期待过我会成为一位作家。
但我想,那时候,我已经成为一位作家。至少,在父亲的示范下,我已经在像一位作家一样疯狂地阅读和思考。在与父亲极为偶尔的闲谈中,我认识了托尔斯泰、巴金、尼采……那些他长期阅读的作家。在闲谈中,他向我展现了他如何把他们的思维化作了自己的思想武器。虽然,这样的闲谈只是凤毛麟角的。
我们的家庭仍沉浸在七位数债务的压力中。我的父亲还需要采取很多行动,那些行动仿佛永远是紧迫而无尽的……将他从休息中拉出来,将他从拓展自己的可能性中拉出来,甚至,将他从与儿子交谈的本已很短暂的时间中拉出来。我们关于文学的对话很难详细展开,我们从来没有一本正经地,为了文学而讨论过文学。可这一点也没有影响我同样也调用起那些作家,主动地展开对我生活的思考。然后,我就学会用自己的时间去寻找更多的作家了。
为此,我一直相信,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位作家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是作家很久了。因为他早已形成了像作家一样的阅读习惯与思维方式。他可能只是缺少一些相应的技巧。而技巧,只要通过耐心的学习,都是可以最终习得的。
我的探索给我带来挫败,我的挫败就把我引向阅读
高考结束后我才真正拥有了更多的时间。但我尚未把时间用在成为作家的努力之中。我从来没这样想过。成为作家,是一个宏大而过于抽象的目标。我不敢朝这个方向去想。
我想过很多种对自己人生的方案,我尝试创业,在一次并不惨痛的失败后我想,我应该加深自己的专业;我在各式各样的大公司里实习,试图能在一项行业的一个岗位里找到我的一席之位;我结交了各式各样的朋友,尝试去理解他们的生活,并自问这样的生活是否是我想要的……我做了许多让同龄人感到意外而好奇的尝试。这些尝试占据了我每天白天的几乎所有的时间。
尝试是必要的。但高强度的尝试也会带来高密度的挫败。挫败多到一定密度,则必然会带来痛苦与分裂。可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让这些挫败从根本上影响我。我的生活,有一如既往不会分裂的地方。我仍一直在像父亲一样阅读。
我的探索给我带来挫败,我的挫败就把我引向阅读。越是这种时候,阅读越是能给我带来我应有的感知,以及面对生活的新的方法论。尤其是生活给我带来重大挫折的日子,我一周能读完五本书。
就像父亲曾经向我示范的那样,我用新的阅读组织新的经验,使内心的轨迹微调;而不至于在它找到正确的方向前,因先前的经验全盘遭受否定而慌乱地脱轨。
——或许,我就是这样开始我的写作的,在我还没有意识到它就是写作的时候。我只是把那些思维的过程记录了下来。而或许恰好因为这些思维的转变不是以数理逻辑为基础,而是基于一种与前人作品、内心观念、哲学观测的互文。我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就摸到了文学的门口。
《宝塔与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下的。
后来这首诗受到了许多专家的关注。关于它的转载、报道有很多篇,解读也有很多种。但有真正的朋友问起的时候,我只会说:“这就是对一种挫败状态的整合,以及因此带来的,确实的,对生活的和解与感激。”
当时我还在创业,刚做出了一些起色,更多的需求和风险也随之逐渐浮现水面。我还沉溺在一种“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的情怀之中。但就在这样的时候,团队里两三位核心成员突然相继表示,可能需要离开。他们也都是学生,现在家里人希望他们更好地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同时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比如负责程序开发的合伙人刚输掉一场豪赌(他固有的嗜好,但这次他真的赌得一分钱不剩了);开始剑拔弩张地问我要钱,不然也要带着所有的资源离开……
我的笔像是被笔下的文字推着走的
情感上,我感到的只有压力与背叛。
但在一个安静的傍晚。我独自坐在书桌前的时候,写下了这首诗:
宝塔与湖
那些人从四面八方赶来
有的是为了登塔、有的是为了看湖,
丰腴的湖,远处青山隐隐,
云朵让天空无限扩大。
宝塔前排起密密长队,接起湖边散装的人群,
又将下塔的人交还给湖边,
整个过程无比冗长。直到
黄昏溶铜般降临,笼罩住这片慵倦的景,
我们仍在塔上,再上一层,湖又小一圈。
那天我反倒在一个极为冷静和放松的心情里。我的笔像是被笔下的文字推着走的。我想到什么就先写下了什么。
第一句下笔,我不自觉地就写下了“那些人”——他们就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也许就是聊了三两句梦想,对方答应了一句:“好,我跟着你干。”我想起那时的感动,以及一年多以来我们的筚路蓝缕。那么,我应该想起我们出发时的可爱的样子。无论如何是出于什么目的,那都是真诚的。
第二句开始,我想,我该如何说出我现在的困境呢?我不能任凭自己的冲动说气话,于是,想寻找一个文学上的类比。比如,一群人聚在西湖旁边。但有的是为了登塔,有的是为了看湖。而现在看湖的人到了时间,要沿着湖走远……
是这样的。可即使是这样,我不由打断自己的比喻,客观地做出评价,他们确实在整个过程中都无比投入地在场,甚至我们也一起经历了不少美丽的风景。就像“丰腴的湖,远处青山隐隐/云朵让天空无限扩大。”
——可为什么看到了美丽的风景,却不愿意继续留下来呢?我急切地问,因为这就是当时困于心梗的最大的诘问了。
那,就顺着比喻来说吧,因为分明人心是灵动而相对的;这样的矛盾是流动的,看湖的人也会去尝试登塔看看,登塔的人也会下来看看湖……
——但矛盾究竟是什么呢?
“是视觉。”我看了一眼窗外的黄昏下的马路。在昏暗的灯色下,人群显得愈发模糊:“就像,越是往塔上走,越会把湖边的人看得抽象。而在湖边的人走得愈远,也会觉得塔这个物件愈发渺小。”
我一边不自觉地就把窗外的天色写进了我的诗里。一边借助着这番思考,想着,如果我能真正冷静地和团队成员谈一次话。那又该说些什么呢?
——我当然想要把我在塔上看见的价值观传递给他们。
可一个个刚刚开始探索人生路径的青年,应该创业还是在正统的路径去寻找更多的积累;又或者是否该在已经极度困难的时候杀鸡取卵……这谁又说得清呢?
分明是说不清对错的事情。一时间也不能说清楚。
我看着我已经写下的“我们在塔上,再上一层,湖又小一圈。”,决定添上一个“仍”字。
诗写完了。
没有这个“仍”字,那仅仅是诗人“会当凌绝顶”俯视一切的豪情。但现在看来,这样的豪情应该被打破。正如在塔上的我如果仅仅俯瞰那些在湖边越走越远的人,只会产生不解与责怪。正如我内心对他们还怀有责怪,但那只是因为我还在塔上。我无法超过自身的视觉,而获得真实的知觉。
添上“仍”,则就是一种看破自身局限性的无奈了。我感知,那么也因此否定了我的偏见性。我也因此知道,应该去获得真实的焦点。
如此,就让我们把整首诗的焦点重新聚焦在第一句吧。“那些人从四面八方赶来”,那才是真正没有偏见的一句话,没有自欺欺人的话;恰好,也正是整首诗最温情的话。
原来在第一句话写完之后,这首诗的主旨已经写完了,别的句子都是它的旁注。正如,我们后来发生的不愉快,都不会使我们出发时候的真诚变质。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你们曾经赶来。
一个作品在启发别人之前,需要真的使自己受益
两年前,我们家的经济情况终于渐趋正常。父亲认为,有必要花一些钱让我去更多的地方走走。我们一起去了埃及。在开罗,我们沿着尼罗河的岸边走着。我突然对他说,我想做一名全职作家:“但这很困难,真的,太困难了。我甚至无法出一本自己的诗集。”
我补充说,因为现在的环境,若是单纯写作,肯定无法支持我的生活。
说这些的时候我避免父亲的目光。我不知道该如何看着他,他已经六十岁了,却依然还在为这个家庭工作。而我很快就要毕业了。照理来说,我应该要尽快接起经济的责任了。
这一次,我们又聊起托尔斯泰、巴金……那些他如数家珍的作家,他们的生活,以及我们各自对他们作品的见解。
“所以,你知道文学与电视剧的本质区别。”父亲总结道,“那些作家都是真正地经历了那些故事和苦难。至于写下来,只是需要另外花一些时间。”
我们面对尼罗河,双手撑在河岸的栏杆上。我望着对岸灰色的城市轮廓,海燕往来于阿拉伯船只,冒起蒸汽……
“当然,你的写作也会帮助你的生活,就像,一面盾。而这将是你最珍贵的武器。”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
我的父亲一如既往是对的。
两年后的今天,我感受到,更多的矛盾像那日尼罗河的潮水,正不由分说地向我涌来。相比写《宝塔与湖》时的矛盾,我见证了真正如尖刀一般地企图淹没我的恶意。我见到了一群人能如何像癌症一样麻木不仁地扩散,把同根生的伙伴愉快地踩在脚底;或者一个人能如何像智齿一样血淋淋伤害自己声称正在保护的人,也就在我面前,微笑而轻易地修改着自己的说辞;我也经历并被迫参与了真正的欺骗与背叛……我每天要花上大多时间,爬起来,与这些战斗,保护我身边需要保护的人。
所以,我现在仍没有太多时间把它们写下来。
但这些都不影响我成为一个作家。甚至,只会让我更清晰地意识到我为什么要写。
有朝一日,我会把它们全写下来。但在此之前。我的文学都不是武器,都只是一面盾。一项作品在启发别人之前,需要真的使自己受益,在自己身上实践了最基本的功能,才能负责地传递给别人,所以它只会是一面盾。但正如我父亲所说,这面盾将是我与我的读者们最珍贵的武器了。
而我的父亲是对的。人生当然需要这样一面盾。
毕竟,未来的路还很长。——我是说,我总会有时间把它们都一一写下来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